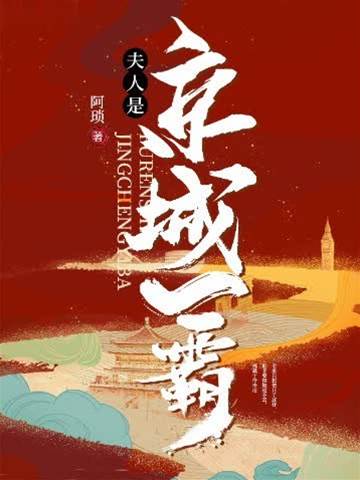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重生之蒲葦如絲》 65.六十五
話說到了這個地步,面子上是怎麼也過不去了。左氏立刻向坐在一旁的池氏發作:「濮太太,您這兒,好家教啊!」
池氏真是啞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個,大姑娘脾氣執拗,也沒別的意思。姐姐這樣的好首飾,不給也罷了。您別氣,小孩子不會說話,別放在心上。」
左氏見池氏口風極,竟是順著如姒的話說,連一句斥責言語都沒有,越發烈怒滿:「你們家如今也是出息了,這是跟搭上了好親家就目中無人了。哼,這回仲哥兒的事,燕家一句好話也沒說。你們家也跟著是不是?」一甩手,便怒沖沖揚長而去。畫扇被采菀塞了盒子,自然也不能再給出去,同時也是滿臉憤憤,心想這濮家大姑娘真是不識抬舉,白了一眼就趕跟著自家太太去了。
這場見面不歡而散,池氏與如妍如姝倒不算意外。就如同先前所想,如姒連自己親爹都左右開弓的打臉,又怎麼會將石二太太放在眼裡。甚至覺得這場面太平淡,如姒的火力連十分之一都沒開呢。
如姒對這個結果還算是滿意的,婚姻大事上最重要的還是父母之命,妁之言,只要左氏堅決反對,石仁瑯的那些心思算得了什麼。前世里就算左氏是因為石仁瑯有心而上門提親,那麼如今鬧這樣,是怎麼也不會再想自己做兒媳婦了吧。
如姒心輕鬆,幾乎是哼著小曲兒回了月居,繼續去設計年後開張的茶樓名字和招牌。既然主題是要走短平快的快餐路線,那什麼呢?麥當茶?茶當勞?肯德茶?茶德基?
胡思想了半日,到後來腦越開越,什麼小茶,茶底撈,永和豆茶,雖然沒一個合適當招牌來用,如姒卻自己咬著筆桿笑了好一會兒,就當是穿越的小小自娛自樂了。
Advertisement
鋪子名字一時想不出什麼好的,也就先放下了。如姒向窗外,又開始思念陳濯。他這一趟出城緝盜走了數日,起初如姒還不覺得什麼,過了七八天還沒有什麼消息就有點牽掛了。只是古代又沒通訊設備,除了打發采菀和陳潤每日去素三娘子那邊點個卯、既是照應著也是等消息之外,就沒什麼能做的了。
隨後數日里,如姒一直懸著心,做別的事便有些難以專註。尤其陳濯這樣的捕頭出差又不比那些行商運貨,除了聽說今年冬天格外寒冷而惦記著風寒冷暖和行路安全之外,也會擔心緝盜過程之中的兇險。畢竟上一回在隋掌柜命案中抓人之時,陳濯的右臂就曾經被盜匪劃過一刀。如姒偶爾也會再想起他手臂上這道傷疤,心裡很怕舊事重演。
轉眼進了十一月,算算陳濯已經離京辦差快要二十天了,京城又下了一場小雪,天氣越發寒冷,而陳濯還是沒有任何消息傳回來,連素三娘子也開始有些擔心。月居中的如姒同樣越發憂慮焦躁,卻無計可施。采菀夏月等人不免打起神,侍奉的時候格外謹慎小心,以免因著如姒的心緒不佳而躺槍。
十一月初九,京城難得連著晴了兩日,寒意好像也減輕了幾分,如姒便想著親自去看素三娘子。陳濯久久未歸,如姒也有些擔心素三娘子的。
衫更換完畢,藥材和補湯也準備好了,如姒剛要出門,便見小丫頭仙草急急跑來,臉上神有些怪異:「大姑娘,上門了!」
上門?那麼就是陳濯回來了!
如姒不免又驚又喜,然而片刻之後又覺得不對,陳濯若是回城應該會經過東城門,沒理由不知會陳潤一聲自己放心。難道這是個驚喜?又或者自己想多了、這是給如妍提親的?畢竟如妍也十三歲半,完全是可以說親的年紀了。
Advertisement
沉了片刻,如姒就采菀先將藥材和補湯送去百福巷給素三娘子,自己則叮囑仙草幾句之後重新回房等消息。
不到兩盞茶時間,雙蟬跟著仙草一起回了月居,臉上皮笑不笑:「大姑娘,老爺請您過去一趟。」
如姒心裡已經有了些約的猜測,便點點頭,照例由朝留著看家,自己帶著夏月過去。
跟著雙蟬過去,竟然不是到應該與或者客人見面的中堂,而是直接到了濮雒的書房。如姒見雙鶯站在門口,便知池氏應該也在,黛眉越發蹙,但腳步並不猶疑,由夏月打起簾子,便進門去觀這新版的花式作死。
書房裡濮雒臉鐵青地坐在書桌之後,另一旁的池氏憔悴之仍舊並未全然恢復,只是捧著茶碗低頭坐著,也看不出喜怒表。
如姒環視一圈,便注意到書案上擺著數頁書信,好像中間還夾著幾枚紅紅綠綠的花式書籤。
「老爺找我有什麼事?」如姒數日來一直心煩躁,無發泄,平素對著朝采菀等人只能強忍,看見了濮雒和池氏就再沒有控制脾氣的意思了。濮雒沒像之前一樣客客氣氣地坐下吃茶,而也不想跟這兩個人渣多廢話,就乾脆直接站在濮雒書桌前發問。
「什麼事?」濮雒上下打量了如姒兩眼,目中難得出幾分剛強的銳利,忽然怒喝一聲:「你還有臉問!孽!跪下!」
如姒冷笑一聲:「老爺不要沒事找事,聲音大不代表你有理,有話就說,沒話說我就走了!」
「放肆!」濮雒大怒,拍案而起,「你這個不孝,做出這樣喪德敗行的事還敢忤逆!給我跪下!」
如姒見他怒氣發,臉通紅,連額角和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確實不似作偽,若不是桌子隔著,只怕他都有心撲上來手。但如姒自己心裡何嘗不煩躁?退了半步,輕喝一聲:「夏月!」
Advertisement
夏月立刻箭步上前,將如姒擋在後,同時雙掌一錯,並指如刀,擺了個過招的起手式。夏月素來話沉默,衫也利落,這架勢擺出來再配上堅定而警惕的眼神,看起來實在殺氣十足。
濮雒萬沒料到竟有這樣一出,他這個讀書人口雖然也不怎麼樣,但是手肯定更不行,登時便本能地哆嗦了一下,子也不由退了半步。夏月散發出來的武人殺氣便如一柄利刃,將濮雒原先的氣勢攔腰斬斷。
「你,你,你真是反了天了!」當濮雒意識到自己的本能反應相當於大寫「慫」字的時候,立刻又生出新的怒氣,並不是很瀟灑但卻很準確地指著如姒的鼻子質問,「你竟還想弒父嗎!」
如姒掃了一眼基本等於裝死的池氏,又皺眉向濮雒:「老爺,您到底知不知道什麼有話直說?我進門到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還不知道,您大呼小的有完沒完?到底有什麼事?說清楚。」
濮雒又指了如姒好幾下,卻到底在夏月的威懾下不敢再往前半尺。轉而將手放下拍向桌子:「你看看這是什麼?當著你舅舅的面,你言之鑿鑿說不要父親母親給你安排親事,那你就自己去跟人家私相授嗎?你還有沒有廉恥!」
私相授?如姒想起陳濯,角浮起一冷笑,誰私相授了,我跟未來婆婆關係好著呢,我們是正大明的好嗎!而且此事真正的重點是,濮雒所說私相授的對象,還指不定是誰呢!
如姒點點頭,示意夏月收掌退後,自己上前拿起濮雒書案上拿起那一疊書信並書籤,快速瀏覽翻看了一回。越看邊冷笑越深,又仔細看了看那書籤,眉宇更是完全舒展。
Advertisement
濮雒看著如姒神這樣鎮定,也不由生了些疑:「你怎麼說?」
如姒看了他兩眼,臉上的輕蔑越發毫不掩飾,冷笑了兩聲便轉頭向池氏:「太太,老爺對我不上心、認不出我寫的字也就罷了。太太你也不認識?你不認識我寫的字,總該認識三姑娘的字吧!恭喜你啊,三姑娘自己尋了會讀書的好婿呢。」又將那幾枚題了詩的香木書籤抻出來摔在濮雒眼前:「濮翰林,濮老爺,您不是讀書人麼?字差別都分不出來?這一枚桂花的是我去年給如姝的沒錯,後頭幾枚上的字,這都一樣嗎?」言罷把那些信箋也扔在書桌上,甩手就走了。
如姒一路出去再被聽見濮雒的阻攔,而池氏的哭聲和濮雒的咆哮則很快在後響起。
如姒越想越生氣,看池氏的樣子是應該已經猜到了甚至默許了如姝的行,而濮雒的白癡程度則是又一次刷新對所謂讀書人的認知。這到底是怎樣的十年寒窗啊,簡直連基本的判斷能力都沒有。
但最讓如姒心煩的,還是這事背後的推手。上門是大事,不可能是石仁瑯自己私下去找的,必須是通過母親左氏,或者因著喪父而拜託了大伯父石贛,總是是得有長輩出面來提親的。他到底是怎麼說服長輩的?另一方面,石仁瑯若是發現自己被騙想報復如姝,將這些東西直接拿給濮家就是了,通過算什麼?
難道他還指將錯就錯,讓濮雒為了「遮家醜」而把自己許配過去?
此時此刻如姒真想跟石仁瑯大聲說:你到底喜歡我什麼?我改還不行嗎!
一路回到月居,如姒的眉頭都快擰麻花了,既牽掛著陳濯的遲遲未歸,又煩躁於石家的魂不散,進了門將斗篷解了朝邊的人手裡隨手一扔:「先掛著吧,我不出門了。」
「天太冷,不出門也好。」接了斗篷的人微微含笑,聲音是慣常的沉穩而溫。
猜你喜歡
-
完結142 章
穿越之不受寵王妃
琳綾一個現代女子,莫名其妙的穿越到了逍遙國若薇公主的身上,爲了國家的利益,她必須出嫁到赤炎國,嫁給一個脾氣暴躁的、冷酷無情、根本不把女人放在眼裡的王爺…他就是看她不順眼,他處處刁難她,對於他來說看她難堪就是一種享受.她成了一個不受寵的王妃,哼不就是不受寵嘛!有什麼好怕的.我琳綾照樣能夠玩轉古代,而且那不是還有一大堆美男在等著自己嘛!
21.2萬字8.18 36005 -
完結506 章

獨佔醫妻
【女主穿越,雙潔,互寵,一生一世一雙人】他是君侯府嫡子,卻被人設計被迫娶了將軍府病癆子嫡女,本已做好成為鰥夫準備,卻不想那勞什子沖喜還真有用,再見他那小娘子,竟然可以下床走動了,他覺得做不成鰥夫了,那相敬如賓也蠻好的……可是那心底漸漸浮現的酸酸甜甜、患得患失的滋味是何意?
88.7萬字8 55176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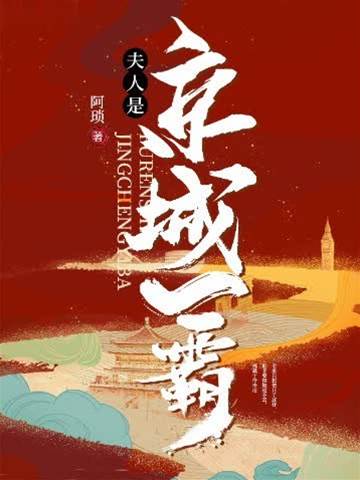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1726 -
完結115 章

和清冷權臣共夢,嬌嬌臉紅心跳
【甜寵 雙潔】薑四姑娘年幼便喪失雙親,常年躲在薑家的內宅裏從未見過人,及笄後還傳出相貌醜陋膽小如鼠的名聲,引得未婚夫來退親。隻是退親那天,來的並不是她未婚夫,而是未婚夫的小叔,更是她夜夜入夢的男人。薑芙有個秘密,從及笄後她每晚就夢到一個男人,那男人清冷淩厲,一雙鐵掌掐住她的腰,似要將她揉進懷裏......後來未婚夫退親,京城眾人譏諷於她,也是這個男人將她寵上天。---蕭荊性子清冷寡欲,年紀輕輕就掌管金吾衛,是京城貴女心中的最佳夫婿,隻是無人能近其身,更不知蕭荊早就心折夢中神女。夢裏乖順嬌媚的小姑娘,現實中極怕他,每每見了他都要躲開。可她越是怕,他就越想欺負她。“你夜夜夢到我,還想嫁給旁人?”又名:春/夢對象是未婚夫小叔
20.9萬字8 310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