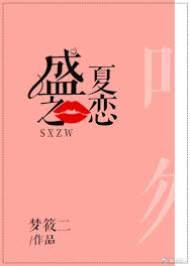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重生破繭成蝶》 第五百一十八章、借勢
飯桌上,慕建國和吳懷兩人頻頻舉杯,兩人不談政治,不談夏桐的婚事,只是說些無關要的話。
今天最高興的莫過於金雛,一方面是慕建國和吳懷總算坐在了一個飯桌上,雖然沒有把酒言歡,但是起碼不再冷眼相對;另一方面是賀慕堯和程毓的到來,意味著兩人至八字有了一撇。看來,慕家的兩個難題都要解決了。
最不開心應該是常若善,本來不大喜歡程毓,沒想到現在還要跟程毓為親戚,程毓娶了賀慕堯,對程家的事業絕對是一個大助力,這將來程毓的氣焰不得更囂張了?
兩個不喜歡的人一個了自己兒媳婦,一個了自己外甥婿,怎麼想怎麼不爽。
偏偏程毓這一會也不肯安靜下來。
「姥姥,你說是我和堯堯先辦婚禮好還是小二和夏桐先辦婚禮好?」程毓隨著賀慕堯改口姥姥了,以前一直是的。
金雛聽了這聲「姥姥」,笑得都合不攏了,說:「都行。不了,還是你們先辦吧,你們兩個這麼大歲數了連孩子都沒有,你們抓辦。斯年好歹兒齊全了。」
「我就知道姥姥疼我,姥姥,您這麼仗義,我送姥姥一份大禮吧,姥姥喜歡什麼?」程毓問金雛卻看著賀慕堯。
「我姥姥喜歡的東西多了,什麼貴你買什麼就好了。」賀慕堯沒好氣地回了一句。
「堯堯吃醋了?堯堯,沒關係,我也送你一份大禮,你喜歡什麼?」程毓忙換了一副表。
「我們們呢?我們們結婚你不預備送份大禮?」慕斯年問。
程毓斜了慕斯年一眼,說:「我憑什麼送你,要送也是送夏桐。別忘了,我是夏桐的娘家人。東西我都預備下了,絕對震撼。」
Advertisement
「什麼呀?」趙慕芝好奇先問了出來。
「說出來就沒有意思了,到時,我準備給大家曬出來。」程毓賣了一個關子。
「這個主意不錯。到時,我們們也把給夏桐的陪嫁曬曬,省得有人總以為我們們家桐桐佔了便宜,我們們夏家吳家也不是沒有名姓的人家。」趙慕芝笑著說道。
廖宛玫聽了這話,笑著說:「萱萱,你怎麼也越來越像個孩子?老話說的好。財不白,包子有不在褶上。就像你溫萱,即便你穿一地攤上的服,可是有你溫萱的份在這擺著,誰敢小看你?今天的桐桐也不是前幾年那沒有半點名氣的夏桐。需要你們大家給撐撐門面。我這曾孫現在完全有底氣,可以站在斯年的邊。」
「謝老祖宗提醒。是我糊塗了。」溫萱笑著認錯了。
「媽不是糊塗了。是不捨得把小姑子嫁出去,生怕委屈了夏桐。這幾年沒四搜尋好東西,見了拍賣會就想去看看,有什麼好字畫都要想盡辦法拍了來,比對我和阿越強多了。」趙慕芝故意噘了噘。
溫萱聽了這話,笑著說:「這話回去問問你媽就知道了。你結婚時你媽媽是不是恨不得把家裡所有的好東西都給你當陪嫁,生怕委屈了你。」
趙慕芝聽了嘻嘻一笑,說:「那也是看在媽媽的彩禮份上。」
賀慕堯見常若善聽了這些臉上有些不自在,想了想。拍著手說:「對了,夏桐,我有件好消息要告訴你,我爸爸說了,前幾天他接見外賓,對方特地提出要看看你的書畫刺繡作品,我爸把他們帶到了程毓的店裡,他們挑了好幾幅書畫走。」
「有這事?我有這麼大的名氣?」夏桐不大相信這事。
「真的,是國來的,他們說在你老師看到你的作品,也看到你繡的山水雙面綉,很神奇,知道你在圍棋和古琴方面的名氣很大,很好奇你怎麼還能寫的一手好字,畫的一手好畫。我爸還自掏腰包買了幾張你的古琴專輯送他們呢。」
Advertisement
夏桐一聽這個,就知道是借bill的了,bill手裡有不自己的東西,前段時間,bill在家裡接了電視臺的專訪,他家的客廳就擺了好幾樣夏桐的作品,當然也包括那幅雙面繡的小擺件。
以bill的名氣,再刻意提到夏桐幾句,夏桐想不紅也難。本,就是一個話題人,一個這麼年輕漂亮的華人古琴家跟bill的樂團合作了兩年,最後一場音樂會謝幕的時候的丈夫當場向求婚,很多波士頓的市民還記得帶著家人在河濱公園嬉戲的影,總是很謙恭的,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
「這事是真的,我這次來就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想補充些字畫,還有一點,你能不能綉一件大宗作品,作為鎮店之寶放在我的店裡?」程毓問。
「綉是在綉,可是,我是預備自己開畫展時用的,等我開完了畫展,再放你店裡好了。還有,這刺繡相當的花時間,我一年也未必能有一件好綉品,我也是想,既然綉就要綉自己的特東西。」
夏桐現在繡的是自己的那幅大型工筆畫,因為有大量的人,每個人的服裝表什麼的都不一樣,夏桐一年也未必能完工,現在每天還要陪老人說說話。
夏桐那次看了廖宛玫拿出來的幾幅綉品,了些啟發,也預備一年綉一到兩幅作品,大件的,同時配上自己的書畫,過幾年開一個大型的書畫綉展。
夏桐這幾年不打算出去上班,說實在的,公司的事本用不著心,那些事誰都可以做,而夏桐想趁自己年輕的時候,再多磨練些自己的字畫,想留下一些好的作品,這個比去公司上班要有意義得多。
「以前的作品也沒有嗎?隨便拿一幅好的來也行。」程毓還不死心。
Advertisement
「以前?那你去找若愚舅舅吧,他手裡有十幅唐詩作品,就是不知道他肯不肯讓給你。」夏桐自己手裡還真沒有留下什麼綉品。
「我有一件旗袍,桐桐繡的梅花都能看出一片片在微風中飛舞,能聞到梅香,我穿了幾次,誰都誇好。」吳明伊笑著說。
「真的嗎?肯讓出來?」
「借你擺幾天還是可以的。」吳明伊笑著點點頭。
「姥姥,你看人家吳都慷慨解囊了,您不能這麼小氣吧?」程毓又磨上了金雛,他從賀慕堯裡知道,夏桐有一幅綉品,出價十萬夏桐沒賣,送給了金雛。
「好好,我也借你擺幾天。」金雛也笑著點頭。
「那我畫廊就多了一個賣點了。我現在就打算做這些非質文化方面的工作,我要把夏桐修補的那些龍袍全都拿出來展覽。」程毓很認真地說道。
夏桐心念一,看了一眼廖宛玫,問:「你知道清末的江南廖家嗎?」
「當然,那是做綉品起家的,用的。」
「我老就是廖家刺繡的傳人,我手裡還有我老的兩件綉品,不如你也借給你,撐撐門面。」
「真的?老,您是江南廖家的傳人?」程毓驚喜地問道。
廖宛玫聽了點點頭,說:「可惜,拿不針了,我的這點本事,都教給了桐桐。」
「夏桐,我不是吹牛,到時你的綉品,我給你掛上一個江南廖家的嫡派傳人,你的綉品還能賣高一個價。」程毓興了。
「去去去,nǎ里涼快nǎ里呆著,我家桐桐的綉品是拿來賣的嗎?我們們家缺錢了?」慕斯年不聽了。
「哎呀,你們說了半天,我還沒說到正題呢。」賀慕堯著急了。
「什麼正題?」
「我爸說,他下個月要去出訪兩個東亞國家,你的名氣在東亞最響了,所以,我爸說,要把你的專輯和你的書法當做一項特別的禮送給對方。」
Advertisement
「什麼?」夏桐驚呆了。
「你先聽我說,我爸說,你只寫小幅的唐詩作品就行,別太大了,不然的話價格會超標的。」
「哈哈,瞧瞧,我慕家的兒媳寫的字都能當外禮送出去了。」慕建國聽了哈哈大笑。
「怎麼還自己人挖起了自己人的牆角?真是一個傻丫頭,這事給我辦就行了,我們們還能一筆傭金,也能把我們們的畫廊名氣打出去。」程毓彈了賀慕堯一下。
當然,誰知道程毓說的是玩笑話,他不是缺錢的人。
「夏桐,恭喜你,你真是越來越厲害了。」趙慕芝舉起了酒杯。
「這確實值得好好慶賀。」溫萱也笑了,舉起了杯子。
一晚上,就常若善和黎如珍沒怎麼開口說話,也不進話,要不是慕建國拉著,要不是想看看兩個寶寶,常若善真的不想進夏家這個院子。
說來也是怪,現在的夏桐確實越來越厲害了,名和利都有了,可是常若善就是喜歡不起來。
夏桐越功,就顯示常若善當年的眼拙,這是其一,其二,慕家不缺名和利,尤其是慕斯年,慕斯年需要的是一個能穩穩噹噹在他邊照顧他的人,這樣他才能一心一意地顧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兩頭辛苦地跑來跑去,已經跑了兩年國還不夠,現在又要往鄉下跑了,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
猜你喜歡
-
完結485 章
萌妻小寶神秘爹地求抱抱
魚的記憶隻有七秒,而我,卻愛了你七年。 ——喬初淺。 喬初淺從冇有想到,在回國的第一天,她會遇到她的前夫----沈北川! 外界傳言:娛樂圈大亨沈北川矜貴冷酷,不近人情,不碰女色。 卻無人知道,他結過婚,還離過婚,甚至還有個兒子! “誰的?”他冰冷開口。 “我……我自己生的!” “哦?不如請喬秘書給我示範一下,如何,自—交?”他一字一頓,步步趨近,將她逼的無路可退。 喬景言小朋友不依了,一口咬住他的大腿,“放開我媽咪!我是媽咪和陸祁叔叔生的,和你無關!” 男人的眼神驟然陰鷙,陸祁叔叔? “……” 喬初淺知道,她,完,蛋,了!
86.5萬字8 13912 -
完結471 章

萌寶尋爹:媽咪太傲嬌
母親去世,父親另娶,昔日閨蜜成繼母。 閨蜜設局,狠心父親將懷孕的我送出國。 五年后,帶娃回國,誓將狠心父親、心機閨蜜踩在腳下。 卻沒想到轉身遇上神秘男人,邪魅一笑,“老婆,你這輩子都逃不掉了……”
83.4萬字8 75541 -
完結84 章

敗給喜歡
多年后,雨夜,書念再次見到謝如鶴。男人坐在輪椅上,半張臉背光,生了對桃花眼,褶皺很深的雙眼皮。明明是多情的容顏,神情卻薄涼如冰。書念捏著傘,不太確定地喊了他一聲,隨后道:“你沒帶傘嗎?要不我——”謝如鶴的眼瞼垂了下來,沒聽完,也不再停留,直接進了雨幕之中。 很久以后,書念抱著牛皮紙袋從面包店里出來。轉眼的功夫,外頭就下起了傾盆大的雨,嘩啦嘩啦砸在水泥地上。謝如鶴不知從哪出現,撐著傘,站在她的旁邊。見她看過來了,他才問:“你有傘嗎?”書念點頭,從包里拿出了一把傘。下一刻,謝如鶴伸手將傘關掉,面無表情地說:“我的壞了。” “……” *久別重逢/雙向治愈 *坐輪椅的陰郁男x有被害妄想癥的小軟妹
24.9萬字5 8280 -
完結501 章

金牌律師Alpha和她的江醫生
ABO題材/雙御姐,CP:高冷禁.欲腹黑醫生omegaVS口嫌體正直悶.騷傲嬌律師alpha!以為得了絕癥的岑清伊“破罐破摔“式”放縱,三天后被告知是誤診!換家醫院檢查卻發現坐診醫生竟是那晚和她春風一度的漂亮女人。岑清伊假裝陌生人全程高冷,1個月后,江知意堵住她家門,面無表情地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我懷孕了。第二句:是你的。第三句:你必須負責。——未來的某一天,江知意堵住她家門......
172.4萬字8 11795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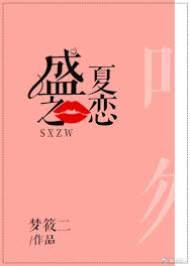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6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