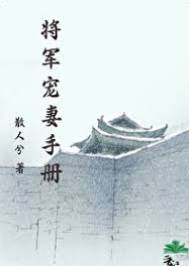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玉殿嬌》 第58章 喜脈
謝灼攥著危眉的手往外走, 一路上宮人皆避讓,危眉求他松開自己,謝灼全然不在意。
謝灼帶進了側殿, 危眉俯在桌案邊,渾僵,如墜冰窟。
危眉心涼到麻木,看到殿門外宮人來回奔走, 說話聲哭嚎聲影影綽綽傳側殿。
不知過了多久,僵的四肢才恢復知覺, 終于接了這個事實——
的丈夫已經死去。
帝國失去了最高的統治者,如今的, 份也不再是尊貴的中宮皇后。
燈籠的在夜空中回,森森就像鬼魅。
危眉做了一夜的噩夢,夢里帝上全是, 自己上也是, 從夢里驚醒時, 大口大口息, 長發散在肩膀上, 整個人虛弱無比, 一轉眼,刺眼的亮就從窗外照了進來。
危眉從榻上下地,形搖搖晃晃, 一雙手從旁出, 扶住了的手臂。
“娘娘, 您小心點。”
危眉聽到承喜的說話聲, 這一刻, 積依舊的緒涌出, 淚水奪眶而出。
握住承喜的手,張地問:“你要不要,謝灼有沒有對你手?”
承喜臉不太好看,卻也強撐著向危眉出笑容道:“攝政王沒對奴婢做些什麼。”
危眉知曉小宦盡忠職守,一路跟著自己不容易,心中激涕零,走到梳妝鏡前,拿出珠寶首飾塞到他手中。
小宦也掉了幾滴淚。
主仆二人寒暄了幾句,危眉聽到嘈嘈雜雜的說話聲,詢問外頭況怎麼樣。
承喜如實道:“陛下駕崩,從昨夜到今早,未央宮來了好幾波人,攝政王一直在與屬下議事,太后娘娘匆匆趕來,看到陛下的龍,悲慟不已,已是昏了過去,如今外面還圍著不人。”
Advertisement
危眉輕聲道了一句“好”,走到梳妝鏡前,拿起梳子給自己梳頭,比起離京前人瘦了一大圈,瞧著弱不勝,虛弱無比。
而是皇后,今日這個場合,自然不得不出面。
未央宮上下掛滿了素縞,白紗隨著風飄,氣氛沉痛且抑。
大殿之中擺放著一棺柩,眾嬪妃哀哀地泣,兩側各跪著十二沙彌,低低的誦經聲從他們口中傳出來。
隨著皇后的到來,眾人讓開一條路。
危眉在大殿中央跪下,著眼前漆黑的楠木做的棺柩,眼前浮現起昨日帝死前的一幕幕。
覺口一陣疼痛,四周空氣越發稀薄。對帝的死沒有多愧疚,可此刻過往的恨意與怨意浮上心頭,為自己的過往遭遇傷心,竟也真掉下了幾滴淚。
危眉膝行幾步,到帝的棺柩邊,痛哭道:“陛下——”
聲音哀轉,滿是絕,猶如啼,聽得人肝腸寸斷。
眾人看著皇后娘娘一素,俯趴在帝棺柩前,長眉如煙,目染哀愁,整個人脆弱至極。
那樣明的春,灑在上,卻加重了上的伶仃。
殿前來的員,皆避開了眼睛,余下的宮人也低下了頭,目染上了幾分憐憫。
說到底,也是一個可憐的人。
這一個月來,宮中大大小小發生了許多事。先是葉婕妤小產,后是皇后不見行蹤,一個月不曾面。
對此,外界眾說紛紜,有人說皇后是慘遭攝政王幽,也有人說皇后已經不測,更有不堪耳的言論,說是皇后被攝政王凌.辱,不堪折磨,于未央宮中自盡,而攝政王將此事了下來,不許泄一點風聲。
裴太后不是沒有帶人來闖未央宮要見帝,皆被攝政王的人給攔在了殿外。
Advertisement
然而不管哪一種猜測是真,有一點肯定的是,如今帝崩逝,皇后新寡,膝下沒有子嗣,攝政王報當年皇后的背叛之仇,又或是政治立場的不同,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眾人見皇后帶漸寬,像極了這些時日到折磨,憔悴得不樣子。
殿彌漫著哀傷的緒,皇后哀哀痛哭,幾乎暈厥過去。
到了正午,殿中文武百離去。
危眉手絹揾淚,在侍的攙扶下起,避開眾人到殿整理容貌。
挑開簾子,尚未走幾步,后便傳來一道腳步聲。
來人走得沉穩,是一道男人的步伐。
危眉轉過,目便是一道頎長的影,裴素臣挑開簾子走了進來,簾子悄然落下,擋住了外人的視線。
“表妹。”
危眉一雙通紅的眼睛看著他:“表哥。”
裴素臣一步步走近,危眉鼻尖聞到他上水沉香的氣息,不知他找自己有何事。
“表哥有什麼話與我說?”
危眉仰起頭問,聲音帶著幾分哭腔。
“表妹一個月不曾面,可否告訴我,這些日子你在未央宮經歷了什麼?”
裴素臣的目太過銳利,就像是冰寒的雪,薄薄的眼簾抬起,里面華畢。
裴素臣又近了一步,危眉側開了目,低頭用帕子去眼角淚珠,閉了閉眼,好一會才抬頭呢喃道:“攝政王是將我囚了。”
裴素臣眉心一下鎖住。
的面慌張,眼里寫著恐懼,落淚的樣子惶恐不已,如同沾滿珠明的花。在他面前哀傷而哭,不得不說,這副容確實能引起男人的保護。
“謝灼囚了我,令我待在未央宮中,不許出殿一步。這些日子來,我生不如死,過得渾渾噩噩,昨日親眼看著他對陛下了手,我做了一夜的噩夢,恨不能隨陛下而去,可謝灼監視著我,將宮的一切尖利的東西都收走,不許我尋短見。表哥,你說他為何還留著我?”
Advertisement
面前遞過來一塊干凈的絹,那雙手骨節分明,纖長有度。
“表妹將眼淚,我未曾用過這塊帕子,”
危眉搭上他的手,指尖蜷起:“多謝。”
等完了淚,裴素臣才道:“謝灼是否對你做其他更過分的事?”
他口中過分的事指什麼,不言而喻。
危眉搖頭否認:“只是囚,沒有強迫我。”
裴素臣低低道了一聲“我知曉了”,聲音溫:“好不容易能見你一面,知道你沒事便放心了。我與太后都很擔心你。不是不想來見你,是謝灼的人把持了未央宮,如何也不許人進來。”
春窗,讓他清冷的眉眼看上去和了幾分。
危眉握了手帕,心中莫名被的緒填得滿滿的,從小表哥便對格外關懷,雖然有時不能完全幫到,但關心也是真的。
危眉眼眶發酸:“多謝表哥說這些話安我。也謝謝你之前告訴我真相,否則我現在還被蒙在鼓里,不知危月的真實份。”
走上前去,還說幾句,眼前忽然一黑,子往前栽去。
裴素臣從旁扶住:“怎麼了?”
危眉有些頭暈目眩,好一會才回過神來,意識到自己倒在他懷里,連忙避嫌地退開一步,搖了搖頭,“最近心力瘁,子有些勞累。”
裴素臣嗯了一聲,低下頭在耳畔道:“陛下已經崩逝,你便趁著現在和我去建章宮,太后邊的人可以護著你。”
危眉眼睫輕輕一,對上裴素臣琉璃似的眸子。
幾乎是一瞬,危眉就想好了回答。
太后那里是虎口,謝灼這里何嘗不是狼窩?哪一個都靠不住。
能依仗的只有自己,必須先在兩者中維系一個平衡。
Advertisement
僅僅依靠自己的能力,絕對逃不出謝灼的手掌心,所以瞞了實,告訴裴素臣自己被囚在未央宮,也是看他聽了這話,能否助自己一臂之力。
危眉輕聲道:“我去整理一下妝容,午后便去建章宮探母后。”
裴素臣道了一句“好”,便先離去。
危眉回到自己的側殿,換了一件素的。
卻說那邊,裴素臣來到建章宮,宮人迎上去,恭敬行禮:“裴大人。”
裴素臣頷首示意,繞過簾帳,一直往里走,看到裴太后坐在床榻之上,神凄惶,兩鬢斑白。昨夜還是一頭黑發,今日已經是雪發蒼蒼。
幾乎是一夜白頭。
裴素臣在榻邊坐下,往裴太后后墊了一個靠枕:“姑姑?”
裴太后目從窗外落到了他上,低沉的聲音問:“見到你表妹了?”
裴素臣道:“見著了。這一個月來,表妹都被謝灼關在未央宮,昨日更是親眼看到了謝灼對陛下手。”
裴太后冷笑連連,淚水從深陷的眼窩里滾下:“謝灼這個狗畜不如的混賬,我恨不能生啖其,他的,咬斷他的嚨!”
說到最后,裴太后已是暴怒,抄起一旁姑姑手里的藥碗,重重砸碎在地。
殿頓時跪了一片人。
的口上下起伏,目狠毒。
面對攝政王的步步,裴家不是沒有作,也趁著謝灼離京半個月了手,在朝堂給攝政王一黨施,卻都被對方一一化解。
裴家是文世家,再如何權勢深厚,相比于把握王朝命脈軍隊的武將,天生便幾分話語權。
如今帝一死,帝位空懸,兩方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裴太后手撐著額頭,“不能再等了,得先穩住儲君之位。眼下要麼從宗室里過繼一個孩子到皇后的膝下,要麼讓后宮有妃子有孕,到時候對外聲稱是陛下的腹子。”
抬起頭來問:“能信得過皇后嗎?”
裴素臣閉了閉眼,薄輕啟:“可以。”
“與攝政王青梅竹馬,萬一倒戈投靠攝政王怎麼辦?”
裴素臣斬釘截鐵道:“不會。”
裴太后詢問緣由。
裴素臣道:“表妹格實則外韌。既得知危月的真實世,也知曉當年謝灼接近都是欺騙,絕對不會再對謝灼有所眷,甚至由而生恨,姑姑應當更信賴才是。”
裴素臣素來會察人心,能這樣說便有十足的把握。
裴太后聽他說完,眉心深深皺起,良久道:“那便聽你的話,相信你表妹一回。讓先過繼一個子嗣,然后過段時日,對外聲稱已經懷了陛下的腹子。”
裴素臣道:“可。”
“此事由你來勸。”
裴太后看向裴素臣,尚未等到他的回話,忽嚨發,重重地咳嗽起來。
姑姑連忙遞上去一塊錦帕,捂著太后的,揭開一看,蜿蜒,猶如紅蓮。
姑姑轉頭焦急地喚一側立著的太醫,讓他上前來給太后診脈。
恰在此刻,殿外人稟告,道:“皇后娘娘到——”
危眉走進大殿時,見到一群人圍在太后榻前,太后角流出跡,面慘白如紙,哆嗦,額頭卻因為虛弱滲出許多細汗。
太醫給施針,裴太后痛苦蜷起子。
良久,太醫才提著藥箱起,了額頭上的細汗。
“微臣已經施針完畢,太后娘娘還需多服用湯藥,切記萬不可再怒傷肝。”
宮人捧著湯藥殿,危眉主地上前,接過藥碗,“給我吧。”
空氣里漂浮著苦藥味,織著淡淡的腥味,縈繞在危眉鼻端,怎麼也散不去。
眉心微蹙了一下,想要下那份不適,可忽然腹中一陣惡心往上涌,當即擱下藥碗,帕子掩,干嘔了幾下。
這一聲吸引了殿所有人的目,裴太后與裴素臣齊齊向。
危眉只覺如芒在背,指甲掐進手心。
企圖用笑容掩飾自己的慌張:“兒臣今日在未央宮中跪了許久,有些子不適,頭暈目眩。”
可旋即,又干嘔了幾下,子輕輕地蜷起來。
殿空氣凝固住了。
危眉轉過來,對上裴太后投來莫測的目,眼里神瞬息變幻,先是詫異,后是猶豫,最后是狐疑與震驚。
裴太后扶著姑姑的手臂,抖著聲音道:“太醫,你來,快給皇后探探脈象。”
猜你喜歡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58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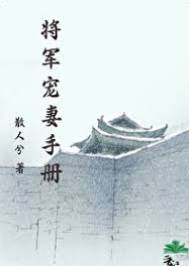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10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