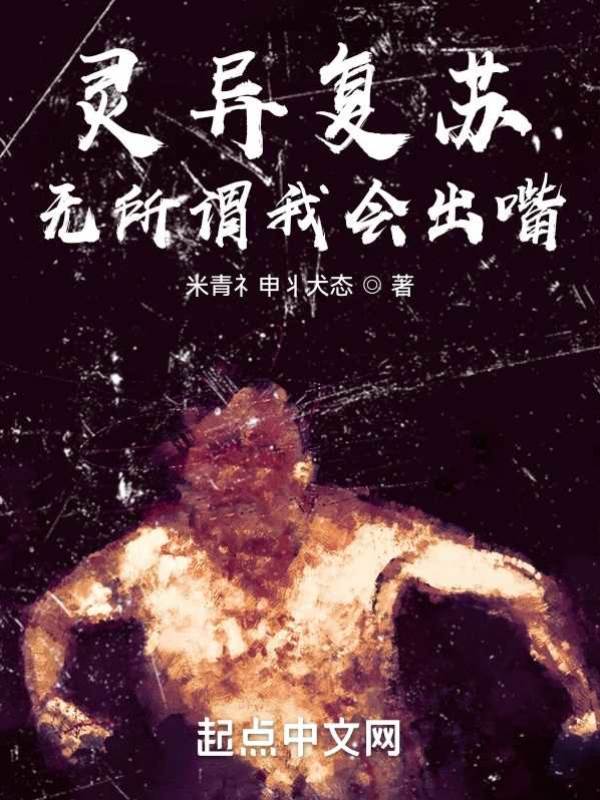《開封府美食探案錄》 第60章 熏雞
說起典當品, 人們往往頭一個想到的就是隨可見的當鋪,但實際上,還有許多其他行當的鋪面也兼做典當的買賣, 食住行,無所不包。
有時客人來買東西, 恰巧手頭拮據, 便將所有抵消一部分錢款,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
就好比, 一件棉質單在正經當鋪可能只能換取二十文錢, 但如果去布莊或店, 只要你在他家買東西,或許店家就會出二十五文收購。
別小看這區區五文錢, 在賢惠的媳婦們手中, 甚至就夠一家老小吃一頓了。
而被收走的則會經由店家拆分翻新, 略加點修飾,重新制作, 轉手以三十甚至四十文的價格賣出。
這就使得尋找包袱的任務變得極為繁重。
元培一副過來人的架勢,“對啊, 這種事很常見的嘛。當年我的佩劍損壞,去兵鋪子買新的時, 饒是鐵質低劣,也還用舊劍抵了一半價錢呢。”
阿德苦連天, “哎呀我的爺, 都什麼時候了,您還得意呢。”
沒出事的時候這種做法確實兩相益, 可如今命案當頭, 苦的可就是他們這些差役。
沒奈何, 外出找包袱的衙役們只得又將搜查目標從單純的當鋪擴大到當鋪和布莊、店。
若這幾再找不到,恐怕還要去別的管吃喝拉撒的鋪面問問。
因目標太多,一整天下來,愣是半點結果都沒有。
傍晚收工時,馬冰抓在東河縣轉了幾圈,買了只被烤暗金的熏,又買了點本地產的大豆,回去喂馬,意外發現王征家的騾子還沒還,便順手逗弄起來。
這頭騾子長得不錯,在同類中已算高大健壯,圓滾滾的眼睛看著頗溫順。
Advertisement
似乎聞到了馬冰提著的豆子的香氣,它蠕著將頭出來,又不敢靠得太近,小心翼翼地看著。
馬冰失笑,果然抓出幾把放它眼前的食槽中。
那騾子哼哼了幾聲,甩著尾,快樂地吃起來。
它似乎一點兒都沒有被染主人被害的霾。
沒心沒肺的。
陳維種地確實有一手,今年的黃豆還沒下來,馬冰買的自然是去歲的存貨,但顆粒飽滿,個頭都比外頭的大一圈,看著就喜人。
昨兒開封府眾人吃著豆腐也覺香甜,馬冰就想著,回頭新一季的大豆下來,一定要去東河縣開的糧鋪里買些。
用這麼好的黃豆做豆腐,燉魚頭吃得多香呀!
馬匹和騾子、牛、驢等是分開住的,不然各類牲口脾不同,放在一容易打架。
馬冰喂完騾子,提著黃豆去隔壁找自家大黑馬,就見謝鈺也在喂馬。
真心馬的人并不會完全將馬匹在他人手中,哪怕暫時客居別,也會時常過來瞧瞧,說說話,刷一刷,增進。
謝鈺是軍出,坐騎就是最忠誠的戰友和伙伴,分來的比常人更深些。
馬冰的大黑馬也認得他,見主人遲遲不到,便踢踢踏踏往他邊湊,又長了脖子要去人家的坐騎食槽里搶飯吃。
謝鈺的馬兒格沉穩,對認識的同類很好脾氣,不好意思直接驅逐,眨著眼求助似的過來:
咋辦?
謝鈺有點無奈,猶豫了下,還是給黑馬也放了些。
一般來說,騎士需要馬匹的絕對服從,所以他很給別人的馬兒喂食。但這個……
他搖了搖頭,搬了些草料放大黑馬面前的食槽,不住慨道:“真是什麼人養什麼馬……”
Advertisement
剛好過來的馬冰:“……”
不是,謝大人您什麼意思?
刻意放重了腳步,謝鈺一僵,有點懊惱地著手朝空氣打了下,轉打招呼,“馬姑娘。”
他極在背后議論別人,今日不過有而發,卻偏偏被正主逮個正著,難免尷尬。
馬冰瞇著眼瞅他,倒背著手,圍著他轉了好幾圈,“謝大人呀謝大人,好個正人君子……”
謝鈺被看得大囧,耳尖兒都泛了紅,十分不自在。
就是后悔,很后悔!
他認命地嘆了口氣,“抱歉。”
馬冰哼了聲,先往自家大黑馬腦瓜子上敲了個暴栗,用不大不小的聲音說:“你呀你,瞧瞧這點出息,強盜啊!”
就算我不來,難不東河縣衙的馬夫還能著你?
大黑馬吭哧吭哧嚼草料,吃得頭也不抬,只用大眼睛斜覷著,半點不見悔意。
那我就只是試探下嘛,他非要給,送到眼前的好東西還能扔出去?
看他們如此,謝鈺只覺好笑。
當初第一次見面時,這姑娘分明可以明搶的,卻還是給了自己一點藥!真是天地。
“大人覺得兇手會是什麼人?”馬冰去提了桶水,給大黑馬刷。
天熱了,馬兒也容易出汗,時常用清水洗刷一下,清爽又干凈。
大黑馬快樂地甩著尾,回過頭去討好地拱了拱的腰。
馬冰嫌棄地推了它一把,“滿都是渣滓!”
謝鈺跟著往邊上避了避,“如今看來,誰都有可能。”
據劉喜和尤小田夫婦的供詞,王征當日離開時已經有了幾分醉意,一個看上去頗值錢的醉鬼,絕對是歹人的最佳目標。
河岸附近有人來,是最好的手地點,告示出去數日,仍未找到一名人證。
Advertisement
可惜案發后幾天頻降大雨,水位暴漲,犯罪現場已經完全被淹沒于河水之下,沒辦法尋找新證。
那兇手是怎麼將王征從騾子背上弄下來的呢?
恐嚇?設局?
或者……本就是王征自己下來的。
酒勁兒會持續很久,所以不能完全排除王征回家途中酒勁上來,自己掉下騾背。
而喝酒的人容易口,也可能他走到半路口,停下來去河邊找水。
兇手或許是在城中就開始尾隨,又或者當時恰好就在河邊,無意中看見了這個財富外的醉鬼。
此時附近無人,王征又醉醺醺的,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機會!
馬冰皺眉,“若真是圖財,搶了就走就是,何必殺人?”
那王征固然不是什麼好貨,但若只是為了一點財就下死手,也著實過分。
謝鈺看了一眼,“或許有人天生狠心,也或許是王征反抗,惹惱了兇手,或是看到了兇手的臉,索一不做二不休。”
馬冰點頭,“確實。”
但馬上又發現一個奇怪的細節,“謝大人可曾記得尤小田夫婦說過,當時劉喜暴起打人時,王征半點沒有反抗。”
丟了這麼大的人,他也只是被驅逐出門時外強中干地嘟囔幾句,然后便憤憤離去。
而衙役們之前詢問王征的友人時,也有許多人說過此人欺怕的品。
因他太過“識時務”,所以在外面幾乎從不,當然,也不敢與人結仇。
照這麼說,后面遇到歹徒,他應該更害怕才是,真的會反抗嗎?
謝鈺沉片刻,心中漸漸有了猜想。
眼下有幾個可能:
一是兇手本兇殘,視人命為無,不過順手殺掉王征。
二是兇手是人,被王征無意中看到面目后,殺人滅口。
Advertisement
不然其實醉酒的人在慌中真的很難記住東西,只要兇手逃,茫茫人海卻去哪里找?完全沒必要滅口。
而第三種可能,就是王征真的反抗了,惹怒罪犯,將其殺害。
表妹家的經歷讓他怒火中燒,卻又畏懼劉喜的格而不能反抗,一路走來必然憋了一肚子火。
而偏偏這個時候,又有人跳出來搶劫,這樣的倒霉事在短時間迅速疊加,王征怒意上頭,在酒勁的作用下做出比平時更為勇猛大膽的舉也有可能。
又或者,王征發現對手是弱者!
在接的第一時間,王征迅速做出判斷:這是個自己可以對付的弱者。
欺怕的本卷土重來,他覺得自己被蔑視,再加上之前的氣,所以當即決定反抗。
奈何王征錯誤地估計了雙方實力,最終被殺。
但王征的親友都被仔細盤問過,大家的反應都很正常,所以人作案的可能不大。
那麼……
就是府最不想遇見的陌生人一時興起作案。
這種案子只要兇手小心些,不留下證據,幾乎無從查起。
因為大街上走的,甚至與你肩而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兇手。
“別板著臉啦,”馬冰收拾起水桶和草料袋子,“慢慢來嘛,走,我請你吃!”
又是!
自從來到東河縣衙,一行人每頓的飯桌上至有一半以上的菜肴與相關,饒是再怎麼好吃,幾天下來,大家都已經聞變。
偏謝鈺不是那等會仗著份胡要求的子,知道民生多艱,不忍心要求陳維上別的好飯好菜,只好悶悶忍耐。
看著謝鈺帶著幾分苦大仇深的臉,馬冰哈哈大笑,甩了甩手上的水,干脆拽著他往外走,“走嘛,這個烤應該不同,我聞著很香的。”
謝鈺被拽了個踉蹌,并未掙扎,迅速調整了姿勢后跟著往外走。
馬冰并未回頭,似乎很放心將后背給他,從謝鈺的角度看去,被高高吊起的馬尾辮一甩一甩的,顯得很得意。
他微微垂眸,看著幾節白皙的手指掐在自己深的袖上,莫名覺得歡喜。
馬冰才剛洗了手,只在空中甩了幾下,并未干。此時便有幾滴水珠順著指紋落,很快在袖上暈染出更深一層的水漬。
那水漬迅速擴散,沿著布料紋理向上攀爬,謝鈺看著,就仿佛覺到某種讓他快樂的緒,也一并順著攀援而上,慢慢沁口。
天氣很熱,汗水黏在上并不舒服,但謝鈺卻不住翹起角,仿佛連撲面而來的熱風中都帶了雀躍。
馬冰說得沒錯,那先熏后烤的確實很味,實的質越嚼越香。
“很好吃吧?”馬冰又去煮了一壺酸梅湯,里面加了烏梅、桂花和山楂干,用硝石快速降溫,夏日喝起來就很舒服。
謝鈺點頭。
確實很香,但他卻覺得自己的一大半心思都不在那上面。
大約只要是此此景,什麼都不會太難吃。
“哇,你們竟然背著我開小灶!”
一大汗的元培從外面趕回來,大老遠就開始喊。
結果剛一靠近,他的臉直接綠了,立刻抱著頭發出痛苦的哀嚎:
“怎麼又是!”
他現在打個嗝兒都是味兒,覺自己都快被腌漬味了!
話雖如此,但見馬冰和謝鈺吃得香,他砸吧下兒,還是很誠實地加了。
“咦?這個口和味道都很獨特呀!”元培又開心了,然而一抬頭,“哎,大人您臉不大好啊。”
謝鈺拉著臉不做聲。
“大人?”邱安在院門外探討一瞧,“啊,正好在。”
謝鈺瞥了元培一眼,后者擎著半拉翅膀站起來,含糊不清地問:“吃嗎?”
謝鈺:“……”
干脆這次就不帶他回去了吧?
“趙老太家的熏嗎?確實好吃,不過今天算了,”邱安笑著擺手,難掩興道,“大人,包袱找到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