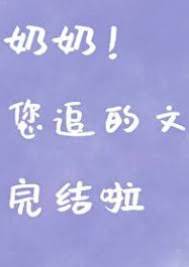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偷風不偷月》 第99章 第 99 章
壹號和如云沒了管教,一黑一白著馬尾跑開了。
項明章渾重量依著楚識琛,徹底傾瀉后心緒麻痹,半晌,他打直脊背,睜著一雙幽深無底的眼睛,問:“我嚇到你了嗎?”
楚識琛尚未松開懷抱,搖了搖頭:“沒有,那我安到你了嗎?”
項明章一剎那活過來,沉郁的臉漫上一點縹緲笑意,他也說沒有,說著傾向楚識琛,還要再擁抱片刻。
楚識琛狡黠地向后一閃,倒退著走,項明章撲了空,過刺激的男人,變了稚又虔誠的困,目不轉睛地跟著主人。
漸漸退到一片連綿的草坡,楚識琛腳下不平,垂眸的瞬間項明章迫近他,用骨子里的侵略和征服將他牢牢抓住。
兩相撞,一起失去了平衡,項明章抱著楚識琛摔在草地上一滾,連大的下擺都互相糾纏。
他們氣吁吁地松開,不計形象、不管臟凈地躺在草坡上。
許久,呼吸平復,周遭靜下來,項明章問:“在想什麼?”
楚識琛說:“想你八歲是什麼樣子。”
項明章自己都沒印象了,只記得個子很高,他從小就比同齡人高一頭。
假如年意味著天真快樂,那項明章的年短暫到可以忽略不計。他不怎麼說話,課業忙碌,每天練習書法和鋼琴,還要參加各種育運。
“我小時候特別攀比。”項明章回憶道,“和項如綱、項如緒比,和姑姑家的表姐比,和那些董事家的孩子比。”
楚識琛揣測:“因為項行昭?”
項明章分析當時的心理,說:“我知道他偏我的原因,我既嫌惡心,又拼命讓自己襯得起這份偏。”
年的他大概是害怕的,怕旁人說他不配,從而發現不可告人的真相。
Advertisement
楚識琛想起項家人酸溜溜的夸贊,說項明章是最像項行昭的,這份“相似”之中,偽裝占了幾分?
他問:“項行昭在照著他自己培養你?”
“是我在主為他。”項明章無法否認地說,“項行昭是個狡猾的老匹夫,我真的像他,他才會信任。我也只有像他一樣,才能取代他。”
項明章念小學后,每年寒暑假項行昭會帶他去項樾,從一天到三天,再到一整個工作周,他被允許自由進出任何部門。
中學的時候,項行昭讓項明章參與公司的項目,一開始是言傳教,明面上的企業運作,背地里的馭人之道,商場策略,商人心機,項行昭都教給了項明章。
后來項行昭就不管了,讓項明章跟著一眾董事和管理去“混”,人敷衍或尊重,得到反對還是擁躉,全憑項明章的本事。
在漫長煎熬的年歲里,項明章揣著不符合年紀的深重心思,一次次通過項行昭的考驗。
十八歲人,項明章正式為項樾的東,甚至有了職位。
大二那年項明章創辦科技公司,項行昭本來是反對的,不允許他的事業重心偏離項樾,為了表忠,他把公司命名為“項樾通信”。
二十多年來,項明章無時無刻不戴著面,欺騙著所有人,要不是恨意骨,他恐怕某一天會神分裂。
在項行昭面前,項明章孝順、聰明、強勢得恰到好。他小時候假裝羨慕別人有父親,長大后假裝思念著項瓏,項行昭被他騙過了,把對項瓏的和愧疚一并投到他上。
直到項行昭中風,變得糊涂,項明章才出對項瓏的不屑,當別人提到白詠緹,他才出冰山一角的憤怒。
項明章的出類拔萃是真,風度翩翩是假,爭強好勝是真,盡忠盡孝是假。
Advertisement
他對瑣事沒什麼耐,因為他嘗夠了忍耐的滋
味,一樁丑事,一個,他可以藏十年,二十年,直到目的達。
經年累月,項明章的能力越來越強,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大。他是項行昭培育的一棵樹,逐漸深葉茂,無人能撼。
更重要的是,大樹才能遮風擋雨,項明章陸續安頓過去無力保護的人,接手尋找項瓏,在項樾不斷擴大勢力范圍。
祖孫的關系發生逆轉,中風之前項行昭已經放手了很多,項明章從一顆威脅白詠緹的籌碼,變項行昭需要依賴的臂膀。
楚識琛著漫天繁星,腦中閃過項明章親歷的萬千日夜,最終回歸發的原點,他問:“伯母這樣子多久了?”
項明章低沉地說:“搬出靜浦大宅,差不多就這樣了。”
白詠緹曾經是驚弓之鳥,竭力吊著一口氣活著,離開泥沼后,皮囊依舊,卻沒有了神氣。
楚識琛心生惋惜,轉念道:“只要伯母自在舒服,別的不要。”
“你說得沒錯。”項明章嘆息,“縵莊就是避世的地方,躲進來覺得安全,所以不肯出去。”
楚識琛扭過臉,冬季干枯的草葉刺痛了臉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來。”
項明章道:“你說‘縵’是束縛,那我算不算作繭自縛?”
“不。”楚識琛阻止項明章鉆牛角尖,“就算是,你帶我來的第一次開始,你的繭殼就已經破了。”
項明章說:“遇見你之前,我沒想過會帶人來這里。”
好比年沒有天真,項明章青春期也沒有悸,人前做戲人后籌謀,唯獨缺失了喜歡一個人的本能。
楚識琛陳述道:“除了我,沒有別人介你的領地。”
Advertisement
“沒有。”項明章說,“除了你,誰又能把我看穿。”
項明章去楚識琛的手,到了大口袋掉出來的煙包,他撿起來,解開細繩拿出包里的雪茄和火機。
楚識琛翻坐起來,說:“不能直接點火。”
項明章道:“我記得你先咬了一口。”
楚識琛捉住項明章的手腕,傾咬住茄頭,占著,他輕抬眼皮用目示意,不能多不能就咬這個位置。
咬下來吐掉,楚識琛了下薄。
項明章打著火機,躍的一簇火在黑夜里閃爍,楚識琛抬手擋風,腦后是皎皎白月,一張臉映得橙紅。
雪茄點燃了,項明章用力吸/食,有些嗆,吹出白煙寒風倒灌,他躺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
楚識琛問:“味道好嗎?”
項明章說:“太濃了。”
“羅歐與朱麗葉不是最濃的。”楚識琛道,“應該給你拿一支清淡的。”
項明章修長的手指著雪茄,問:“你喜歡濃的還是淡的?”
楚識琛探籠罩在項明章上方,把送出的雪茄搶下來,還用指尖掃過項明章的掌心給個甜頭,回答:“癮犯了,不挑。”
如云和壹號晃了一圈跑過來,達達馬蹄響在坡下,楚識琛嘬吸一口雪茄,吐息霧,他在夜幕西風里低下頭,將余存的一縷薄煙渡進項明章的口中。
項明章摟住他,翻一滾沾了滿背細草,他們共一支解憂的羅歐與朱麗葉,頂著同一片浩瀚蒼穹,至渾冷。
已是三更半夜,送倦馬歸廄,項明章和楚識琛去南區睡覺。
縵莊實在太大,走得人,楚識琛騎馬耗了力氣,腳步漸漸拖沓。
項明章停下來等了兩三次,單膝下蹲,說:“我背你。”
Advertisement
今夜誰都不輕松,楚識琛道:“不用。”
項明章說:“等你走到別墅,天都亮了。”
楚識琛憊懶地玩笑:“那我們看日出。”
項明章不廢話了,擒拿似的把楚識琛拽到背上,順勢起,勾住大一顛就背穩了。
楚識琛束手無策,手環項明章的脖子。他只有年時被管家背過,一路晃悠著小,到家發現丟了一只小皮鞋。
母親訓斥他,說他不穩重,他難過得哭了,父親又來說,確實不夠穩重,男子漢怎麼能掉眼淚。
如今回想,那點小事微不足道,楚識琛側對項明章的耳鬢,問:“你哭過嗎?”
項明章沒反應過來:“什麼?”
楚識琛說:“這麼多年你哭過嗎?”
項明章回答:“沒有。”
楚識琛慨:“真是堅強。”
項明章掐他的大,脆弱退去,恢復了平時的霸道:“別用先輩的語氣跟我說話。”
楚識琛半路睡著了,項明章背著他走到別墅,不忍醒他,把他輕輕放在床上,只掉了弄臟的大。
項明章退到外間關上門,了無睡意,終究惦念著白詠緹的狀況。
他掏出手機撥通,剛響兩聲就接了,北區的座機電話永遠是青姐負責接聽,他直接問:“我媽怎麼樣?”
耳邊傳來白詠緹的聲音:“我沒事。”
項明章沉默下來,良久,說:“媽,怎麼還沒休息?”
“等下就睡了。”白詠緹道,“明早和識琛過來吃早餐,我讓青姐煮了姜湯。”
項明章問:“為什麼要喝姜湯?”
白詠緹說:“馬場躺了半宿,我怕你們著涼。”
項明章攥著手機,不能想象白詠緹放心不下地追出來,遠遠躲在馬場周圍著他的表。
他妥協了,說:“我會告訴楚太太——”
然而白詠緹打斷他:“我太久沒出門,一定落伍了。”
項明章愣道:“媽……”
白詠緹的語氣那麼輕,做的決定卻比千斤重:“就告訴楚太太,勞關照,我答應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04 章

最愛你的那十年
從來吵著要走的人,都是在最後一個人悶頭彎腰拾掇起碎了一地的瓷碗。而真正想離開的時候,僅僅只是挑了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門,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賀知書于蔣文旭來說是空氣是水,任性揮霍起來時尚不覺得可惜,可當有一天當真失去的時候才悔之晚矣。 “你所到之處,是我不得不思念的海角天涯。” BE 虐 慎入 現代 先虐受後虐攻 情深不壽 絕癥 玩野了心的渣攻&溫和冷清的受
13.1萬字8 13339 -
完結68 章

軟刃
言微靜悄悄嫁給了城中首富秦懷鶴。 她很低調,懷著秦懷鶴的孩子,為他居屋守廳堂,洗手做羹湯,卻換來了他不痛不癢的一句調侃:“她就這樣,言微人輕嘛。” 言微留下一句話,再也沒有回頭。 “他什麼都有,除了心肝肺。” 言微走后,秦懷鶴才知道,她曾經是他的捐贈對象,來找他,不過是為了“報恩”。 從此,一直在云端上行走的秦懷鶴再也看不到如她那般,心藏柔刃披荊斬棘的女人。 秦懷鶴在雨夜里,一把攬住她的腰肢,眸光深幽,“親一下,我把心肝肺掏出來給你看看。” 言微紅唇輕牽,“秦懷鶴,算了。” 友人:“鶴哥,心肝肺還在嗎?” 秦懷鶴:“滾蛋!” 他什麼都有,除了老婆和孩子。 一年后,秦懷鶴端著酒杯斂眸看著臺上神采飛揚的女人,與有榮焉,“我孩子她媽。” 言微明眸善睞,答記者問,“對,我單身。” 會后,他堵住她,眼圈泛了紅,“言總越飛越高了。” 言微輕笑,“人輕自然飛得高,還得多謝秦總當年出手相救。” 秦懷鶴眸子里那層薄冰徹底碎了,欺上她眼尾的淚痣,“你就這麼報恩?我救過你,你卻從未想過回頭救救我。” 秦懷鶴的微博更新一句話: 【吾妻言微,我的心肝肺。】 #深情千疊斷癡心妄想,沒心沒肺解萬種惆悵# #我不只要歲歲平安,還要歲歲有你。# 溫馨提示: 1、不換男主,he。 2、歲歲是寶貝,很重要。
21.7萬字8.09 30399 -
連載1666 章

冥王崽崽三歲半
華國第一家族霍家掌權人收養了個奶團子,古古怪怪,可可愛愛,白天呼呼睡,晚上精神百倍!大家在想這是不是夜貓子轉世投胎?冥崽崽:本崽崽只是在倒時差,畢竟地府居民都是晝伏夜出呢!人間奶爸:我家崽崽想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通靈家族繼承人:要不讓崽崽帶你們地府一日游?提前了解一下死后生活?冥王: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312.4萬字8.18 33834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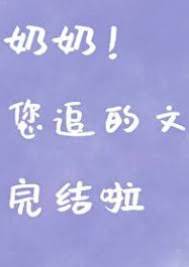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3168 -
完結719 章

封少,你家小祖宗馬甲掉了
注孤生的封二爺有一天對所有人宣布:“爺是有家室的人了,爺的妞性子柔,膽子慫,誰敢惹她不開心,爺就讓他全家不開心。”然後——“這不是拳打華北五大家、腳踩華東黑勢力的那位嗎?”“聽說她還收了一推古武大族子孫當小弟。”“嗬,你們這消息過時了,這位可是身價千億的國際集團XS幕後大佬。”然後所有人都哭了:二爺,我們讀書不算少,你不能這麽騙我們啊。而被迫脫馬的祖盅兒隻想:這狗男人沒法要了,日子沒法過了,老娘要滅世去!
126.9萬字8.18 47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