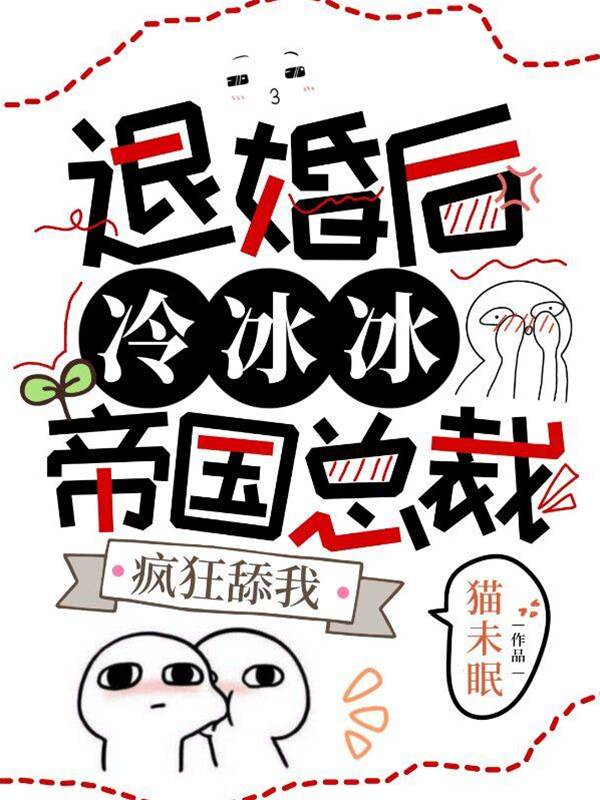《八零之撿漏前任小叔》 第19章 第 19 章
第19章四個男人一臺戲
初挽也沒想到,這個年輕店主竟然是聶南圭。
不過想想也是,在一九八四年,家里就很有些老玩意兒,能把攤子鋪這麼大的,四九城里也沒幾家。
說起聶家的歷史,要追溯到清朝晚年了。
從清末到解放前,古董界值錢的是青銅,那個時候古董玩家講究的是三代青銅,也就是夏商周青銅。
那個時候瓷本沒法和金石比,也就是宋元名窯瓷的價格還能比較高,其它的本比不上,隨便一件商代銅鼎能換一堆正經窯名瓷。
初家祖上是做瓷的,也做玉珠寶,到了初挽太爺爺這一輩,他不甘心默默無聞,便開始做古董生意,開始的時候他做元明清瓷,但是這個發不了什麼財。
發大財的都是金石玩家,他知道這市場行,也開始想青銅這一行。
要學青銅,必須有四書五經的底子,要對夏商周歷史文化了如指掌,太爺爺在這方面也是下了大功夫研究的,總算是了門。
而那時候,靠著青銅發了大財的,頗有幾家,其中一家就是炭兒胡同的聶家。
從聶南圭往上數四代,也就是他祖爺爺那一輩,是前清的翰林,可惜被牽連獲了罪,罷了,但到底是曾經的翰林,結識了一批翰林院的金石學者。
他被罷后,便干脆做了古董商,專搜集了青銅給那些金石學者老翰林。那個時候老翰林金石學家們都喜歡銘文,青銅上有銘文才能賺大錢,這聶家祖爺爺本四書五經底子好,拓了公鼎上的銘文來臨摹篆刻,為仿鑄做偽的大行家,這買賣便經營得如魚得水,了西安知名的大青銅商,也就了“西安造”仿鑄青銅的大名。
Advertisement
本世紀二十年代,西北鎮嵩軍攻打西安,圍城八個月,聶家傾全族之力支持守城將領楊虎城李虎臣,但是這一仗打得艱難,城中絕糧,五萬百姓活活死,十三朝古都遭遇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劫,聶家元氣大傷。
為此,聶家其中的一脈離開西安,遷往北平城,也就是聶南圭這一支。聶南圭太爺爺道行深,在四九城站穩了腳跟,儼然為經營青銅的大戶,甚至做到了北京古玩商會副會長的位置。
自己太爺爺早年為了增進見識,四淘換銘文拓本,曾經和西安城聶家一位子孫結,花了重金求得散氏盤和公鼎銘文,誰知道那位聶家子孫就是一吊兒郎當公子哥,自己太爺爺五百銀元求了一些篡改的假銘文,引以為恥,從此不喜聶家,到了聶家遷至北平,雙方彼此忌憚,面和心不和。
之后,聶家購得一大批青銅,以為是正經商代青銅,花了大價錢,其實那是“蘇州造”,是當年鑄銅名匠周梅谷的作品。太爺爺和周梅谷有些,知道這批所謂“商代青銅”的來歷,不過他自然不吭不響,聶南圭太爺爺因為這個打了眼。
后來日本侵華,他們從天津運往九江口的一大批貨,船到了錢塘灣,被日本駐杭州灣海軍劫走,花錢托人索要兩年未果,那麼一大批青銅就這麼便宜了日本人,聶家再無能力購置底貨。
好不容易日本投降了,東民巷花旗銀行庫房案一聲炸雷,幾家大古董商遭劫,這次不各家損失慘重,更是折損了親人數條命,初挽姑,聶家三爺,并當時法國大古董商盧芹齋義子,都牽連其中。
這搶劫案名震京津冀,撲朔迷離,聶家推斷太爺爺的九龍杯引來災禍,太爺爺卻覺是聶家三爺里應外合招惹是非引火燒,雙方由此再不顧同行之誼,互相怨恨。
Advertisement
想起昔日恩怨仇,初挽也是笑嘆一聲。
在之后的許多年里,初挽和聶南圭幾次棋逢對手,因為祖輩舊怨,也因為彼此咽不下那口氣。
但是以后的聶家,終究再不復往日的輝煌,此一時彼一時,青銅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致華的小小鼻煙壺瓷,遠比搬運那笨重的青銅省心,任憑你是夏商周稀世珍寶,在古董玩家眼里,也不如一件宣德青花瓷來得有趣。
而瓷,是初家的老本行。
今天自己能在聶南圭手底下奪得明朝大開門青花瓷并全而退,原因有二,一則自己沾了重活一世的便宜,這聶南圭如今到底青了一些,自然吃了虧;二則,也是聶家在瓷上,到底欠了火候,沒有初家的家學淵源深厚。
想到這里,初挽出手,了自己帆布包中的五顆玉珠,將那顆漢代黃玉珠拿出來,下,卻見那玉珠和如脂,細膩滋潤,澤濃郁猶如蠟,這樣的玉珠,實在是罕見。
仔細打量了一番,那黃玉珠上還有一個小孔,小孔穿得非常規整,兩頭還導出一個小引弧,這種做工,實在是罕見。
這顯然是朝珠的珠頭。
朝珠是清朝員上朝的披掛,按照品階不同,也各有不同。民國初年,清政府沒了,古玩市場上便流出大量朝珠,這些朝珠五花八門,價格不一,舊時人家箱子底有些朝珠,魚龍混雜和普通玉珠摻和在一起,倒是不稀罕。
不過眼下這一個,和田黃玉珠,在那時候也只有一個人能用了,那就是皇帝。按照歷史上的記載,這朝珠應該是乾隆皇帝祭祀地壇專用的了。
這可就又比普通的黃玉珠更添了許多價值,雖只有一顆,但也不容小覷。
Advertisement
按照初挽的評估,十年之后,炒作一番,二百萬估計也是有戲。
旁邊蘇鴻燕見了,好奇:“你這個珠子好看,像是炒的小黃栗子。”
初挽笑了笑,隨意用拇指挲著,之后漫不經心地放在帆布袋中:“是好看,留著玩吧。”
心里想著,這聶南圭若是知道,自己就在他眼皮底下,得了青花瓷蓋罐,還得了這麼一粒乾隆用朝珠,估計能氣死。
反正不管因為什麼原因,和聶南圭的第一次手,完勝了。
初挽又想起那聶老頭,那人的眼才毒辣,今天也是多虧了他不在,才自己討了這麼一個大便宜。
這時,蘇鴻燕小心地抱著幾個瓶瓶罐罐,自然是寶貝得很,又有些得意,覺得自己“撿到了”。
陸建昭:“按說就算清朝仿的,青花瓷的,清朝的青花瓷也值錢!”
初挽將自己的五顆珠子收好了,這才慢吞吞地道:“清朝仿元青花瓷,一百五十塊還是可以的。”
蘇鴻燕激:“那就是了,撿著了!”
初挽卻問:“不過就剛才那小店主,那明樣兒,你從他手里撿,你覺得可能嗎?”
蘇鴻燕一想也對,不過很快道:“那不是你厲害嘛!”
初挽:“我再厲害,也不至于從人家手里討便宜,沒好的事,人家不干的。”
陸建昭聽得蹙眉:“挽挽,什麼意思?”
初挽:“這雖然是清朝仿元的,但是民國掛的彩,掛彩的活兒做得不行,價錢大打折扣了。”
蘇鴻燕:“啊?”
陸建昭詫異:“那值多錢啊?”
初挽想了想:“十幾塊錢吧?”
蘇鴻燕一口氣差點沒上來:“什麼?”
陸建昭也懵了,瞪眼睛:“挽挽,這是什麼意思?十幾塊的東西,咱花一百五買?這不是給人送錢嗎?”
Advertisement
初挽:“別急,咱們走僻靜地兒慢慢說。手里東西你們拿牢了,別摔了。”
這一提醒,蘇鴻燕趕抱了。
當下一行人走到了一僻靜墻底下,初挽讓蘇鴻燕打開包袱,拿出來那蓋罐,用包袱皮了,才道:“我讓你買,醉翁之意不在酒,買的不是那民國掛彩的打眼貨,而是這個——”
這一說,兩個人都詫異了,打量著這其貌不揚的玩意兒:“這不就一破蓋罐嗎?這都有裂紋了!”
初挽嘆:“這可是開門貨,明正統青花瓷蓋罐。”
蘇鴻燕一聽,眼睛都瞪大了,自然知道明青花瓷意味著什麼,那是明朝青花瓷最鼎盛的時候,全世界都認明青花瓷!
如果真是明青花瓷,這就不是一百塊兩百塊的了,這必須得大幾百,甚至上千!
初挽用包袱仔細了,最后指著底下:“瞧,景德鎮窯廠燒的,假不了。”
蘇鴻燕倒吸一口氣:“這,這如果是真的,咱賺大發了!”
初挽點頭:“把心放肚子里吧,真的。”
陸建昭回憶著剛才種種,突然間一拍大:“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買這個,對方以為糊弄住你了,以為你看走了眼,想把這個掛彩的當正經清朝仿的賣給咱們,他一心惦記著想沾咱們這個便宜,結果你利用他的求心態,順手讓他把這個蓋罐搭給咱們了!”
初挽:“對。”
蘇鴻燕想起剛才種種,自己還在那里急赤白咧地想著急買那個后掛彩的瓶子,還生怕這件事鬧黃了,沒想到人家初挽早盯上了青花瓷蓋罐!
喃喃地道:“我犯傻了,是我犯傻了。”
初挽卻道:“這就是你的妙啊,就是你急切想要的那勁兒,那是一般人想演都演不出來的棒槌相,所以他才大意了,如果沒有你,就我一個人去,這事絕對不了。”
棒槌是古玩行的行話,意思是敗家,傻子,不懂還要買。
蘇鴻燕呆了呆:“意思是我就是一個起哄架秧子的?”
初挽點頭:“差不多,你不可或缺。”
陸建昭聽著,再次恍然:“所以你當時不是真生氣?就是故意拿樣子,趁機要求搭上這件!我還說呢,怎麼突然這麼大火氣,都要和人吵起來了!”
初挽:“對,蘇姐姐不懂行著急想要,我被你催得了分寸,不及細想只能買,但是討價還價不舒坦,下不來臺,要面子,這個時候才可以賴著要他搭一個小的。不然無緣無故提起那蓋罐,他必生疑心,或者我們兩個都是行,他也得起疑了。”
就聶南圭的明,但凡這過程他起了謹慎之心,就別想從他手里拿走這青花瓷蓋罐了。
蘇鴻燕打量著那青花瓷蓋罐,愣了半晌,最后喃喃地說:“這就是傳說中的高手過招嗎?”
初挽:“這才哪兒到哪兒,就隨便玩玩吧。”
蘇鴻燕看著初挽:“這,這確實是青花瓷嗎?”
初挽不想解釋這個:“你回去讓你爸仔細研究研究就是了,反正一百五十塊,買不了吃虧,萬一你后悔了,不想要了,行,給我,看在你今天當棒槌演戲的份上,我二百塊收。”
蘇鴻燕忙道:“那不至于,不至于……不過你費了那麼大的勁,我,我是不是得分你點?”
初挽:“不用了,我也沒興趣,你自己留著玩吧。”
蘇鴻燕呆呆地看著初挽,一時不知道說什麼。
初挽看著也就一高中生的樣子,年輕又單純,結果……
明朝青花瓷,被一說就是“留著玩”??
初挽:“再說我也沒吃虧,我那不是隨手買了幾粒珠子嘛。”
如果不是有那件后掛彩的瓶子打掩護,要想從聶南圭眼底下拿到這黃玉珠,未必就能,就算了,那代價也不小,所以這也算是自己得到的回報了。
一點不虧。
*******
蘇鴻燕抱著罐子瓶子高高興興地走了,陸建昭再看初挽,那眼神就完全不一樣了,那就是敬佩得不行了,像是拜神仙一樣的眼神了。
以至于上公車的時候,陸建昭從旁竟然出手要虛扶著,那一臉的恭敬殷勤,簡直沒眼看。
初挽看著,有些無奈,不過也有些悉,這是悉的后來的陸建昭嘛,其實人不錯,在收藏之道上對言聽計從,拍收藏類電影的時候還請做技指導。
猜你喜歡
-
完結66 章

他只對她溫柔
你已經是我心臟的一部分了,因爲借走的是糖,還回的是心。—— 宮崎駿 文案1: 請把你的心給我。—— 藍晚清 當我發現自己愛上你的時候,我已經無法自拔。 —— 溫斯琛 愛上藍晚清之前,溫斯琛清心寡欲三十年,不嗜賭,不.好.色。 愛上藍晚清之後,溫斯琛欲壑難填每一天,賭她情,好.她.色。 文案2: 在T大,提起生物系的溫教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姓溫,但人卻一點溫度都沒有,高冷,不近人情,拒人千里。 但因爲長得帥,還是不少美少女貪念他的美色而選修他的課,只是教訓慘烈,一到期末,哀嚎遍野。 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溫教授?適合遠觀,不適合褻玩。 然後,學校貼吧一個帖子火了,「溫教授性子冷成這樣,做他女朋友得有多慘?」 底下附和聲一片—— 不久,學校貼吧另一個帖子也火了,「以前說心疼溫教授女朋友的人,臉疼嗎?」 底下一溜煙兒的——「疼!特碼的太疼了!」
19.7萬字8 16870 -
完結453 章

閃婚禁欲保鏢野又撩!好心動上頭
【驕矜明豔大小姐VS冷酷禁欲係保鏢】【閃婚 先婚後愛 追妻火葬場 雙潔】傅西洲缺席訂婚禮那天,司棠棠成為了全城笑柄。她宣布取消婚約,轉身上了顧硯深的床。顧硯深是她保鏢,冷酷禁欲、不近女色,一向厭惡女人占他便宜。清醒後,她準備給他一筆錢當作補償,男人卻強勢求婚:“大小姐,嫁給我,以後我護你周全!”本以為隻是一場協議婚姻,沒想到婚後他卻寵妻成狂,撩她、勾她又纏她。-失去司棠棠後,傅西洲後悔了,想要重新追回她。告白那晚,他看到她被男人摟進懷裏:“大小姐,親一下。”“顧硯深,收斂一點。”男人低聲誘哄:“乖,叫老公。”“老公~”傅西洲目眥欲裂,上前質問她為什麼嫁給一個保鏢?當天晚上,傅家就接連損失了好幾個大項目。-傳聞,A國總統府的太子爺低調又神秘。司棠棠拿到國際影後大獎那天,受邀到總統府參加宴會。她不小心看到了一幅油畫。女人膚白貌美,天生尤物。那不正是她嗎?油畫下寫著一行小字:暗戀不敢聲張,思念爬滿心牆。“大小姐,你看到了?”男人走過來,將她從身後擁住。她心慌意亂,不知所措。“顧硯深,我們說好的,隻是協議夫妻。”男人俯身下來,親得她眼尾泛紅,“大小姐,愛我好不好?”#蓄謀已久##男主暗戀成真#
86.3萬字8.18 97876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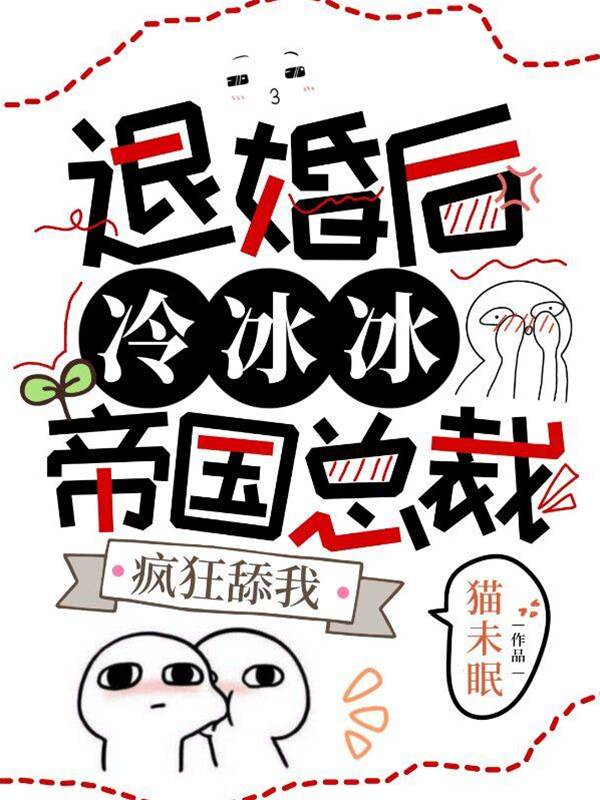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6470 -
完結250 章

錯撩後,總裁失控
父母雙亡後,蕭桐羽被寄養在從小有婚約的林家。高中畢業那一天,她看到暗戀多年的林家少爺和校花翻雲覆雨,果斷轉身離開。大學畢業後,爲了小小的報復心,蕭桐羽進入季氏,成爲了帝都首富季允澤的貼身祕書。季允澤是帝都最高不可攀,令人聞風喪膽的黃金單身漢。撩人成功那晚,蕭桐羽後悔了,她哭着求饒,季允澤卻沒有放過她。“一百萬給你,買避孕藥還是打胎,自己選。”“謝謝季總。”後來,季允澤撕爛了蕭桐羽的辭職信。“你敢跨出這個門一步,我讓你在帝都生不如死。”再後來,季允澤被人拍到蹲在地上給蕭桐羽繫鞋帶,大雨淋溼了他的身子。“季總,這熱搜要不要撤下來?”“砸錢讓它掛着,掛到她同意嫁給我爲止。”
47.2萬字8.33 1082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