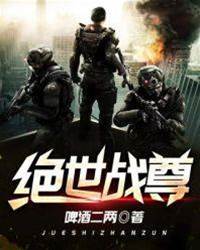《山野小神醫》 第42章 老子要你一條腿
「前幾天晚上,是哪個狗日的帶了三車人去黑龍潭村點我家房子的?」方奇說這話時,兩眼死死盯著「小霸王」張波。
張波角搐了下,歪著皮笑不笑,慢條斯理道:「呵呵,原來那是你家房子,你得罪什麼人,知道吧?」
方奇兩眼充腦瓜皮一陣陣發,抄起桌子上的酒瓶子就扔過去。
這張波原來也不含糊腦袋瓜子一偏,「嘩啦啦」酒瓶子就在地上摔的碎。
那小太妹尖著跑出去,鎚子還勸呢:「蹄子哥……別手,有話好好說。」
被方奇拔拉到一邊:「特麼給我死開!」
其餘幾個混混跳開,拎起椅子要開干。
張波歪歪頭,把脖子擰的嘎吧嘎吧直響,這貨倒淡定的很,歪歪:「用不著你們,我來收拾他!」
那幫子混混呼呼啦啦全出去,還把門帶上。
方奇看看這貨裝,冷聲道:「張波,你老了!乾脆我給你改個名字,老王八!」
「小霸王」張波面對方奇辱,竟然沒氣,只是臉更加沉,全突起,那是隨時應戰的節奏。
方奇搖搖手指頭,擺出絕對的樣,嘬著牙花子嘖嘖有聲,一字一頓道:「沒-用-的,老子要你一條!」
張波桀桀怪笑,突然彈起一條綳的滿桌子上的杯盤一齊砸向方奇。
Advertisement
方奇一挫抬綳在桌子上,一時間屋子裏盤子碗飛,桌椅砸的嘎嘎直響。
張波是老牌混混,天天過著刀頭的日子,靠打架鬥毆吃飽的,自然有兩下子。
可是現在的方奇有三下子四下子,比他還牛比他還橫,這三個手指頭田螺——吃定它了。
倆人懟上拳腳,張波才覺得自己力有不逮,本不是一個量級的,眼見方奇出拳頭如電自己都沒能看清楚。
幾拳頭落在臉上,張波頓覺腦子嗡嗡直響,跟鑽進幾百隻蜂似的。趕雙臂護住頭部,一挫蹲下,看起來他好像要落敗似的,右手出其不意地從小彎里拔出刮刀,單手往外一遞扎過去。
那刀扎過來時,方奇左抬膝猛頂張波的下頜,尖刀從左大邊刺過去他卻渾然不覺。
但這一膝蓋頂上張波的下頦兒,張波腦袋又撞向牆壁,「咚」地聲悶響,便再也支撐不住挨著牆壁倒下去。
方奇彎腰拉起他他右鋪在倒在地上的椅子背上,鉚足力氣抬腳跺下去。
張波「嗷」地聲慘,聲窗子玻璃「喀啦啦」直響。
站在外面的幾個混混聽這靜直覺得骨悚然,一個個臉如土面帶驚懼,鎚子魂都嚇飛了,結結說:「霸……霸哥,這聲音,是……是,是霸哥……」
Advertisement
那小太妹蹲在牆邊瑟瑟發抖,一把鼻涕一把淚,臉上妝彩抹的跟鬼畫符般難看。
這幾人正抖著不知道咋辦才好,就見房間門一響,方奇從裏面走出來,跟剛打扮完似的一邊整理服,一邊撣著服上濺的菜。
那幾個混混靠著牆站一溜兒,鎚子站在門口另一邊,方奇牛不牛狠不狠他最清楚,高一的時候沒挨揍,當年去找小霸王張波給他撐腰,連張波都不願意出頭。
方奇扭臉看鎚子直靠牆站著,氣定神閑地問:「你有沒有去?」
「沒……沒,他們,他不帶我。」鎚子結結回道。
方奇又來到門那邊找個塊狀最大最壯的,「啪啪」拍打他的臉:「你點我家房子了?」
那小子咧的跟開口的荷包蛋似的:「蹄,蹄子,哥,他們,他們著……」
話說沒說完,就挨了七八個大子,只覺得下面一熱,一泡搔哄哄的尿從大衩順著大一直流下去。
方奇挨個兒子,頭挨了幾個一屁坐在地上號淘大哭:「蹄子哥,我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的,要不打死我也不敢啊。」
站他旁邊的板寸頭撲通一下跪在地上,其餘幾個一看也紛紛跪下,跟磕頭蟲似的腦殼撞的地板咚咚直響。
走到那小太妹跟前,看嚇那樣,「呸」了濃痰:「不上路的東西!」
Advertisement
抖抖被染紅沾在上的子,問鎚子:「明兒個你去城東的老鬼修車鋪,把電話號碼給老鬼,你隨隨到!」
鎚子磕頭如搗蒜,連連應聲。
方奇環顧了下二樓,心裏還納悶兒,剛才還熱鬧的,這會兒咋就沒人哩。
下樓時就瞧見下面圍了一圈子人議論紛紛,見他下來跟看見個大章魚似的一齊住看著他,自給他閃開一條道。
方奇面帶微笑走過去,心裏舒爽無比,現在就差周然一條了,老子不弄斷一條,還要丫的給老子蓋上四間大瓦房,你真當老子的方家府邸是你的燒烤柴火?!
忽然後有人:「這位……壯士留步!」
方奇差點兒笑噴,回過頭來,見是個四十多歲有威嚴的中年人:「你開的是龍門客棧?」
圍觀的吃瓜群眾都憋不住低聲「吃吃」笑,心說這老闆是個逗,小伙也真是逗的不行。
「咳咳,」老闆臉尷尬,「請問您貴姓?」見方奇面不善,忙從口袋裏掏出張名片雙手遞過來,「哦,是這樣,這是張貴賓卡,您來吃飯可以隨時免單。」
方奇翻看著的金卡片,眼不經意地往二樓暗的人影子瞄了眼,收起名片:「!」轉往外走。
他不傻,在這麼高檔的酒樓打架人家沒報警,還給他免單,用腳趾頭都能想出來是咋回事。
Advertisement
出來時,就見那個大禿瓢還拉著葛昭昭得得說個沒完,也不知道在說啥子。
公證的人已經走了,趙三剛正蹲在地上煙,看見方奇出來埋怨道:「我尋思你掉茅坑裏呢,咋撒個尿恁長時間,屙屎了?」方奇漫應著掏出手機,還以為多長時間呢,從進廁所到出來十分鐘都沒要。
大禿瓢瞅見方奇出來,也不好再跟葛昭昭嘮纏,揮揮手鑽進小汽車一溜煙開走了。
方奇走到葛昭昭面前,迎著路燈,葛昭昭一眼瞅見他上的,訝然道:「你怎麼流了?」。
猜你喜歡
-
連載18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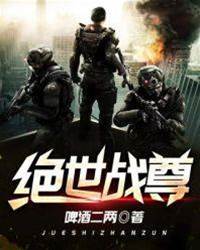
絕世戰尊
“給我查,我丈夫究竟是什麼身份?”“小……小姐,他……他的身份不得了……”洛天,昆侖殿至尊龍帥。五年間,你為我飽受屈辱。如今我榮耀歸山,血染半邊天。往后余生,我定讓你萬丈光芒!…
337萬字8 55762 -
連載3256 章

神算小村醫
神算小村醫村花:林飛,你不是神算子嗎?算算我啥時候嫁給你村醫:嗯……上卦乾,下卦巽,天風姤卦,女壯男衰,不好意思,你命中缺我。寡婦:神醫,也給俺算一卦。村醫:上卦坤,下卦…
612.1萬字8 22620 -
完結732 章

我的姐姐是大明星
某年某月某天,禍水姐姐忽然說:「我要做明星」 秦澤淡定道:「老姐,你想被老爹活活打死,我不反對」 禍水姐姐義正言辭:「秦澤,姐姐照顧你這麼多年,這個鍋,你必須背」 這是一個姐姐不斷坑弟弟的故事。 秦澤:「媽蛋,還好我有系統」 ...
184萬字8 11656 -
連載728 章

神話紀元,我進化成了恆星級巨獸
蒼穹之上,數千米長的鯤從城市上空飛過,無視漫天導彈轟炸,震撼世界。 有長達千米的滅世巨蟒摧毀城市,吞噬百萬人,在數顆核彈爆炸下緩緩離去,全球失聲。 來到這個危險世界,意外獲得一個蠑螈分身的江左迷茫了。 巴掌大小的六角蠑螈能做什麼?拍視頻賺流量?去小溪抓蝦米?還是……進化成巨獸?繁華城市中,一頭別名六角龍,擁有無限進化能力的六角蠑螈,漸漸朝著神話傳說的滅世巨獸進化。 體長十米,百米,千米……並且在同步強化的特性下,江左的本體也在變強,力量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快,甚至……
305萬字8.18 1494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