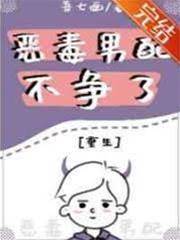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快穿之我是女主死對頭》 第50章 年代文里的小可憐化繭成蝶(49)
李風鈴又把自己寫好的稿子前前后后看了兩遍,確定里面沒有錯別字和不通順的語句以后才把信紙折整齊,放進信封里。
然后又從空間里面找出來一張最不喜歡的郵票好,才把信收進空間里,準備明天去放學的時候去郵局把信投進郵筒里面。
這里面李風鈴時不時的就會去郵局買一些郵票回來,反正能在樹林鎮收集到的郵票全都收集齊了,郵局里的胖阿姨每次看到李風鈴去都是笑的見牙不見眼的。
在胖阿姨眼里,李風鈴可是的財神爺,平時幫李風鈴收集郵票,可沒從李風鈴這里得好。
而且可是聽說了,這個經常來這買郵票的小姑娘,爺爺可是退下來的老首長,人脈多著呢,肯定得討好著,萬一有一天有事需要求到人家頭上呢?
而李風鈴覺得胖阿姨的這種做法無可厚非,是人的本,并不討厭,反而是經常給收集到一些不常見的郵票,對的幫助也不小。
一開始李風鈴收集郵票只是為了能給自己以后多攢一些家底兒,但是時間長了,每天看著各種各樣的郵票,李風鈴就開始發自心的喜歡了。
發現其實每一張小小的郵票里面都有許多的意義,越看越覺得有意思,而且李風鈴每次看到自己收集到的滿滿一大本郵票,都覺得心里有一種驕傲油然而生。
到了學校,依然是認真的學習,即使現在學習的東西早就已經掌握了,李風鈴依舊珍惜在這個年代里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
李風鈴覺得的心態和以前看的各種小說里穿越主的心態完全不一樣,從來不覺得從發達的后世來就應該用一種蔑視的眼看待現在的人。
Advertisement
人人平等,沒有誰就應該為世界的中心,哪怕李風鈴現在氣運已經回歸,重新為這個世界的氣運主也不行。
沒錯,是來做任務的,是帶著原主的仇恨來的,包括自己,心里的仇恨也一刻都不曾忘記。
但是報仇并不是胡的攪風攪雨的理由,有仇報仇,有怨報怨,誰害了你就去找誰,不會平白無故的牽連別人。
所以李風鈴來了以后不管是對沐家人還是二賴子李寡婦,甚至是后來想要找麻煩的虎哥一行人,李風鈴下手都狠的,沒給他們留一點兒的活路。
因為那是他們自己欠下的債,現在到了還債的時候了,但是一人做事一人當,李風鈴從未想過波及到別人。
同樣的,如果有一天李風鈴真的回到了的前世,他要報復的是把推進火坑里的人,而不是帶著仇恨回去毀滅世界的,世界又不欠他的。
和李爺爺李生活的這里面,讓李風鈴到了,這個世界里的人和原來的世界沒有什麼區別,都是有有的,所以在不同世界生活的每一天。
努力做到熱生活,但是絕不做圣母,為一個敢敢恨得俠客就好。
現在這個時間,社會都還著呢,所以學校里每天上課的時間并不長,下午就上兩節課就可以放學回家了。
放學了,李風鈴心里一直記掛著投稿的事,所以鈴聲一響,李風鈴就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書包,竄出了教室,騎著自行車直奔郵局而去。
把信扔進郵筒里以后,李風鈴又照例去見了胖阿姨,今天的運氣準時不錯,胖阿姨竟然又給收集到了兩張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的郵票。
李風鈴爽快的給了錢,開開心心的拿著郵票就離開了,想要趕快回家,然后把這兩張郵票在自己的集郵冊上,是想想就心頭火熱。
Advertisement
時間過的很快,轉眼間一個多星期就過去了,正好是周末,上午,不怎麼有外人顧的柳樹村迎來了兩位特別的客人。
這兩位客人分別是縣報社的記者劉巖和市報社的記者方天,兩人是都二十多歲的大小伙子,騎著自行車,一路風塵仆仆的來到了柳樹村。
現在正是秋收的季節,凡是能彈的全都下地干活去了,那些不能下地得也都就在家里忙活家務。
所以劉巖和方天進了村一個人都沒見到,最后還是在一棵大愧樹下面看到幾個正在玩耍得小孩,劉巖從口袋里面掏出來幾塊水果糖分給孩子們,打發他們去了大隊長回來。
有糖可以吃,孩子們拿了糖,就算都呼呼啦啦得朝著地里跑去,都想第一個找到大隊長。
一群孩子也說不清楚,就只是告訴王浩仁有兩個穿的特別整齊,還騎著自行車的哥哥來了村里,要找大隊長,現在正在大槐樹下面等著呢。
王浩仁一聽,還以為是公社里的領導來柳樹村視察來了呢,趕放下鐮刀,用搭在脖子上的巾在臉上胡的了兩下汗,就急急忙忙的往大槐樹的方向跑去。
生怕去晚了,讓公社的領導等著急了,再以為他這是不歡迎領導視察,消極怠工,到年底影響大隊評先進就不得了了。
王浩仁快要到大槐樹下的時候,趕停下來,深呼吸了幾下,讓自己的呼吸平穩下來,又使勁兒在自己的上拍了拍,拽了拽沾滿土和草屑的裳,自己覺沒有那麼邋遢了以后,才快步朝著劉巖和方天走去。
待到近前一看,王浩仁就愣住了,他本就不認識自己眼前的這兩個人,公社的大小領導,他當了這麼多年的大隊長,全都認識,但是這兩個年輕人卻是眼生的很,難不是公社新來的干事?王浩仁在心里這樣想著。
Advertisement
不過不管對方是不是公社的領導,從他們的穿著,以及邊停著的兩輛七新的自行車,王浩仁就知道他們的份不簡單,不是他這個大隊長可以得罪的。
也不是說他這個軍人出的大隊長就是一個趨炎附勢的迷,實在是他也沒有辦法啊,柳樹村這麼窮,每年冬天都得靠領公社的救濟糧才能沒有人死凍死。
萬一他一不小心得罪了什麼人,而牽連到整個村子就麻煩了,不管是救濟糧,種子化農啥不都得公社分配啊?
而且樹林鎮就那麼大點地方,凡是有頭有臉的人之間都有著千萬縷的聯系,稍微手指頭就能讓整個村子不好過。
為了讓村民過的舒服點,王浩仁這個從軍隊出來的直腸子的漢子也不得不小心謹慎,人前都是一張笑臉。
只是沒人知道大隊長王浩仁的心里那個苦啊,他一個當兵的,啥時候過這種窩囊氣,以前在部隊看誰不順眼,都是干他丫的,現在可好,年紀大了,還得學習場的那一套,他心里怎麼能好?
看到一個材魁梧的大漢朝著他們走過來,劉巖和方天就知道這應該就是柳樹村的大隊長了。
劉巖率先向王浩仁快走了兩步,滿臉笑容的說:“這位同志你好,你就是柳樹生產大隊的大隊長吧?我是咱們縣報社的記者劉巖,我后的那位是市報社的記者方天同志,這次來你們柳樹生產大隊是想了解一些況的。”
劉巖噼里啪啦的一堆話說的王浩仁一頭霧水,他搞不明白記者來他們村子干啥,能了解啥況,難不他們村子又有哪個小兔崽子犯了事兒,把記者都給招來了?
不管自己在心里面怎樣的唧唧歪歪,王浩仁大隊長的表面功夫還是做的很到位的,滿臉堆笑的和兩位記者同志分別握手問好。
Advertisement
嗯,他仔細看過了,一個縣報社,一個市報社,還是記者,他惹不起,那還能咋辦,哄著唄。
“兩位記者同志歡迎歡迎,不知道你們大老遠的來我們大隊是想了解什麼況?”王浩仁心忐忑的把自己想知道的問出了口,只希別像自己想的那樣真的是有什麼不好的事兒。
此時正在自家院子里和李爺爺并排躺在躺椅上曬太的李風鈴連著打了好幾個噴嚏,害的和爺爺都以為要冒了,嚇得李趕給買了一個薄毯子蓋上了。
而事的始作俑者王浩仁大隊長已經滿臉笑的都是褶子的領著兩位記者,朝著大隊部走去了,同時打發一個跟著看熱鬧的村民趕去村尾見李風鈴。
剛才他已經從劉巖和方天這里把況了解清楚了,原來是他們大隊的李風鈴小同志向市報社投了稿,稿子寫的不錯,而且還有很多知識,這次方天來就是向李風鈴了解的那些辦法是不是真的有用的。
還說如果李風鈴同志的稿子里面的容都是真實有效的,那可是能夠造福整個榆林市的好事兒。
聽了兩位記者的解釋以后,王浩仁提起來的一顆心總算是落回了肚子里面,是好事兒就好,這回他們柳樹村也能跟著出名了,說不定到年底公社還能多給派發一些救濟糧呢,那樣孩子們又能多吃幾頓飽飯了。
所以王浩仁才從剛才言不由衷的笑變真心實意的笑,還笑的一臉褶子。
猜你喜歡
-
完結121 章
魔道祖師
前世的魏無羨萬人唾罵,聲名狼藉。 被情同手足的師弟帶人端了老巢, 縱橫一世,死無全屍。 曾掀起腥風血雨的一代魔道祖師,重生成了一個… 腦殘。 還特麼是個人人喊打的斷袖腦殘! 我見諸君多有病,料諸君見我應如是。 但修鬼道不修仙,任你千軍萬馬,十方惡霸,九州奇俠,高嶺之花,<>
0萬字8.18 33101 -
完結459 章
重生香江風雲時代
重生香江,隻為那一抹溫情;步步崛起,隻為那華語凋零;東山再起,隻為了雪恥揚眉;捍衛珍寶,隻為了初心可貴。
86.4萬字8 9187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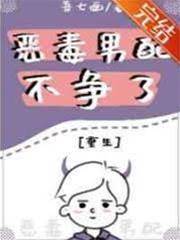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0240 -
完結920 章

盛寵之嫡女醫妃
前世,南宮玥是被自己坑死的。她出生名門,身份尊貴,得當世神醫傾囊相授,一身醫術冠絕天下。她傾儘一切,助他從一介皇子登上帝位,換來的卻是一旨滿門抄斬!她被囚冷宮,隱忍籌謀,最終親手覆滅了他的天下。一朝大仇得報,她含笑而終,卻未想,再睜眼,卻回到了九歲那一年。嫡女重生,這一世,她絕不容任何人欺她、辱她、輕她、踐她!年少溺亡的哥哥,瘋癲早逝的母親,這一世,她必要保他們一生幸福安泰。原以為這一世,她會孤獨終老,冇想到,前世那個弒父殺弟,陰狠毒辣的“殺神”鎮南王卻悄然出現在了她的生命裡。隻是……怎麼畫風好像不太對,說好的冷血陰鬱、心機深沉去哪兒了?
383.4萬字8 40514 -
完結728 章

錦桐
新書《吾家阿囡》開始連載啦! 李桐重生了,也清醒了,原來,他從來沒愛過她惜過她…… 姜煥璋逆天而回,這一回,他要更上一層樓,他要做那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寧遠千里而來:姜煥璋,小爺我專業毀人不倦……
127萬字8 52743 -
完結685 章

嬌嬌那麼乖!傅爺趕緊破戒!
《虐渣、雙重生、男主後上位》餘歌跟傅景辰結婚後,他出軌了,她病了,癌癥晚期,快死了,跟傅景辰離婚後,她獨自死在了冬日裏。傅景辰重生了,回到了青春年少時,那會,他們還很年輕,他們沒結婚,她還活著,他還是想娶她。餘歌重生後見到京城的活閻王,她記得上一世,男人雙腿截肢,一生未娶,膝下無一子,半生淒涼,男人長身玉立,籠罩在暗處,她聽傅景辰提及,都是對他二叔的驚恐之色。她低眉叫了一聲:“傅二叔。”那嗓音軟而糯,如魔音貫耳,那窈窕的身段映入眼簾,眸子微暗。他手戴佛珠,強悍的身軀將她抵在牆角,手指抵在她下巴,微抬,寒眸攝魂:“跟了爺,如何?”餘歌抬頭撞入那雙寒眸,身子發顫,聽到這話,肝膽欲裂,小臉蒼白如紙,滿眼驚駭之色。“二、二叔!”她退後幾步,渾身止不住的發顫,滿眼驚恐之色,對麵前恐怖的男人敬而遠之。那雙寒眸微瞇,隱約有了幾分不悅之色,眼裏滿是侵占:那雙骨節分明的手挑起她的下巴,醇厚的嗓音性感磁性:“怕我?”“爺給你的,你受也得受,不受也得受。”——強大尊貴如傅懷靳也會自卑,因為雙腿的殘疾,不敢擁有她,他瘋魔病態的喜歡著自己的侄媳婦,卻礙於世俗和自身的殘缺,不敢靠近半分
61萬字8.18 1143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