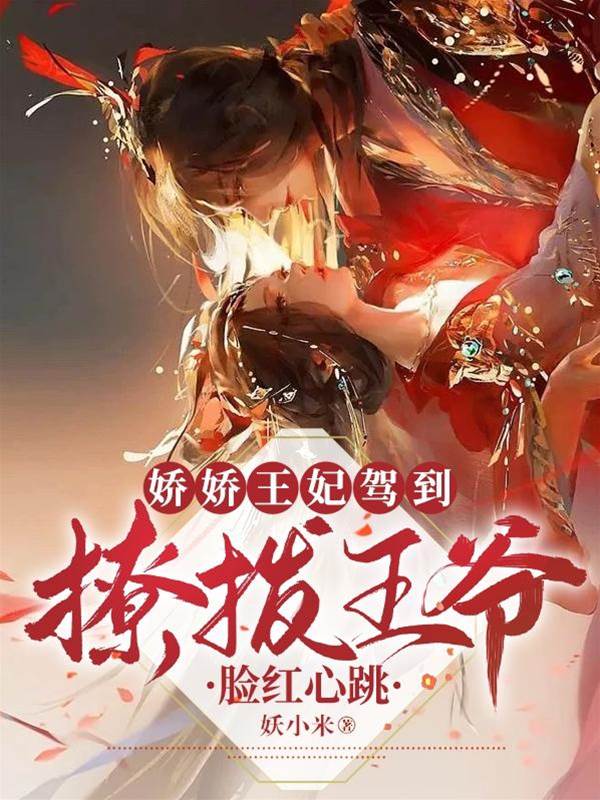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明月咬春》 第56章 第56章
他說這句話時, 葭音面上的積雪恰好墜下來。
雪塊子不大,幾乎是無聲地墜落在地上, 不一會兒就沒了影。
鏡容的聲音很克制。
不知是因為凝在后面站著, 還是因為知曉自己將要去赴一場將家命都賭上的刀山火海。
葭音腦海邊還回響著他先前的話。
這一次若是勝了,雖不能名垂千古,卻也能換得大魏一段時間的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可若是敗了,就是萬劫不復。
故此, 他對說,夫人,請您回去。
葭音沒有第一時間回應他的話,扶著一棵樹干壯的樹站穩了。今日穿了件極為素凈的蘇繡月華白襖,外披著金祥云大氅。那氅的紋路極淡, 素雪絹云,有些融為一。
腰間一塊芙蓉玉墜子, 隨著的作輕輕搖晃著, 日雪影, 清麗的面龐上帶著些堅毅之。
出聲, 于佛子前立住, 不在意對方刻意營造出的隔閡。
徑直問他:
“鏡容,你也是來找齊崇齊老將軍的麼?”
葭音的聲音脆生生的,像雪珠子墜在艷麗的花蕊上。鏡容微微低頭, 看。
“鏡容, 你不必避著我,我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道, “我知曉, 沈星頌請你宮為圣上看病, 又讓你找齊崇,請他出山。你所做的,我都知曉,我也知曉你為何要避我。”
似乎怕會惹生氣,鏡容抿了抿:“我沒有要刻意避你。”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想把我也牽扯進來。”
聞言,他沒有說話,算是默認了。
這場政治風云跟葭音沒有什麼關系,是林家的人,林家在場上向來是中立派,深諳中庸之道。如今政局,朝堂上也幾乎整整齊齊地自分為了兩列,一列是以沈星頌為首的,簇擁皇后娘娘與小皇子的臣子,主張立嫡;另一列是以何聿為首,簇擁何貴妃與二皇子之人,主張立長。
Advertisement
那林家大公子卻不同,對這兩撥人,其既不親近,也不得罪,大有明哲保之作風。
可在這波詭云譎的場里,當風雨真正來臨的時候,誰又能保全自呢?
葭音并不覺得林家、并不覺得自己可以全而退。
凝離二人有一段距離,聽不清他們的話。見鏡容這般,葭音忍不住走上前,輕輕拽了拽對方的袖子。
“鏡容,我想與你一起。”
他上很香,袖上,是沁人心脾的雪水與溫和佛香融的味道。
倏然一道凌冽的東風,將樹枝上殘存的積雪吹落了,險險地墜在佛子鞋履邊。鏡容一向清冷,即便與相,有些時候的話依舊很。二人談論時,他往往是安靜地坐在一邊,聽著葭音的話,溫和而笑。
葭音迎上他的眼睛。
不似鏡容,可以將滿腹意忍、克制到了極致。學不會像鏡容那般不聲,波瀾不驚。
郎披雪氅,周遭一時寂靜,可那一雙眉目明艷灼熱,似是這片冰天雪地里唯一的活。
“你避我,是怕我也被拉到這件事里來,可你知不知,我早已同你一樣,在泥沼之中。這些天,我總是怨恨三年前的自己,太過膽小懦弱。我原以為,當我面對我自己不能承擔的事時,選擇逃避,就會得到命運的僥幸。”
但實際上,并不是老天爺的寵兒,而是兵臨城下時,怯懦的叛逃者。
道:“我原以為,我只要不想你,不念著你,我只要逃過去躲過去,什麼事就可以萬事大吉。”
“鏡容,我原以為,這三年,我已經把你忘了個干凈。”
三年前,林府后院,葭音深知自己承擔不起與鏡容私.奔的后果。
Advertisement
害怕,畏,膽怯。只能說那樣的話,試圖把他走。
也試圖把他從自己心底里走。
白雪清寒,撲面的是刺骨的寒風,葭音忍不住瑟了下子。
這一個不起眼的小作落在鏡容眼底,他立馬心疼了。
他道:“阿音,別說了。”
“鏡容,你讓我說完。”
將領子往上提了提,冷撲撲的寒風刺得其臉頰有些發紅,卻渾然不覺,繼續說著:
“可當我在憫容的生辰宴上,看見梵安寺的佛子走進來的那一剎那,竟下意識地去找你。你站在廊檐下,雙手合十,恭敬而疏離地喚我夫人。那時候,我覺得我的呼吸都要碎了。”
“我原以為,我在心底里,把你藏得很好。藏到……連我自己都可以忘記,我曾經喜歡過你。”
深吸了一口氣,聲音發,“或者說,我真以為我可以騙過自己,我之前并沒有多麼喜歡你。我對你的喜歡,只是青春懵懂時的年無知,我不會把你記得這麼深切的。”
如果不是他出現在林家,再度出現在眼前。
“我原以為,我可以忘記你的……”
鏡容舌發。
他向來看不得這般,不是覺得不好哄,而是覺得心疼,覺得舍不得。
他忽然很想走上前去,將面前的小姑娘抱住,以自己這單薄卻也溫熱的之軀,替抵冬日寒風。
“直到聽說泉村的事。”
說起泉村,葭音的心好了些。與鏡容在泉村的那段時,是至今最好的一段回憶。
“聽到泉村發了瘟疫,我害怕極了。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不顧地去泉村,去那里治病救人。”
葭音回憶著自己當初的心境。
一想到這兒,鼻子就開始發酸。
Advertisement
“我當時很害怕,害怕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瘟疫來勢洶洶,天災面前,一個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很怕,很怕又要重蹈三年前之覆轍,于是趕忙去同林子宴說,自己要跟鏡容一起去泉村。
要與他一起。
哪怕,是與他一起死在那里。
“在泉村經歷了這麼一遭,我突然覺得,這世上也沒有什麼再難的事了。我連與你一起死都不怕——”
聞言,鏡容微微一蹙眉,終于開口打斷:
“莫要胡說。”
葭音笑了笑:“我的意思是,我和你連死都不怕,還怕與你一同走上風口浪尖、在眾人的口誅筆伐聲中在一起麼?”
所有的兵荒馬,他們都經歷過了。
即便世事坎坷挫折,也沒有阻攔他們重新相,反而給了他們一種繼續相下去的勇氣。
攥了佛子的袖。
他今日穿得很薄,又在雪地里面站了這麼一遭,不用想,手腳定是寒冷如冰。葭音悄悄將手進那袖口,鏡容也沒攔著,一下子,到了對方的手指。
奇怪,鏡容的手指竟很溫暖,寒涼的居然是。
冷風倒灌,刺骨的寒風變得刺目,倒灌的眼眶。
回想起與鏡容經歷過的一切,葭音很想哭。
承認,自己是氣。雪氅攥了對方的手指,緩聲道:
“況且,齊崇老將軍脾氣是出了名的古怪,不喜與人接,才將家安置在陡峭的山崖之上。他沒有家人,也沒有下人,你單槍匹馬地來請他,有多請他的勝算?”
說起正事,鏡容原本想嚴肅些。
可目一落到上,看見被冷風吹得紅撲撲的臉蛋與鼻尖,佛子的聲音不了下來。
他搖搖頭,“我也不知。”
Advertisement
“你看,鏡容,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懂得投其所好的道理。”
鏡容怔了怔:“投其所好?”
點點頭,抑制住方才的緒,盡量冷靜道:“你一直活在眾人敬仰的目中,自然不知道該如何求人,如何去討好一個人。就想面對齊崇,他看上去不近人,但我打聽過了,這位齊老將軍呀,就特別喜歡聽戲。”
“我雖然已有好些年沒唱戲了,但好歹在戲班子里面活了這麼多年,唱戲討老爺子歡心不算什麼難事。我跟你一起過去擺放他,哄齊老將軍高興了,請他出山的希就多了一分。”
說罷,像小孩子邀功似的揚起頭,“喏,你看,我跟你過來用可大了呢。”
的手,攥著鏡容的手指。
從他溫熱的手指上,汲取到一些溫度。
鏡容毫不避諱夸贊,溫聲:“阿音很聰明。”
“你又不喚我林夫人了?”
的手指的,讓人忍不住想。
如此想著,他便放縱著自己,輕輕了一下。
“不了,”鏡容輕聲道,“以后能不,就都不了。”
腳邊的雪融化了些,積了一個淺淺的水洼。葭音拽著他,走到另一邊。
聞言,抿抿,緩緩笑開。
“好,鏡容,我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嗯,你說。”
他看起來乖極了。
也許被剛剛這麼一哭,他也完全嚇到了,全心全意想著,如何才不讓難過,才不讓生氣。
語氣也不溫和下來。
沒有了剛走上山坡時,他刻意營造的疏離。
葭音知曉,他的疏離,亦是一種無聲的保護。鏡容想以自己的方式保護,舍不得在這場洪流中到傷害,殊不知,亦不舍對方這般。
寧愿,與他一同被來勢洶洶的洪流湮沒,也不要在這場浩劫中,做一個面不染泥土的自保者。
“你答應我,以后無論發生了什麼,都不要一個人扛著。你要說出來,千萬別悶在心里,人會悶壞的。”
葭音也了他的手指頭。
“你要相信我,要相信我們可以一起渡過很多很多難關。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你都不要松開我的手,都不要丟下我一個人。鏡容,好嗎?”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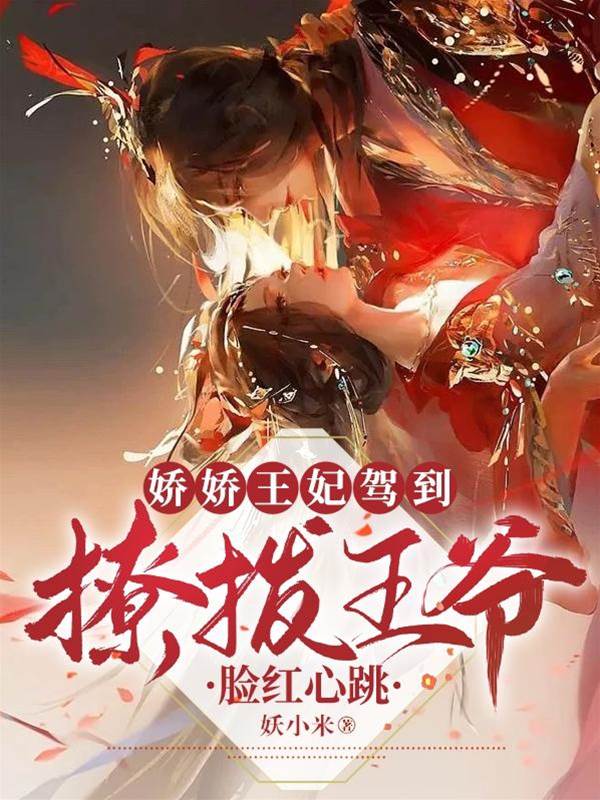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98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515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