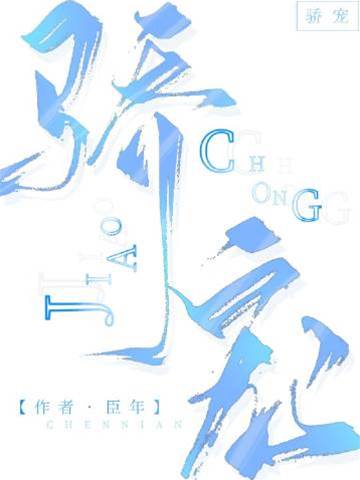《天真》 第49章 在哄
溫盞意外地,捕捉到另一個重點:“收養?那男孩不是親生的?”
困:“他不是你戰友的弟弟嗎?”
商行舟立馬反應過來,會錯了意。
扔掉煙頭,他將車窗升起來,搖頭,低聲:“沒,小孩是收養的。跟你猜得也大差不差,何叔和何阿姨是我一個小戰友的爹媽,我那小戰友前幾年在邊境犧牲了,他父母都上了年紀,生不出第二個孩子了。”
讀書人,中年喪子,仍然維持面。
兒子什麼都沒留下,里除去配槍,證件,只有一只舊手機。
手機里裝著他生前的照片和語音,不多,老兩口反復聽。
但沒多久手機就壞了,那些信息沒有同步云端,再也找不回來。
老兩口特別難過,沒想過儲存卡有壽命,信息會過期,會消失。
何阿姨在吊唁會上哭得昏過去,醒過來,商行舟背脊筆直坐在床邊,很堅定地告訴:“以后我是您兒子。”
可他天南地北到跑,本來也沒法在西城老人家面前盡孝。
很巧,差不多是半年之后,他執行任務,在西城救下一個小孩。
任務結束,要放人走的時候,小孩不走,粘著他。
商行舟沒什麼耐心,敷衍地揮手不想看見他:“行了,沒事了,回家,找你爹你媽。”
小男孩死盯著他,搖頭:“不回去。”
商行舟:“怎麼?”
小男孩:“沒家。”
商行舟詞窮,問了問況才知道,世界上真有這麼巧的事兒。
這男孩父親是警察,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因公去世了,母親改嫁之后不管他,把他寄養在親戚家。
親戚可想而知地懶得搭理這小孩,踢皮球似的到踢,小孩都八歲了,還沒學。
Advertisement
這種況,商行舟在中間費了點勁,才把手續合理地走完。
“然后。”他手指敲擊方向盤,把個中麻煩一筆帶過,“何阿姨他們家,收養了何頌。”
車靜悄悄,溫盞有點詫異,又覺得合理。
商行舟在這種事上,好像一向是很有耐心的。
但,還是沒忘記最開始要問的那個問題,謹慎地指出:“我為什麼要高興?”
“因為我沒結婚啊。”商行舟手指敲在方向盤上,側眼過來看,漫不經心地帶一子拽勁兒,“你說我邊連一個的都沒有,哪來的兒子,我又不是草履蟲,有分裂就行。”
溫盞默了默,提醒他:“商行舟,你不用特地證明給我看的。”
他微頓。
又說:“你有沒有兒子,都跟我沒有關系。”
車一瞬即靜。
車窗已經關上了,暖氣充盈,溫盞垂著眼,兩人離得近,溫像是織在一起。
商行舟手指微頓,不自覺地在方向盤上收,又松開。
再開口時,近乎咬牙切齒地,他問:“溫盞,你真不在乎?”
他跟解釋了,輕飄飄的,不太聽,好像他這些年過得如何,都無所謂。
溫盞抿著,不說話。
無聲勝有聲,的答案在這里。
心里的小火苗蹭地竄起來,緒堆疊,商行舟生不起氣,移開目,反而輕笑出聲:“好樣兒的,姑娘,微信你也不打算加了,對吧?”
一直沒通過的好友驗證。
微信沒有拒絕按鍵,只能忽略或者過期。
多賤啊這產品,給驢蒙上眼又在人面前栓胡蘿卜似的,不給信,就那麼吊著。
平平無奇的,尋常的一天,商行舟車停在路邊,不斷有居民笑著、談著,從邊經過。
Advertisement
車氣溫逐漸攀升,驅散清冷的氣息。
他心緒起伏,覺這些熱氣也和溫盞上的氣息糾纏在一起,縷縷地纏繞著,解不開,趕不走。
良久,商行舟漫長地嘆息:“我那支小隊匯合了,要去出一個任務,兩三天就回來,我下午走。”
微頓,他沒看,不甘心似的,低聲問:“我走了,你也不來送我?”
溫盞聞言,偏過頭,靜靜地看他。
仍舊沒開口,目里帶著淡淡的疑,明明一句話都沒說,好像就已經在問: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去送你?
商行舟抵了抵腮,朝后靠,認輸似的,啞聲:“算了,不送我就算了。你去北京等我,等我回來,有話跟你說。”
他沒看眼睛,手臂朝后探,從后座上拿起一個紙袋。
不管不顧,將里面東西拿出來,一個一個放到溫盞的帆布包里。
也幸好今天背的是帆布包。
他想。
不然這麼多,裝都不裝不下了。
“你一天拆三個。”他數著,啞聲說,“拆完我就回來了。”
溫盞沒阻止他的作,一直著他。
看著他,往的包里,塞進一串盲盒。
這東西最近幾年風靡全國,在哪都不難見到,但偏偏溫盞當時和涂初初拆的是城市限定,也沒弄明白,商行舟在西城是怎麼買到這一堆的。
“走了。”塞完最后一個,商行舟沒看,把帆布包放回懷里。鑰匙進車,他調轉車頭,清冷地返程,“送你回軍區。”
高原,藍天,陌生但安寧的城市,熱烈的、流的。
溫盞抱著包,盯著商行舟堅毅的側臉,好一會兒,嘆氣似的,問:“手機還在嗎?”
商行舟沒反應過來:“什麼?”
Advertisement
“你那個故去的小戰友的,手機。”溫盞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但總之有認識的人,可以試試,“也許我可以找人試一試。但你說得對,儲存卡是有壽命的,不一定能修得好。”
有時候覺得現代科技已經非常厲害,哪怕再短暫的信息,再簡單的表達,擊穿圈層,也能通過短視頻抵達千家萬戶,來到每一個有手機的人面前,被他們以各種形式刷到。
但有時候又覺得,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些留不住的,影像,聲音,圖片,如果有一天消失在浩如煙海的信息里,就是真正的消失了。
失去一段記憶,像將一個人拔出出自己的人生。
你沒辦法逆轉時鐘,也沒辦法強行將他留下。
只有失去的痛,地久天長地,停留在深。
商行舟下頜微繃著,明滅的不斷從他脖頸撲漱閃過,映亮他的臉。
很長時間,他低聲:“在我手上,回去我找給你。”
他說:“辛苦了,你試試看。”
-
回軍區,溫盞睡了個午覺,一覺醒來,下午三點半。
遲千澈已經等在樓下。
兩人驅車去往附近的舊城墻,西城春天還未到來,只有冬青郁郁蔥蔥。
現在是旅游淡季,城墻上人很,有小學生被父母帶著,在上面騎自行車。
痕跡歪歪扭扭,風迎面吹,風聲里織著小孩子遙遠的笑聲,和家長不厭其煩的喊聲:“我松手了?我真的松手了?”
溫盞跟著遲千澈走了一段路,他穿黑大,指給看:“出了這道墻,那邊是西城以西。”
溫盞瞇眼過去,眼看不到的地方。
再往西,海拔比這里更高,水鹽堿度超標,山口常年大風,能看到萬仞冰峰。
Advertisement
“他們當地人,取名字,說那個地方,是‘黑’和‘苦’的意思。”遲千澈說,“水不能喝,得靠人運。因為海拔太高,常年輻高反、有風沙,前線兵總是頭暈耳鳴,駐守幾年就要換人,心臟病病發率也高得驚人,當地人均壽命只有四十五歲。”1
溫盞站在墻邊,極目遠眺。
晴天,天空藍得讓人窒息,流的云層手可及。
舊城墻隔開,仿佛兩個世界。
一個世界安居樂業,另一個世界窮山惡水。
手機忽然微微震了震。
溫盞下意識低頭,陌生的號碼,彈出一條新消息:
「哎,真不來送我?」
愣了下,抬起眼,冥冥之中好像有牽引一樣,向城墻下方。
出城幾十米的地方,行道樹樹影搖晃,招搖的越野,就那麼停下。
駕駛座上的男人推門下車,長邁出,仍然是那件黑沖鋒,他出任務,沒穿有標志的服。
溫盞作微滯,沒想到竟然能在這里,看到商行舟出城的車。
在非常漫長的,遙遠的過去。
一直是這樣看著他,看著他的背影,一次又一次消失,頭也不回地遠去。
屏住呼吸。
可商行舟好像知道在這兒。
下一秒。
流的、熱烈的下,高大的男人忽然回過頭,角勾著抹笑,兩指并攏到額角,遠遠地,朝敬了個禮。
溫盞怔住。
有一個瞬間,好像回到十七八歲,教室里,他側臉轉過來,年輕氣盛,臉上落著。
聲音如同泉水回,清澈悅耳,低低的,落在耳邊:
“你知道嗎,溫盞。世界上,有一些非常壯的東西。”
垂眼,手指到帆布包,想起里面的盲盒都還沒拿出來。
出乎預料地沉,拿出來一個,發現紙盒被拆開過,一就嘩啦啦響。
還裝著別的東西。
抖了抖,抖出一堆子彈殼。
銀的,在下,折出清冷的。
——“高狙的彈殼,就不會生銹了。”
——“我帶彈殼給你啊。”
溫盞垂著頭,發愣。
遲千澈顯然也看到商行舟,他眼中浮起笑意,想起另一個東西:“你知道黃羊嗎?”
溫盞茫然:“我們前幾天,涮火鍋那個?”
遲千澈被逗笑:“黃羊學名蒙古原羚,生活在中蒙邊境,不能吃的。這種,每年春天和秋天會大規模地遷徙,頭羊帶領族群,去往海拔低的地方生活。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穿過草原時,就會被狼盯上。”
高原的狼,骨子里是野的。
那個勁兒,只有野生的、奔跑在荒原上的食,才會有。
他說:“溫盞,商行舟像那種狼。”
溫盞握著彈殼,想。
那應該很早之前,就被盯上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87 章

重生九九:嬌妻又甜又撩
重生前,顧悅歡又黑又胖,腦子還不好使。 重生后,顧悅歡一夜之間回到了80年代,還好,一切都可以重來! 她雙商在線,收拾極品家人,虐渣打臉不手軟! 花式逆襲,廣開工廠店鋪,勵志成為白富美。 結果一不小心撩倒各路男神,閃瞎眾人的眼! 唯獨面對上輩子被她辜負的男人,小心翼翼。 計劃了寵夫36招,剛要嘗試第一招撒嬌打滾,誰知……霍清越主動躺床,「媳婦兒,我躺好了,你可以寵我了」 顧悅歡:「……」 這人,怎麼就不按劇情發展呢?
133.5萬字8 3277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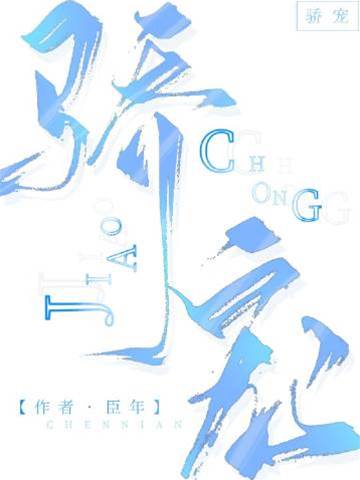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3856 -
完結968 章

霍先生乖乖寵我
溫蔓一直知道,霍紹霆沒那麼愛她,她有求于他,他貪圖她年輕身材好。當他的白月光歸來,他漸漸不再回家,溫蔓守著空房,度過無數個沒有他的夜晚,后來,她等到一張支票和他的一聲再見。……再次重逢,她身邊有了旁人,他紅著眼睛說:“溫蔓,明明是我先跟你好的。”溫蔓笑顏淡淡:“霍律師,先說分開的也是你!如果你想跟我約會,可能要排隊……”次日,她收到千億存款附加一枚鉆戒,霍律師單膝下跪:“溫小姐,我想插隊。”
217.8萬字8.46 885622 -
完結155 章

重生淪陷:她甜誘撩人
重生前,時星瑤暗戀周沉六年,誤以為周沉不愛她,隻把她當成白月光的替身。重生後,時星瑤才知道,周沉暗戀了她九年,他心裏的白月光一直是自己。重來一世,她才讀懂了周沉隱忍的深情,嗜她如命。隻是這個膽小鬼一直不敢承認,她決定主動出擊,撩他寵他,給他所有溫暖。周沉在泥濘中生活了二十幾年,從沒想到有一束光會心甘情願照在他身上。感受過溫暖後,他不願再回到黑暗,陰鷙威脅道:“寶貝,是你主動招惹我的,永遠不準離開我。”
18.2萬字8.18 23229 -
連載308 章

廢墟有神明
[暗戀x甜寵xhex男二上位][可鹽可甜x港區小霸王]那年七月,馮蕪爬到合歡樹上抓貓,許星池路過,拽開T恤衣擺:“阿蕪,把貓扔下來,哥哥幫你接著。”一轉眼,長大後的許星池噙著冷笑:“馮蕪,你幫她把芒果吃了,我答應跟你訂婚。”眾目睽睽下,馮蕪一口一口將芒果吃掉,她摸著手背因過敏迅速躥起的疙瘩,輕聲:“星池哥哥,咱們兩清了。”許星池哂笑:“可以,待會我就跟伯父商量訂婚事宜。”然而他沒想到,馮蕪的“兩清”,是真的兩清。喝到吐血那天,許星池在電話裏求她:“阿蕪,你來看我一眼好不好?”-傅司九忝為港區傅家最為紈絝的老幺,眼睜睜看著馮蕪小尾巴似的跟在許星池身後多年。他多少次都險些被氣笑了。這臭丫頭耳聾眼花就算了,連心都瞎了。那天夜晚,馮蕪喝多了,將柔軟的身子埋進他懷裏,傅司九舌尖抵腮,十分矯情:“你這是做什麽,老子不是隨便的人。”馮蕪抬頭,可憐巴巴還未說話,傅司九膝蓋瞬間軟了:“得,抱吧抱吧。”馮蕪捧住他長相風流的臉,“能不能親一口?”傅司九:“......”初吻被“奪走”的第二天,傅司九懶著調:“外麵天兒熱,小阿蕪可千萬別出門,九哥給你送冰咖啡,順便,把名分定了~
51.9萬字8.18 69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