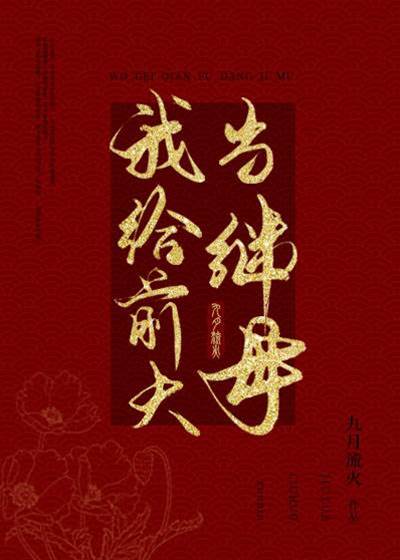《姑母撩人》 第48章 第48章
山桃杏野開無限, 綠水青山林碧影。青禾茅舍相映間,只恐春虛過眼。
柳枝與相扶疏,慢搖在奚甯肩頭, 仿若有一段嶄新的春意躍躍試。他還著簾子遞著手, 悠然淡遠間,十分堅毅,“下來, 跟我回家。”
奚緞云瞧見他肩外的淡淡遙山,山間的返鄉之路有多苦, 能預見,還有孤獨,想想都像有一片冷冰冰的湖,要將淹沒了。
吃得苦,可真是怕了孤獨,看得見黃昏月影, 聽得見鳴五更, 每一刻都凄苦地熬著, 不見來路, 看不盡歸途,只有在寂寂的道路上, 挪一步, 再挪一步。
很心, 可不知為什麼遲遲不肯出手, 與他僵持不下。或許還是為他前途擔憂,又或者,只是一點無傷大雅的縱。
在奚甯的期待里,倏地躥一下, 撒了他手上的簾子,聲音從簾后潑出來,悶悶的,像是撒,“我要回揚州。”
聞言,奚甯卻在簾外悶頭笑了,“真要回去?”
“要回去。”在里頭梗著脖子,絞著絹子。
外頭靜了會兒,才有一聲嘆息,“我說了這樣多,你卻是打定主意不回頭。也罷了,算我們有緣無分,你且去吧,我閣還有事兒,先趕回去了。”
稍刻就有馬兒的嘶鳴,得奚緞云一霎心慌起來,開簾子,眼前晃一下,是奚甯躥了進來,勾著角一笑,將撳倒在車里,“一會兒顛得屁疼,路途遙遠,你怎麼得住?不去了,跟我回家。”
奚緞云兩手在腦袋左右掙一掙,淚眼飛花地瞪上去,“胡說,車里墊得和,哪里會顛得疼?”
“此刻不疼,一會兒就疼了。”說著,他松開一個腕子,火急火燎地往下的,窸窸窣窣裳磨響,像是急不可耐地拆解什麼。
Advertisement
還沒反應過來,奚緞云便攢起眉喊了一聲,跟著從脖子燒了整張臉,疼得連捶他的肩,“你怎麼招呼都不打一聲?!”
“你回、揚州!給我打、招呼了嗎?”字節隨著他上躥,用力的打著頓,像是毫不客氣地就要給個教訓。躥著躥著,出許多的眼淚來,從眼角綿綿地到耳,潤了他的心,他輕輕地抹一抹,將親一親,“不疼了不疼了,馬上不疼了。”
眼淚漸干,卻有什麼從的別涌出來,從里到外潤了瞻前顧后的一顆心。不得不承認,十分貪生,十分貪他在生命里跳,或許有點痛,但正因這種疼痛的開墾,才令得春漫過寒冬,重回大地。
清風拂百丈,涌來夢蝶,生命忽然絢爛得似要在這一刻化為灰燼,燦爛濃烈的花香從野地襲來,重新洗禮了天地。即使無人為證,還有蜿蜒的山路,記載了無數的離別,與相遇,在這相一季。
這一場魂夢重逢始于噠噠的馬蹄聲,急促而慌張。敲得花綢也急促慌張地開簾子去往,果然是奚桓策馬過來,徑直過,揚起漫天黃土。花綢心里暗罵一句“瞎子”,忙出手去揮絹子,“桓兒!”
“瞎子桓兒”業已跑出去幾丈遠,聽見青山里的呼喊,猛地勒了韁繩,踱著馬蹄四張,尋不見,竟到天上去。花綢老遠地翻個白眼,車窗上歪出半截子,“我在這里!”
奚桓適才瞧見,打馬過來,朝車里,瞥見椿娘在里頭翻了好幾個眼皮。他假裝沒瞧見,抻直了腰,“姑呢?”
“你爹去追了。”花綢歪進去,絹子在鼻前揮一揮,揮去馬蹄漸起的飛塵,“我在這里等著,想他必定能把你姑追回來。”
Advertisement
“我去瞧瞧。”
眼瞧著奚桓轉了馬,紅藕比花綢還急,一把撈開,腦袋躥出車窗,“噯,傻小子!我勸你別上趕著去挨打,你追上去,你爹給你打折一條,你信不信?”
奚桓雖聽不明白,卻怕挨打,只得轉馬回來,“好好的,我爹打我做什麼?”
花綢也聽不明白,懶得計較,撥開簾子挑下車,“就隨我在這里等著好了,你爹做事,誰不放心?下馬來歇歇,你們從哪里跑來?”
“從宮里,采薇到碧喬巷秉我,說是姑要走,我怕留不住老人家,就往宮里去告訴爹。他正在閣與六部集議,聽見后丟下事兒就騎馬趕來,好歹趕上了。”說花間,奚桓已將馬栓在樹上,朝花地里向走來,歪著笑一笑,“也怪,你們家人都喜歡把人瞞著,什麼事兒自己就做了決斷,從不肯與人商量。”
這是指桑罵槐呢,花綢聽了,暗里白他一眼,不吭聲,地里隨手掐了朵野花,黃黃的,五個瓣兒,倒好看,要往頭上戴。戴上后嫌頭上金釵妨礙,便摘在手上,烏髻里變得素素的,單襯一朵沒要的野黃花,穿著草黃的,鶯的對襟,好似就是長在這片野地里。
也長在奚桓心里。
四野無人,抬眼間,卻有紅彤彤的滿樹野果。他折下一枝來,細看一看,的,上頭滿布麻麻的白點子,遞給,“這個好吃。”
“是什麼?”
奚桓搖搖頭,自己嚼了一顆,“我在書上瞧見的,能吃,你嘗嘗看。”
花綢摘了一顆,細嚼片刻,兩個眼彎起來,“有點兒酸。”
酸過后,又回著甜,索接過那一枝來,一顆顆往里送。低著脖子,暗窺一眼他睡得發皺的裳,又想起說采薇是將他從碧喬巷揪出來,便有些語重心長。“沒幾日就是會試,還只顧日日在煙花地里鬼混,可好好讀書了?真格耽誤了學業,我不拿你說話,你爹先要打你。”
Advertisement
“你為什麼不拿我說話?”奚桓瞥一眼鼓鼓囊囊的腮,轉過背,牽著擺,遞嬗折下果子兜在上頭,“我記得你從前說過,倘或我沉迷煙花,你先打斷我的。”
潺湲的風散著他有些發啞的聲音,著些寂寥。花綢著他的背影,發現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徹,他又長大了,學會藏起心事。嘆一口氣,酸裹著甜在的口齒間迴泛,“你長大了,染風弄月也沒什麼,只是為了玩耽誤了正業卻不該,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凡事都有分寸。”
“我要是沒分寸呢?”說著,他兜著滿紅彤彤的野果走來,破的果漿沾污了他的銀鼠灰的擺。
花綢也分不清他到底有沒有分寸了,看看果子,又抬眼看看他,“那我也就顧不得什麼名聲面了,親自往碧喬巷去揪著你打一頓!”
他卻洋洋得意地笑,“我等著。”
春從葉罅里撒下來,是跌破金燈與流火,躍在花間,躍上二人的臉與當中橫隔的一尺距離,不近不遠,似乎又回轉當初,什麼都沒變,從未嫁人,只有兩顆心在無人之境里迂回試探。
可走出荒野,回到紅塵,花綢用絹子兜著果子甫房門,就被屋里沉的氣氛驀地嚇退了整個春。
外房里向案跪著個丫頭,裳上掛著漉漉的茶湯,對著風口吹得直打抖,是原就在這屋里伺候的,花綢記得,秋桂,一直侍奉單煜晗的飲食起居。
花綢繞到前頭去,見哭得可憐,便將果子遞給椿娘,躬去攙,“好端端的,你跪在這里做什麼?快起來,地下涼得很。”
秋桂卻將胳膊讓一讓,不敢起。須臾見單煜晗臥房里踅出來,臉上掛著笑,“讓跪著,做錯了事兒就該罰。”
Advertisement
“做錯什麼了?”
他走到上首一張折背椅上,斜花綢一眼,又垂秋桂,使人上了茶,慢吞吞呷一口,等得人心焦了,他才啟口,“不在家,問去哪里了,回不知道。一個丫頭,連主子的向都不曉得,這差事當得也太馬虎了些。不罰一罰,倘或在外頭出了什麼事兒,把的命折了,也不為過。”
花綢稍一琢磨,便聽出些弦外之音,忙辯解,“娘要回揚州,我去送一送,走得急,沒告訴一聲,怎麼怪得著呢?起來吧,地上涼,仔細跪出病來。”
說著去攙秋桂,秋桂窺著單煜晗臉,仍舊讓著不敢起。花綢心里不由起了火,直起腰來,往那頭椅上捉落座,“你有什麼話兒,來問我好了,犯不著拿個丫頭出氣。倒怪了,娘回鄉,我做兒的,去送一送能有什麼錯?也值得你這樣生氣?”
單煜晗聽了,別眼瞧,笑意鷙,語氣淡淡,“我倒不知道這樣大的脾,往日千般和順萬般溫,今日為著個丫頭卻要與我爭一爭。”
“秋桂起來。”花綢朝椿娘抬抬下,椿娘便擱下果子,旋拽起丫頭。
“跪著。”誰知單煜晗又淡淡彈一句,秋桂立時捉安分跪回去。他笑笑,嗅見酸甜的果子香,揭開絹子瞧一眼,鼻稍翕,又笑,“真格是好雅興。”
花綢向來煩他這吞吞吐吐怪氣的調子,有些失了耐,攏了果子兜著往臥房里去,耳后聽見他在外頭打發人出去,腳步聲跟著進來。懶怠與他周旋,便隨手撒了帳,牽了被子佯裝睡覺。
帳外一霎靜悄悄,綺窗進來幾線斜,如同虱蚤爬在單煜晗一側的臂膀,在得到與失去間輕輕搔。他隔著紗帳看那條玲瓏的曲線,好似仕途一樣崎嶇,他在上頭徒徙一生,走得坎坷疲倦。
有那麼一瞬間,他想去抱著哭一哭,訴說他不為人知的辛酸,可往往給與他的,是挑不出差錯的嫻雅文靜,拿他當個長一樣服侍,唯獨不給半點。
的都給了誰呢?是比還讓他歡喜與落寞的奚甯!他忍無可忍,終歸是開了帳,掰轉花綢的肩,眼里飽含著可不可即的恚怨,魯地解的裳帶子。花綢嚇得神魂失措,忙往里頭一,“你要做什麼?!”
單煜晗將的手撳在枕上,半條膝蓋跪在鋪上,接著的裳,“裝什麼樣子?回回這樣問,你心里難道不知道?”
行間,將床架子搖得咯吱響,花綢瞧他有些走火魔的神態,愈發慌張,手腳并用著往外掙,“放開我、你放開我!天白日的,你發什麼瘋?!”
“原來你也有脾氣?”單煜晗扼住的手腕,整個人罩在上頭,卻倏地不了,嗤嗤發笑,“真巧,我也有脾氣。”
話音甫落,他斂了笑意,斂起那些呼之出的傾訴,讓另一種洶涌的念來取代它。他俯下去親,被偏著臉避開,他便順勢出一截舌細細一折就能掐斷的脖子。
像有一條毒蛇纏在花綢的脖子上,蠕中出渾的皮疙瘩。在忍耐他與推開他間反復盤桓片刻,最終認命地闔上眼。可黑漆漆的里,有點恍惚閃現著奚桓悲慟的臉,啞啞地發出聲,“是我太孩子氣,還是你太懦弱?懦弱到連爭也不敢爭。”
大約是不想他失,倏地哪里來的力氣,一把推掀了單煜晗,抬手摑了他響亮的一掌,“你在哪里的窩囊氣,別撒在我上!”
單煜晗怔了半日,眨眼間,恍回神思,漠漠的眼瞥過花綢,下床拂整冠,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風度翩翩地走進書房,從日落干坐到黃昏。
直到丫頭門口奉茶來,被畢安攔住,接了茶端進黑漆漆的屋里,黑點亮幾盞燈,擎著銀釭走到案前賠笑臉,“爺別生氣,雖說戶部河南清吏司的員外郎之職落到了別人頭上,可咱們還有潘大人那條路可走呢。”
說到此節,單煜晗兩手疊腹前,愴然地仰頭向屋頂,“我實在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奚子賢為什麼愿從江蘇調任員來補缺,也不愿意給我。上回在他家中,我分明覺著他有這個意思……”須臾,他拋掉悲憤仰回來,匆匆重振旗鼓,只是仍有昏黃的燭在他臉上輕跳著疑恨,“未必上回,他只是試一試我?”
猜你喜歡
-
連載1471 章
佛係醫妃有空間
她,醫毒雙絕的杏林傳奇,一朝穿越,成了永寧伯府嫡四姑娘雲悠然。一場賜婚,許給了心有所屬的定王蕭君昊。他怒奔沙場,勢以軍功換退婚。可任軍功累累婚約仍依舊,心上人終成側妃。……春竹王妃,水側妃告您善妒,淑妃娘娘命您立刻排侍寢表。雲悠然上旬單日水側妃,雙日花側妃;下旬單日陶庶妃,雙日宮庶妃,抄好給各院都送去一份。定王王妃你呢?雲悠然我?我又冇告狀!……駱馳王爺,花側妃她們於挹芳亭設宴,請了王妃賞月。定王走,看看去。駱馳王爺,小丫鬟特意強調這是專為王妃設的宴。定王……豈有此理,她們到底嫁的是本王還是王妃?
243.7萬字8 53956 -
完結272 章

庶女翻身:夫君,請自重
前世一片癡心,卻錯付絕情帝王,以致家破人亡,含恨自儘。一朝重生,雲伶發誓今生絕不重蹈覆轍,定要棄情愛,報家仇。可誰知,再度入宮,這該死的帝王更加深情款款,引得後宮人人視她為眼中釘,處處危機四伏。嗬,以為她還是剛入宮闈的單純小白兔?流螢舞,假落水,她既能抓住皇上的真心,也能擋得了小人的算計,一顰一笑之間翻雲覆雨……“景南潯,我要親手毀了你的江山,讓你墜入地獄!”正當她步步為營,達成所願的時候……
69.8萬字8 6054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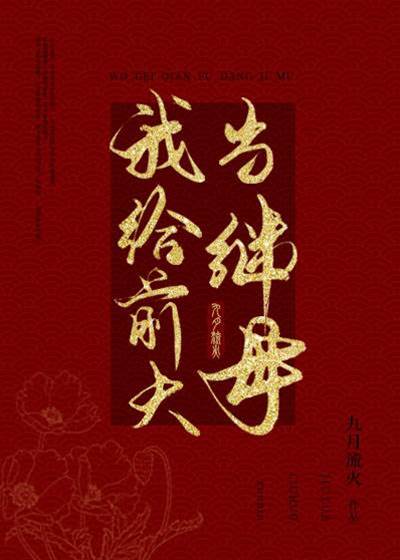
我給前夫當繼母
【微博:晉江九月流火】林未晞死了一次才知,自己只是一本庶女文中的女配,一個用來反襯女主如何溫柔體貼、如何會做妻子的炮灰原配。 男主是她的前夫,堂堂燕王世子,家世優越、光芒萬丈,而女主卻不是她。 女主是她的庶妹,那才是丈夫的白月光,硃砂痣,求不得。 直到林未晞死了,丈夫終於如願娶了庶妹。 她冷眼看著這兩人蜜裡調油,琴瑟和鳴,所有人都在用庶妹的成功來反襯她這個元妻的不妥當。 林未晞冷笑,好啊,既然你們的愛情感動天地,那我這個姐姐回來給你們做繼母吧! 於是,她負氣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前世未曾謀面的公公——大齊的守護戰神,喪妻后一直沒有續娶,擁兵一方、威名赫赫的燕王。 後來,正值壯年、殺伐果決的燕王看著比自己小了一輪還多的嬌妻,頗為頭疼。 罷了,她還小,他得寵著她,縱著她,教著她。 #我給女主當婆婆##被三后我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已開啟晉江防盜,訂閱比例不足70%,最新章需要暫緩幾天,望諒解】*************************************************預收文:《難消帝王恩》虞清嘉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女配文里的原女主。 呵呵……反正遲早都要死,不如活的舒心一點,虞清嘉徹底放飛自我,仗著自己是嫡女,玩了命刁難父親新領回的美艷小妾。 這個小妾也不是善茬,一來二去,兩人梁子越結越大。 後來她漸漸發現不對,她的死對頭為什麼是男人?他還是皇室通緝犯,廢太子的幼子,日後有名的暴君啊啊啊! ***本朝皇室有一樁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比如皇室男子雖然個個貌美善戰,但是卻帶著不可違抗的嗜血偏執基因。 慕容珩少年時從雲端摔入塵埃,甚至不得不男扮女裝,在隨臣後院里躲避密探。 經逢大變,他體內的暴虐分子幾乎控制不住,直到他看到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每日過來挑釁他,刁難他,甚至還用可笑的伎倆陷害他。 慕容珩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樂趣,可是總有一些討厭的,號稱「女配」 的蒼蠅來打擾他和嘉嘉獨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也沒有人可以奪走你,你獨屬於我。 他的嘉嘉小姐。 註:男主偏執佔有慾強,祖傳神經病,女主虞美人假小妾真皇子與作死的嫡女,點擊作者專欄,在預收文一欄就可以找到哦,求你們提前包養我!
36.9萬字8.36 631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