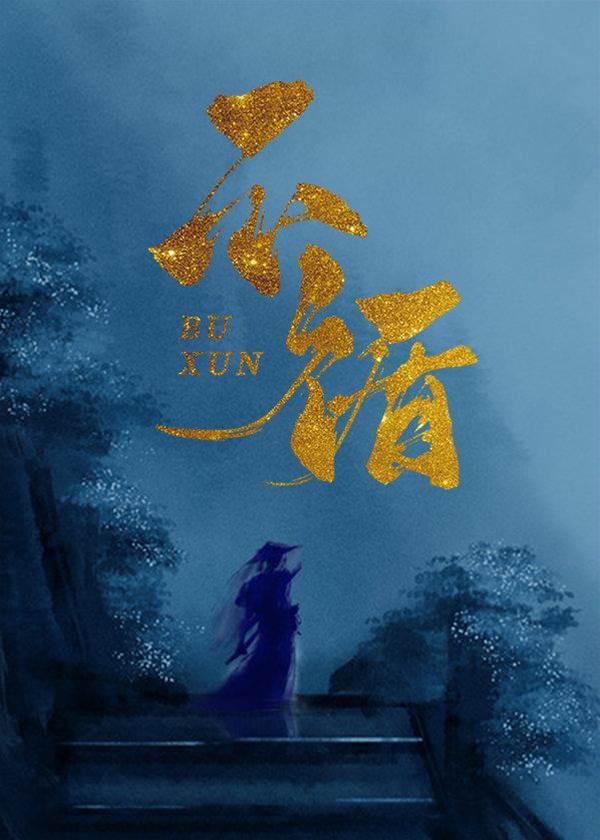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53章 第 53 章
唐厚孜棋藝一般, 圍棋費腦傷神,盤棋下半日的不在數,學院里并不提倡學生沉迷棋道。
他坐下不過半個時辰, 就被句老爺殺得片甲不留了。
唐厚孜也沒脾氣,起深深揖:“句爺爺這手屠龍實在厲害!我還得再練幾年。”
見他起,句老爺知道他這是生了去意, 心里急著回家。句老爺又夸了他幾句,送著華家出門, 自己棋興上來了,留了華姥爺下棋。
從句家出來, 唐厚孜直覺神清氣爽,還當是了卻了心頭一樁大事,心里輕松, 全然不知是院子里清心香的功勞。
唐荼荼還是不太懂“借園子”的意思, 有點不敢信:“真的點銀子也不用給嗎?不用簽個租契麼?萬我們損傷了人家園子里的花木, 怎麼辦?都是別挪過來的好樹, 很貴的。”
觀賞樹里有生長特別快的, 起碼十年方能材。
昨天在句家那園子里看過,滿園的樹種, 唐荼荼幾乎都能認出來, 都是別地移栽過來的佳木。棵樹、片花、塊奇石,都有各自的品名,看便知這園子是拿銀子堆砌起來的。
唐厚孜那高興勁兒歇下去,扭頭看他娘。
華瓊笑了聲:“都是一條街上的, 不用算那麼清楚,咱家和句家平時生意上也有些往來,像他家瓷店里的熏香, 用的全是咱家的;你二舅舅去南方跑商的時候,也會捎帶幾車瓷去,連賣帶送,今年夏那時候,還幫他家拉了單生意。”
“借了個人而已,下回還點好就行了。這是我們大人之間的事兒,不用你倆心。”
華瓊領他倆回了宅里,寫了幾道相關的事,“園子是借下了,怎麼布置得咱們自己想辦法,不能麻煩人家。三五百人的宴席,肯定是要弄臟園子的,讓下人盯著點,別讓客人弄傷人家的花木。”
Advertisement
說到這兒,華瓊頓了頓,覺得唐府沒幾個會來事兒的,立馬話風一轉。
“但那麼多客人,也看顧不過來,就算哪個客人不懂事,咱們是主家,不能當面與客人爭執。損了什麼壞了什麼,回頭我再跟句家商量如何賠。”
宴席還沒開,還不知道能不能開,便把切都想好了,副有竹的樣子,讓唐荼荼和哥哥安下了心。
……
這事兒解決得麻利。
唐府里,唐夫人連上何、宋兩位夫人還坐在一塊發愁,連午飯也沒心思吃,扭頭的工夫,就聽義山高高興興說找好園子了,問“延康坊蓮池夠不夠大,能不能盛得下”。
何夫人又驚又喜:“蓮池?夠夠夠,那可真是太夠了!你們倆個怎麼借著園子的?”
唐荼荼和哥哥目閃爍,支支吾吾糊弄過去了。
在母親面前說娘,他倆誰也沒那麼沒腦子。
可唐夫人知道他倆是從華府回來的,看他倆這表,就什麼都明白了,心里有點不得勁。當著外人面也不好細問,等三位夫人按唐老爺留下的禮程單,樣一樣地商量完,送著二位夫人走了,唐夫人才細問他倆是怎麼回事。
唐厚孜:“是娘跟句家借的,就是那個賣瓷的句家。”
“那可真好。”
聽完,唐夫人并沒說什麼,像往常一樣催了晚飯,安置了些瑣事。等回了自己房里,臉才垮下來,唉聲嘆氣的。
“分明是我快應承住了,偏偏我這也不懂,那也不會。這頭老爺為難,那頭給華家添麻煩——我這應承的是什麼事兒啊。他們娘還不知道怎麼想我……”
胡嬤嬤給拆著釵環,聽這個開頭,就知道夫人又犯擰了,忙溫聲勸道:“怎麼能添麻煩?華家太太給爺持,那不是應該的?爺中舉這麼大的事兒,華家太太要是一點都不出力,才是臉上無呢。”
Advertisement
“夫人把爺當親兒子樣得疼,華家太太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麼會嫌事兒麻煩?”
兩個嬤嬤好不容易才把主子開導好。
自七月初開始,蓮池鎖門閉園,句家全留給了他們。
清早太還沒大盛,幾家的下人早早到了,華家和句家的仆役比他們來得還要早。華瓊大概是怕兩家別苗頭,提前待過了,讓自家下人別往唐夫人跟前湊,兩邊不約而同地分了半園子,各自灑掃起來。
唐夫人和何夫人都是掌家的夫人,勞命,上午忙得腳不沾地,也停不住,吩咐了這個吩咐那個。華家和句家都只來了個管事,卻比們幾個夫人安排得還要有章法。
因為文宴招待的是貴客,要先攔了園中泉眼,掏干凈池塘的淤泥。池子里養著百來尾紅鯉金鯉,清理淤泥就了個麻煩事,得先攔網把錦鯉堵在一頭,清理了那頭,再把魚換去那邊。
華瓊收完租子后,上午趕過來瞧了瞧,眼尖,眼就看見荼荼扎在仆婦堆里,手里拿著漁網桿在池子里劃拉,水濺了半,鞋和腳都了。
唐家的嬤嬤著急喊著:“二姑娘快別玩水了,小心了涼!”
華家的仆婦都跟華瓊一個脾氣,圍了圈,各個給荼荼好:“姑娘網得好準!那頭還有兩條大的!”
華瓊站在上池邊上遠遠去,荼荼那網兜子里是好幾條活蹦跳的錦鯉,個頭大得快要了,有人的小臂那麼大個兒了。
用人家的園子,還敢網人家的紅鯉!華瓊眼皮撲簌簌直跳,進人堆里:“干嘛呢這是?”
水桶里已經裝了好幾條紅鯉了,唐荼荼把這網的三條也放進桶里。老老實實說:“句老爺說這池子里的紅鯉個頭兒太大了,撈幾條上來,中午做魚吃,他說還沒嘗過紅鯉的味兒,讓我們挑個頭兒最大的撈。”
Advertisement
華瓊哭笑不得:“你什麼時候學會網魚的?”
唐荼荼彎起眼睛:“剛學的。這網大,特別好撈,娘你試試!”
“我學這作甚,濺水,這紅鯉又不好吃,就你跟著句家老爺瞎胡鬧。錦鯉是聚福的,你把人家家里的福氣全撈走了。”
華瓊嘮叨了幾句,見荼荼玩得頭大汗,高興的樣兒,自己忍不住也笑了。
在莊子里就發現荼荼這習慣了,這丫頭不管看見什麼新鮮的,就要張問,看見不懂的,也要跟著學。在莊子里住的那幾天,還學會了拿火剪撿牛糞,全然不似個小丫頭。
上還有道理,說不管學來有用沒用,技多了不。這道理不錯,于是撿牛糞,華瓊也沒攔著。
等荼荼把那一水桶魚網滿了,華瓊才拉著去邊上坐下,說起自己的安排。
“娘跟木匠家掌柜定了八十套桌椅,中桌,桌能坐八個人,回去問問你爹夠不夠。我也不知道接帖的客人能來多,但桌椅只能多不能……你慢點喝。”
見荼荼喝水都跟別的孩不樣,咕咚咕咚口喝下去半杯。華瓊腦殼,又提點。
“宴席學問大著呢,陳設啊禮數啊、再到座次安排都有講究,你不是學東西麼?睜大眼睛仔細看,學到一點算點。你是大姑娘了,怎麼管家、怎麼掌事都得學起來,別拖延到以后什麼也不會。”
聽出華瓊這言外之意是“姑娘早晚要嫁人的”,唐荼荼也不吭聲,只管點頭。
母倆說說笑笑,后邊又胳膊挽著胳膊,繞著園子散步。唐夫人遠遠見了,心里有點不是滋味——荼荼都半年沒跟挽過手了。
唐夫人再往西園那邊看,這才個上午,人家西頭的活兒快要做完了,上下兩個泉池子都清凌凌的,池底淤泥洗刷得干干凈凈,竟能看到池底石壁的本。這會兒還在亭子里架起了梯|子,下人爬得高高的,正在掃角梁和檐楣上的積灰。
Advertisement
而們這邊照貓畫虎,干了上午了,還在洗那幾塊石板磚,沒拾掇出個樣子來。
兩邊比,這就沒法看了。
何夫人索把這邊的仆役都派過去,讓華家的管事派活兒,幾人總算能坐下歇口氣,坐在亭里問唐夫人:“那就是借咱們園子的那家主人?看著倒是年輕,家下人也調|教得好,那是你家親戚嗎?”
“……是義山那邊的娘。”
唐夫人坐得直的,撐起“我不在意”的派頭。
可園子是人家出的,這會兒荼荼跟母倆親親熱熱拉著手,何氏又這麼問起來,唐夫人渾都不自在。
何氏瞧臉不好看,忙道:“瞧我這張,不該問的瞎問,妹妹別往心里去。”
只管好奇,好奇完了又不管勸,隔著老遠觀察著華瓊,臉的新鮮。
唐夫人心里有點堵,晌午回了家,下午只把府里的下人派過去做活兒,唐夫人自己沒跟著去了。
躺在涼塌上,輾轉反側地從中午躺到了下午,也沒睡著。等胡嬤嬤回來了,又忍不住去問他們下午做了什麼。
胡嬤嬤好笑:“夫人既然上心著,怎麼不去看看?”
唐夫人話里味兒酸:“人家是親生的母親,給兒子辦文宴,事事都比我想得周到,我杵在那兒顯得多余。”
“你再看人家家里頭的仆婦,那活兒利索的,各個都是一把好手,放咱家里邊當管事都大材小用了,在華家竟只是一群干活的使!……華家太太得是什麼樣的厲害人?怪道老爺忘不了,荼荼和義山也往那邊跑。”
一邊夸,邊酸,直把胡嬤嬤笑出一臉皺紋。
“夫人您又多想啦,老爺和華家太太年見不了兩回,哪有什麼忘不了的?”都不是一道人,平時爺小姐生辰,都是兩家各辦各的,前后岔開天。
胡嬤嬤笑了會兒,怕夫人多想傷神,給了額頭。
全家“夫人”、“母親”地喊著,卻沒幾個記得,主子今年才滿而立。心著家子,連自己都顧不上,當了這麼多年的后娘,心里頭委屈的事不止這麼件兩件,又沒法跟人說,全都得自己消解。
胡嬤嬤心疼,話卻說得不和。
“老奴說句讓夫人不高興的——這鹿鳴文宴,聽說要來三五百客人?饒是大戶人家娶妻,也不過就是這陣仗了。夫人的本事我知道,咱家哪里能持得了這麼大的宴會?”
“后晌我看了看那請帖單子,聽說還有好幾位舉人老爺是三品的家出,人家各自有什麼喜好,有什麼講究,咱們都兩眼抓瞎,夫人得跑多趟,才能打聽清楚?”
“再說,夫人是老爺寫在族譜里的正正當當的夫人,別管它先來后到,您養育爺這麼多年,爺將來出息了,是要給夫人您長臉的,掙個誥命回來,也是給夫人您掙的。”
見唐夫人聽進去了,胡嬤嬤又道。
“您自己悶在房里計較這個,多喪氣,還不如每天去那園子里跟著學學。我瞧他家的管家是真厲害,怎樣安置宴會、怎樣待客都有章法。”
“老奴一下午跟著學到了不——像這請帖,咱們以為送到各家門房就行,可不是哩!得把請帖送到各家管家手上,再勞管家遞呈給他家長房夫人。這條,夫人就不知道吧?”
唐夫人哪里知道這個?沒知道去。
神松下來。
胡嬤嬤循循善:“老奴瞧,爺將來還會有大出息呢,這樣大的宴會只會多不會。夫人這回學一學,手,將來爺中了狀元,做了,再辦這樣幾百人的大宴席,夫人心里不就有數了麼?”
到底是一手養大唐夫人的老嬤嬤,句句都中心思。唐夫人定下心來:“你說得對。”
猜你喜歡
-
完結1570 章

退婚夜!我撕了戰神王爺的衣服
新婚夜,被陷害與男子有染,還要被放火燒死?楚千漓笑得沒心沒肺:“休書我已替你寫好,告辭。”風夜玄將她一把擒住,冷肆陰鷙:“想走?除非從本王屍體上跨過去!”……神醫大佬意外穿成不學無術的玄王妃,楚千漓隻想當一條混吃等死的鹹魚。誰知惹上偏執瘋批玄王爺,一不小心被寵上了天!某日。眾臣哭喪著臉:“王爺,王妃又在大鬧金鑾殿,
177.7萬字8.46 384935 -
完結103 章

夫君位極人臣後
公主府開宴,一處偏僻殿內,賀蘭瓷掐著掌心扶著牆,和同樣腳步淩亂的新科狀元郎陸無憂狹路相逢。一個柔若無骨,一個麵色酡紅。四目相對,雙雙從對方眼中看到一絲絕望。“我先走了……”“我走那邊……”然而更絕望的是,不遠處還能聽見公主侍女和二皇子侍從搜尋兩人的聲音。賀蘭瓷咬唇:“要不你從一下公主?”陸無憂忍耐:“我覺得二皇子人也不錯。”賀蘭瓷:“再說我們就隻能兩敗俱傷了!”陸無憂閉眸:“那就兩敗俱傷吧。”賀蘭瓷:“……?”一夕之後兩人清白全無,隻得被迫成親,然而強敵環伺,這親事成的分外艱難。一邊是虎視眈眈盼著她喪夫的二皇子,一邊是目光幽冷盯著她的公主。賀蘭瓷:“……你能頂得住嗎?”陸無憂:“頂不住也得頂,誰讓我娶都娶了——我將來是要做權臣的,自不會倒在這裡。”賀蘭瓷:“那你努力哦!靠你了!”陸無憂:“……?”經年以後,陸無憂做到內閣首輔,位極人臣,權傾天下,回憶起舊事。門生向他請教是如何走到這裡的。陸首輔心道,隻要娶一位有傾國傾城之姿又時常被人覬覦的夫人,總能催人上進。
48.6萬字8.25 69888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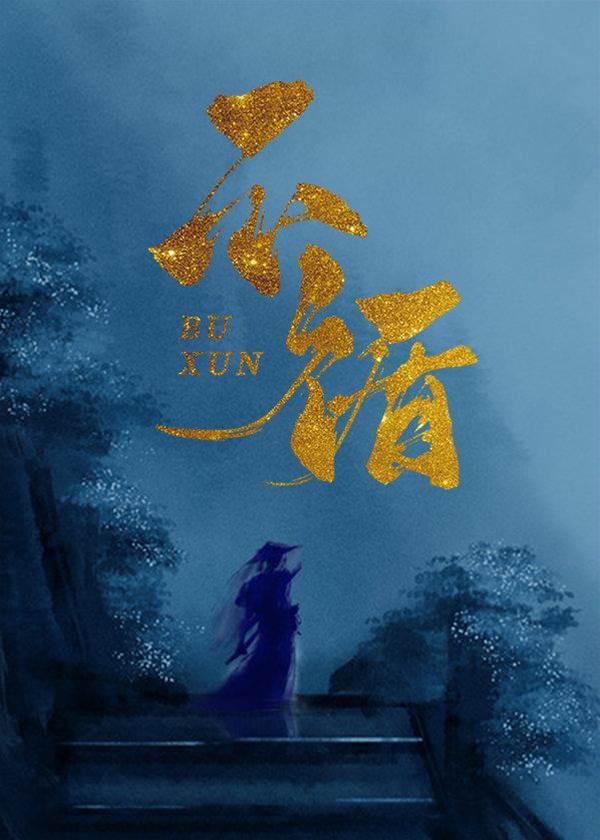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207 章
農門女狀元
農業大學歷史系的宋梔穿越后成了小可憐,父親剛死還沒埋,債主又打上門來要抓她去做小妾,這可怎麼辦?幸好她在現代跆拳道不是白練的,將人打出去就是,可一窮二白的她要如何在女子地位低下的古代生存下去?答曰只有走上科舉之路!且看小小農門女如何通過科舉走上人生巔峰,實現農門女到當朝第一首輔大臣的華麗蛻變!
55.6萬字8 12561 -
完結124 章

吾妻甚是迷人
【嬌軟妖精X清冷太子,雙潔/重生/超甜!超撩!兄長超強助攻!】天凰國嫡出四公主溫若初,傳聞容貌驚人,如仙如魅,琴棋書畫無一不精通。是世間難得的嬌軟美人。眾人不知的是,自小兄長便在她房中掛起一副畫像,告訴她畫中之人是她夫君。一朝被害失去大部分記憶,她終於見到了畫中的夫君,比畫中來得更為清俊矜貴,身為顏控的她自然眼巴巴地跟了上去。“夫君,抱我~”“......”元啟國太子殿下,生性涼薄,宛如高懸明月。自及冠那年,一直困擾在一段夢鏡中,夢中之人在他求娶之時,轉嫁他人。尋人三年,了無音訊。正當放棄之時,在一處淺灘上遇到那女子,她嬌軟地撲向他,叫他夫君。劇場一花采節在即,京城各家貴女鉚足了勁兒爭奪太子妃之位。豈料霽月清風的太子殿下,親自從民間帶回了一名女子養在府中,各方多加打探均未知曉此女子的身份。眾人皆笑太子殿下竟為美色自甘墮落,高嶺之花跌落神壇;未曾想太子大婚當日,天凰國新任國君奉上萬裏紅裝,數不盡的金銀珠寶從天凰運送至元啟,並簽下了兩國百年通商免稅條約,驚得等看笑話的眾人閉了嘴,這哪是路邊的野薔薇,明明是四國中最尊貴的那朵嬌花!
22.9萬字8 14339 -
完結266 章

重生后嫁給廢太子
重生後,餘清窈選擇嫁給被圈禁的廢太子。 無人看好這樁婚事,就連她那曾經的心上人也來奚落她,篤定她一定會受不了禁苑的清苦,也不會被廢太子所喜愛。 她毫不在意,更不會改變主意。 上一世她爲心上人費盡心思拉攏家族、料理後院,到頭來卻換來背叛,降妻爲妾的恥辱還沒過去多久,她又因爲一場刺殺而慘死野地。 這輩子她不願意再勞心勞力,爲人做嫁衣。 廢太子雖復起無望,但是對她有求必應。餘清窈也十分知足。 起初,李策本想餘清窈過不了幾日就會嚷着要離開。大婚那日,他答應過她有求必應,就是包含了此事。 誰知她只要一碟白玉酥。 看着她明眸如水,巧笑嫣然的樣子,李策默默壓下了心底那些話,只輕輕道:“好。” 後來他成功復起,回到了東宮。 友人好奇:你從前消極度日,誰勸你也不肯爭取,如今又是爲何突然就轉了性子? 李策凝視園子裏身穿鬱金裙的少女,脣邊是無奈又寵溺的淺笑:“在禁苑,有些東西不容易弄到。” 知道李策寵妻,友人正會心一笑,卻又聽他語氣一變,森寒低語: “更何況……還有個人,孤不想看見他再出現了。” 友人心中一驚,他還是頭一回看見一向溫和的李策眼裏流露出冷意。 可見那人多次去禁苑‘打擾’太子妃一事,終歸觸到了太子的逆鱗!
41.8萬字8.18 436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