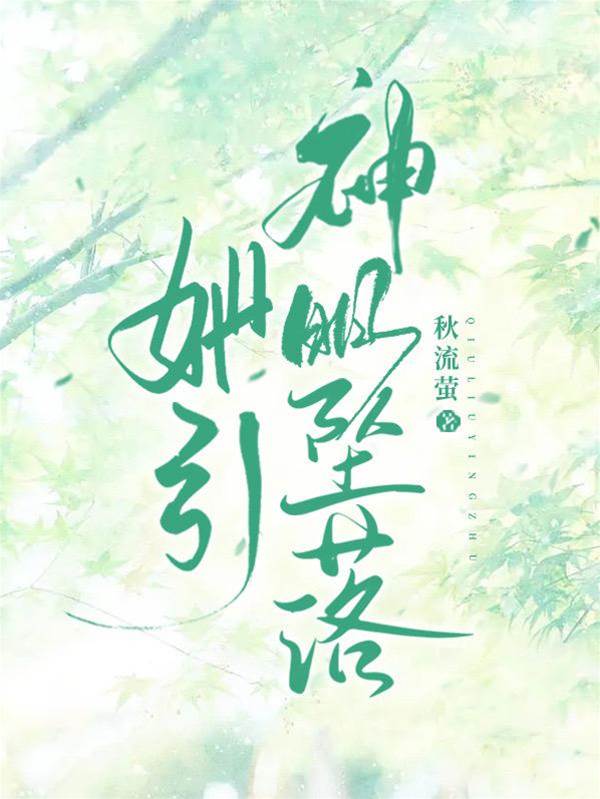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裝傻和眼盲反派聯姻后》 第107章 【IF世界01】
偌大的墓地山上, 來吊唁的親朋好友們來了又走。
宗柏彥就這麼站在墓碑前,盯著那張黑白相的目麻木而空,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哥, 天就要黑了, 走吧。”
宗可言走了上來,將帶來的外套披在自家親兄長的上,眼眶還帶著哭過的紅,“哥,你別這樣, 你再這樣熬下去,容哥他也會擔心的。”
一周前, 宗柏彥相了十年的人許容在家中的畫室里拿刀自盡。
等醫生趕到時,對方的留了一地, 膛和心臟的位置更是被不算鋒利的刀狠狠扎出了五六個口子,足以見得生前的死志。
短短一周,宗柏彥把自己折騰得不吃不喝,重迅速下降,整個人都仿佛靈魂出竅的空殼, 仿佛靠著一口仙氣就能吊著。
“……他會擔心?”
宗柏彥含糊不清地念叨著這個說辭, 卻是一滴眼淚都哭不出來,“他連死都不要我了,還會擔心我?”
“哥,你別這樣。”
宗可言上前攙扶,卻被他輕巧拽開,“你先走吧, 我想要再陪他說說話, 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就想要待在這里。”
宗可言不放心,“不行,你這樣……”
“給我一點時間吧。”宗柏彥的視線終于從墓碑上轉移,看向了自家妹妹,“好嗎?”
“……”
面對兄長近乎絕的請求,宗可言只好退而求其次,“那我讓小陳在底下等你,最多再給你一小時,待會兒回家讓書開車。”
宗柏彥垂下眸,又想起一事,“小意找到了嗎?”
他口中的“小意”,是他和許容從福利院領養的小孩。
一周前,因為目睹且未能及時攔截住對方的自/盡行為,所以被嚇得不行,趁他們大人不注意就跑出了家門,至今都沒再回來過。
Advertisement
“容哥生前最寶貝小意了。”宗柏彥是擔心,也是自嘲,“現在的他不會擔心我,但一定會擔心小意。”
宗可言保證,“哥,警方已經去找了,我一定讓人盯著消息。”
宗柏彥的回答聲依舊輕得沒有力氣。
直到宗可言一步三回頭地離開墓地后,周圍再無其他人后,宗柏彥的雙才驟然發,一米八幾的高個說摔就摔。
膝蓋和手腕嗑蹭在水泥地上,但他像是完全不到疼痛,爬到了冷冰冰的墓碑前,一言不發地挨了上去。
一秒、兩秒、三秒——
宗柏彥猛然砸下一滴眼淚,哭得悄無聲息,卻又在歇斯底里的撕扯。
一年前,為專業教授的許容因指出了學生在作品上的抄襲,就被偏激的對方用死亡來栽贓嫁禍。
即便宗柏彥已經用關系第一時間澄清了所有,但網暴帶來的惡意還是摧毀了本溫的人。
許容患上了重度抑郁,是在一日復一日的陪伴和相中,對方的緒、懷疑還是不可自控地逐漸擴大。
宗柏彥知道人病了,所以每回莫須有的爭執后,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地疏導、陪伴、道歉。
可人的緒不是可以無限拉扯的皮筋,早晚也會有斷裂的一天——
宗柏彥還記得兩人最后一次見面。
那天他為了趕落下的工作進度,通宵和手底下的員工們完了一個并購策劃,因為過度的疲勞,他只好請了朋友幫忙開車送回。
哪知這一幕落在了許容的眼中,就了他徹夜不歸家、乃至于出/軌的證據。
原先的宗柏彥認定兩人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撼,可當天聽見許容毫無依據的質問后。
原本就因為通宵而頭疼不已的他,終于還是點燃了深在心里的導火線。
Advertisement
兩人開啟了有史以來最強烈的爭吵,一氣之下,宗柏彥就沖地回了一句——
“是!他媽就是你想得那樣!要是你覺得和我過不下去了,那我離開就行了!”
然后,他就丟下了許容摔門而出。
實際上,宗柏彥出門不到五分鐘就已經后悔了,但他的和神都已經累到了極限,一狠心還是沒有回頭。
他想要找個地方短暫休息,等到稍微平復緒才回家解決問題。
可宗柏彥沒想到,自己一狠心,許容卻比他更“狠心”。
這一周里,宗柏彥只要閉上眼睛,就是許容滿是的畫面。
對方站在離他幾步遠的地方,不讓他靠近,而是字字、句句淚——
“為什麼說不就不了!”
“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不要我了?”
宗柏彥只要一想到,許容對他們的充滿了失,乃至絕了結生命,宗柏彥就恨不得以命抵命。
“……”
宗柏彥從自己的口袋里出一把工刀,上面還沾著些許難以洗干凈的跡,正是許容生前所用的那一把。
天已經全黑了,墓地四周的燈散了過來,孤獨地籠罩著宗柏彥。
他親吻了一下墓碑上的黑白照,將其牢牢抱靠著,“容哥,你再等等我,等我找到了小意,安頓好了他,我就去找你。”
到時候,他說什麼都不會再犯渾了。
宗柏彥抱著墓碑合上眼,想象中人還在自己懷里的溫度,終究是無法抵擋連日來的疲憊,就這麼睡了過去。
…
夢里的一切清晰又混沌。
宗柏彥在二十歲那年和許容的初遇,也有他死纏爛打對許容的追求,有許容答應往時的激,也有兩人在磨合期產生的小爭執。
Advertisement
從年輕不懂事,到為了徹底長。
從相到相,從結婚到領養小孩,他們的幸福從未間斷,卻又碎得猝不及防。
夢境的最后,依舊是渾染的人,在一點一點地離他遠去、消失。
宗柏彥只覺得被渾的悲痛得難以息、近乎死去,他終于沖破了腳下看不見的束縛,沖去抓住了那雙留有溫度的手。
“我抓住你了!求求你,別走!”
“容哥!”
“——別走!”
宗柏彥驟然驚醒,從床上爬坐了起來,他的大腦還在一陣一陣地犯暈,但眼睛早已經開始接收起了周圍的一切。
手中攥的“溫度”來自于被套,深藍系,上面印著的印染花樣還是許容親自設計的。
這曾經是對方最喜歡的一套床單,只是在一年以前,因為不小心撕扯出的破而被他們徹底丟掉。
怎麼會還在這里?
宗柏彥環視起主臥的布局,一切都很悉,一切又都不一樣了。
悉的是這是他們曾經布置的擺設,不一樣的是,并不是近期的。
空氣中彌漫著早餐的香味。
宗柏彥不可置信地跑下床、打開房門,將視線對準了廚房方向——
屋外的投進櫥窗。
許容穿著再簡單不過的白睡,正在專心攪弄著剛剛熄火的湯鍋,即便只是側,也帶著旁人無法及的溫笑意。
“……”
宗柏彥沒意識到自己呼吸里的抖,等他再反應過來時,他幾乎是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沖進了廚房。
因為跑得過急,他還撞到了立式推拉小車,上面的食品袋散落一地。
聽見靜的許容剛一轉,就被宗柏彥狠狠抱,對方的力度重得仿佛要融進骨才肯善罷甘休。
Advertisement
“容哥。”
溫熱的、鮮活的、是他以為再也不能擁有的人。
連日來不曾徹底宣泄的緒在這一刻徹底發,宗柏彥抱著失而復得的人,哭得痛徹心扉、毫無章法。
許容被他突如其來的奔潰緒嚇得不輕,艱難出一只被錮的手,輕拍著人的后腦勺安,“怎麼了這是?怎、怎麼哭這樣了?”
認識近十年,宗柏彥落淚的次數之又,許容印象最深也就只有兩次——
一次是在剛往時兩人吵架,對方故意裝了欺負的小狗狗,哄得他心和好;另外一次是向他求婚功后,人也抱著他哽咽了幾句。
但從未有過一次,人會哭得像這般崩潰。
許容見自己的低哄不奏效,只好紅著耳換了方式,“老公,到底怎麼了?你抱得太了,我呼吸不過來了,難。”
宗柏彥一聽這話,頓時從痛哭中找回一清明,他松開了懷抱的力度,抖的指尖從許容的眉眼到鼻尖再到側。
許容用余確認自家小孩還沒從房間里出來,才溫而克制地吻了吻宗柏彥的指尖。
“到底怎麼了?一大早的哭得像個孩子似的,也不怕小意待會兒出來了看笑話?”
宗柏彥重新攬住眼前人,帶著失而復得的委屈和恐懼,“做、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你不要我了。”
“瞎說。”
許容哭笑不得地拍了拍他的腦袋,“做個噩夢就把你嚇這樣了?”
宗柏彥深呼吸了兩口氣,“容哥。”
許容繼續安,“我在這呢,夢和現實都是相反的,別怕,我哪里都不去。”
“嗯。”
“我先陪你回臥室洗漱,待會兒讓小意看見這模樣,你這彥爸的形象就要沒了。”
“嗯。”
許容從擁抱著退出,主牽住宗柏彥的手,總覺得又看見了二十歲出頭的人,有點小小的孩子氣,讓他偶爾心。
…
宗柏彥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了自己,又拉著許容坐回到了主臥床上,面對面重新抱懷中。
這子黏人勁,比起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許容無奈卻縱容,問,“現在好點沒有?”
宗柏彥默默接收著眼前的一切,是害怕也是慶幸。
害怕又是夢一場,更慶幸如果是真的,他還有機會挽回還沒發生的一切。
“容哥。”
“嗯?”
“我不是在做夢,對嗎?”
“這都醒了多久了?還在夢里呢?”許容笑他。
宗柏彥靠近,繼續著曾經那些好的生活習慣,“那你今天還沒給我早安吻。”
許容吻了一下,“早安,這樣可以了嗎?”
宗柏彥搖了搖頭,帶著只有對方才能看得懂的撒,“我還是有點怕。”
許容明知道人有故意的分,但還是又親了他,“這樣呢?好點了嗎?”
宗柏彥上了癮,“還想要。”
許容不給,“事不過三。”
宗柏彥聽見許容輕松的語氣,懸在嗓子眼的心終于一點點落回了原地。
他拉著人的手,一字一句地叮囑,“容哥,你要記住我很你,我只你一個人,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我。”
許容沒有刻意去追問那場讓人膽戰心驚的“夢境”,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給予回應。
“不要生病。”宗柏彥挨了上去索吻,酸卷土重來,“不準、丟下我。”
“我不會丟下你……唔!”
許容的回應聲被堵在了口中,被地迎接著宗柏彥珍惜而輕的親吻。
舌尖輕車路地探齒,攪著溫熱和潤,由淺深,繼而變得無比熱烈。
許容被吻得意識模糊,半推半就地倒在床上,用僅存的一理智做著拒絕,“不、不行,嗯……”
“為什麼不行?”
“小意。”許容抬起子,熱著臉提醒,“你還要不要送小意去學習班了?別鬧了。”
“……”
宗柏彥一怔,后知后覺地反應過來。
許容將黏人的伴推開,重新確認了一下床頭柜上的鬧鐘時間,已經早上八點半了,離上課只有半小時了。
“你趕的,那小貓肯定又睡迷糊了。”
許容連忙示意人起,兩人才走出主臥,就看見了逃跑不及時、從而顯得貓貓祟祟的裴意。
雙方視線相對。
裴意的臉瞬間從臉紅到了耳后,不打自招,“彥爸、容爸,我、我什麼都沒看見!”
他早起發現廚房和餐廳里都沒有人,所以才想著到主臥去敲個門,哪里想到過虛掩的門就看見了那種臉紅心跳的畫面!
救命!
他不會被抓起來打屁吧!
猜你喜歡
-
完結511 章

聽說校草被甩了
安靜內斂沉默的少女,嬌生慣養毒舌的少年,兩人之間坎坷的成長曆程與甜蜜情深的故事。*雲慎曾在學校時聽到這樣一段對話--「聽說言謹被甩了……」「誰這麼囂張敢甩了他?」「雲慎啊。」「那個偏遠地區的轉學生?」「可不,不然還能有誰?」全校同學集體沉默了一會兒,唯有一道聲音有點不怕欠揍的說道:「這年頭,言謹還會遇上這麼活該的事情?」雲慎「……」*他們的愛情,屬於那種一切盡在無言中,你圍著他轉,卻不知,他也圍著你轉。很甜很寵,包你喜歡,快來吧~
80.4萬字8 14751 -
連載2595 章

霸道帝少惹不得
安希醉酒後睡了一個男人,留下一百零二塊錢,然後逃之夭夭。什麼?這個男人,竟然是她未婚夫的大哥?一場豪賭,她被作為賭注,未婚夫將她拱手輸給大哥。慕遲曜是這座城市的主宰者,冷峻邪佞,隻手遮天,卻娶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從此夜夜笙歌。外界猜測,一手遮天,權傾商界的慕遲曜,中了美人計。她問:“你為什麼娶我?”“各方面都適合我。”言安希追問道:“哪方面?性格?長相?身材?”“除了身材。”“……”後來她聽說,她長得很像一個人,一個已經死去的女人。後來又傳言,她打掉了腹中的孩子,慕遲曜親手掐住她的脖子:“言安希,你竟然敢!”
424.7萬字8.18 52225 -
完結512 章

新婚夜,我治好了陸先生的隱疾
【一場陰謀撞上蓄謀已久的深情,經年仇恨,也抵不過陸靳宸想要溫晚緹一輩子的執念。】 *** 溫晚緹嫁給了陸靳宸。 她本以為,他們的婚姻只是有名無實。卻不想…… 她還以為,他和她都一樣,各懷目的,於是小心翼翼地守著自己的心。殊不知,他早把她鎖在了心裏。 *** 眾人都等著看她笑話,等著看她被趕出陸家大門的狼狽樣子。 哪知,等啊等,等啊等。 等來的是他替她遮風擋雨,替她找回親人…… *** 片段 他曾醉酒後,撫著她的臉呢喃,「阿緹,我放過你,誰放過我自己?」 他也曾清醒後,黑著臉沖她吼,「溫晚緹,我陸靳宸從和你領證的那一刻起,就認定了你。我們之間不會有生離,只有死別!」 *** ——後來, 人人都羨慕溫晚緹,她不僅是豪門真千金,還是陸靳宸寵在心尖尖上的女人。
98.4萬字8 46945 -
完結50 章

許以晴深
祁邵川是許晴心頭的一根刺……當那天,這根刺扎穿了許晴的心臟,讓她鮮血淋漓的時候,她就徹底失去了愛一個人的能力。但如果所有的一切重新來過,許晴興許還是會這麼做。…
5.2萬字8.18 1413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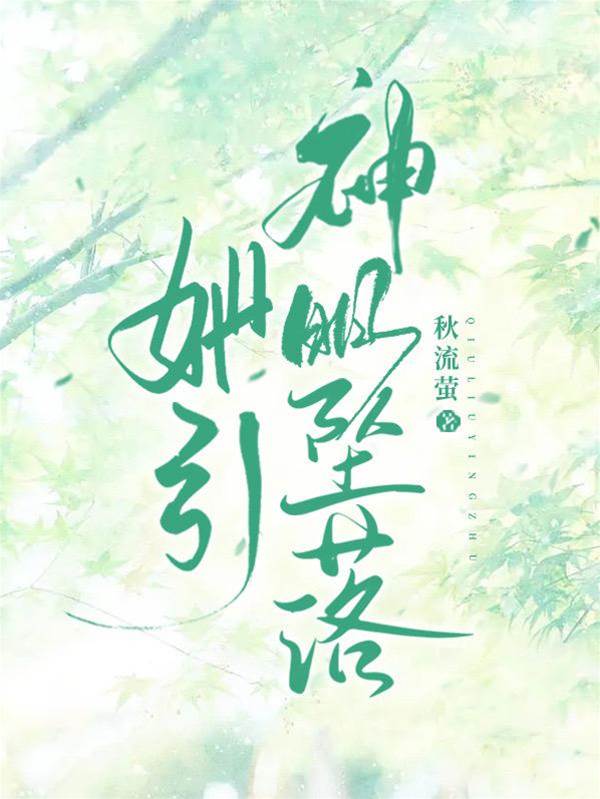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43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