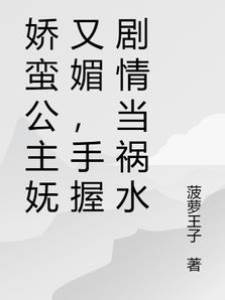《逐鸞》 第106章 第 106 章
仙乃月神山腳下,秦訥帶著十個全副武裝的壯士正在等候。謝蘭胥出現后,這十一人下了馬,遠遠地就向謝蘭胥行禮。
秦訥看見同謝蘭胥一起出現的荔知,眼中閃過一訝異。
“都準備好了麼?”謝蘭胥問。
“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山。”秦訥說,“這十名壯士,是我軍中好友,絕對可信。他們愿為殿下赴湯蹈火。”
隨著秦訥的話語,十名壯士一齊拱手,聲音洪亮道:
“愿為殿下赴湯蹈火!”
荔知在謝蘭胥旁小聲道:
“我們現在去哪兒?”
“進山取寶。”
謝蘭胥打頭往前走去,荔知連忙驅馬跟上。
秦訥和十名壯士先后上馬,前后各五匹,將荔知和謝蘭胥兩人保護了起來。
沿著崎嶇蜿蜒的小路行進了一炷香時間后,天空中飄起了小雪,氣溫愈發寒冷,地面也被積雪覆蓋,山上的樹林銀裝素裹,遮天蔽日,偶爾會有梅花一般的腳印留在樹下。
偌大的神山上,只有風雪蕭蕭的聲音。
越是往上走,風就越大。
荔知努力從飛揚的齏雪里辨認方向。
謝蘭胥時不時停下來,辨認周圍標志。
大約一個時辰后,謝蘭胥在一林里令眾人下馬。
“應當就是此了。”
謝蘭胥率先朝西北方向邁出腳步,其他人趕忙跟上。
仙乃月神山積雪終年不化,荔知每一腳都踩在厚厚的積雪里,雪直沒完小肚才停。再加上山上氣溫突降,荔知邁過深深的積雪來到最終的山前時,手腳都已冷得沒了知覺。
“點燃火把。”
謝蘭胥一聲令下,秦訥立即讓十名壯士都拿出火把點燃。
他們點火的時候,謝蘭胥走到荔知前,下上的外披在荔知上。想要拒絕,卻冷得只能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Advertisement
謝蘭胥的外有貂皮,還有謝蘭胥本的溫,一披上,荔知就覺好了許多。
“我不冷。”
荔知話還沒問出口,謝蘭胥就回答道。
“冷了也不會覺得疼。”
秦訥和十名壯士手里都拿上了燃燒的火把,等著謝蘭胥發號施令。火映照在山里,墻上和地上影影綽綽。
“走吧。”謝蘭胥接過秦訥遞來的火把,說。
謝蘭胥握著的手,往深走去。
黑暗,深不見底,兩人走了快一炷香時間,也沒有看見任何和寶藏沾邊的東西。
火把的照明范圍只在數步之,遠了便是一片漆黑。
荔知屏息凝神地觀察著周圍一切可疑的痕跡,忽然瞧見頭頂有什麼東西。
連綿一片,起起伏伏,像是鐘石一般。
好奇地接過謝蘭胥手里的火把,往上一照——
麻麻層層疊疊的蝙蝠,一個接一個的掛在頂上。
毫無預兆的驚懼直沖腦門,荔知咬住自己的牙齒,生生咽下了這聲尖。
秦訥和那十名壯士雖是男子,但看上去依然大沖擊
。
“冬眠了。”謝蘭胥揣著雙手,一臉淡定地看著頭上的這些蝙蝠,“小聲些就不會吵醒它們。走吧,繼續往前。”
荔知懷著余驚,更加小心翼翼地隨著謝蘭胥往山深走去。
在寂靜得只有彼此腳步聲的環境里又過了大約半炷香時間,一扇若若現的石門,終于出現在眾人眼前。
秦訥神一振,快步走到石門,用火把上下映照了一番,沒有發現危險,才讓謝蘭胥等人過來。
謝蘭胥揚了揚下示意,秦訥讓壯士中力氣最大的幾名上前,想要推開石門。然而石門在兩個壯漢的推下紋不。
Advertisement
又有兩個壯漢加了進去。
四個壯漢一齊使力,石門依然沒有毫開啟的跡象。
荔知皺眉看著眼前的石門,有一個地方引起了的注意。
“這扇門,中間是不是有一條?”
秦訥立即拿著火把湊近,搖晃的火里,石門中央,果然有一條一尺長的小。
“此門是按照地宮來設計的。”秦訥說,“門里應該還有一塊倒下的自來石,傾軋在外邊這扇石門上。”
“所以需要用特制的某種東西,從這條隙里進去,頂開石門背后的東西?”荔知問。
秦訥看了一眼。
“姑娘正解。”
秦訥走回十個壯士邊,其中一人在上搗鼓了一會,拿出一把長短一樣的鐵尺,依次組裝起來后,完整的鐵尺足有一人高。
“殿下神機妙算,這頂門果然派上了用場。”秦訥說。
手持鐵尺的壯漢上前,小心地將鐵尺沿著隙塞了進去。
鐵尺漸漸沒小。
眾人屏住了呼吸,直到石門后傳來咔嗒一聲輕輕的響聲。
手持鐵尺的壯漢驚喜道:“到了,果然是有什麼東西頂著這門!”
又有幾名壯漢加,幾人一起握著鐵尺,用力往另一端使力。
雖然荔知看不見石門背后有什麼東西,但幾名手握鐵尺的壯漢都漸漸青筋畢,滿頭大汗,像是在和什麼龐然大作斗爭。
半晌后,石門后傳來地山搖的轟隆一聲!
門后的自來石立起來了,但石門還是只能半開,只夠一人側進。
“看來還要移開門后的自來石才行,屬下先來吧。”秦訥說。
獲得謝蘭胥首肯后,他側進石門,過了片刻,門后傳來移重的聲音。
半晌后,出了一頭細汗的秦訥從里打開了石門。一人高的自來石就靠在一旁的山壁上。想來先前就是這塊石頭擋住了門。
Advertisement
眾人終于進了石門。
石門毫無生氣,左右都是迷宮一樣的岔路。
“難保這里不會有機關,大家小心。”秦訥說著,走到了眾人的前方,十名壯漢中也只有兩名走在了最后護衛,其余都跟秦訥走去了前方開路。
地道里線昏暗,秦訥長了手臂,努力照亮前方的一片幽暗。
哎喲一聲,是三個壯漢撞到了一起。
“這里太窄了,只能兩人并行。”秦訥說著,指揮眾人兩兩一排前進。
不知誰到了什麼,空氣里傳來像是齒
吻合上的咔嚓一聲響。
“小心!”
秦訥大喊的同時,嗖嗖幾聲,有什麼從正前方飛馳而來!
荔知還沒回過神來,就聽見利箭破空掠過頭頂的聲音,隨后是箭矢刺的噗嗤聲。
接著咚咚三聲。
等回過神時,前后三人已經腦袋中箭,倒在地上死不瞑目了。
鮮順著他們被貫穿的腦袋流了出來。
走在他們這一列的,除了荔知幸免于難,只有十人里面個頭最矮,和荔知高相近的那名矮壯之人仍幸存。剛從鬼門關回來的這人雙目圓瞪,心有余悸,一臉后怕。
這才剛開始便折損了三人,這下誰也不敢大意了,火把不停照映著四周,生怕再開啟什麼機關。
謝蘭胥在不知什麼時候握住了的手,荔知過昏暗的火,看見他神平靜,毫無不安。
而他們這些腦筋正常的人,怕疼,怕死,所以本能地對不知會從何飛出來的暗提心吊膽,如履薄冰。
不對——!
謝蘭胥的平靜,不單是因為缺了一筋。
他對的安危,不應如此平靜才對。
剛剛可是站在那一列遭到機關殺的人里!
他的平靜,或許是因為早就知道那里有著機關,也知道機關的位置,無法對產生威脅。
Advertisement
這樣才是最合理的解釋。
可他為何要對秦訥帶來的人下殺手?
荔知悚然心驚,再看謝蘭胥,他臉上依舊平靜,只是變得更加深不可測了。
眾人靠著投石問安,有驚無險避過幾次機關。終于在謝蘭胥的帶領下,走出長長的迷宮,進一間寬闊的石室。
石室里什麼都沒有,唯有正對著的那面石墻上,雕刻著一枚巨大的“崔”字。
謝蘭胥走上前去,站到崔字前。
取出一把匕首,割破左手,讓滴落下來的鮮流崔字口。
鮮蜿蜒,很快便將石墻上的崔字染得紅。
伴隨著輕輕一聲響,崔字石墻在眾人眼前從中分開一條細。謝蘭胥毫不猶豫手一推,石門向著兩邊打開。
幽風從門后吹了進來。
金盈滿。
荔知不由自主屏住了呼吸。
門后通向一條只可一人通過的石橋,如彩虹一般連接到對面的崖上。金銀珠寶,珍寶玉,難以計數,目不暇接的珍寶幾乎將大半個地填滿。珍寶們如麥浪起伏一般涌著金,金燦燦地堆積在崖下的地。掌大的金磚沉積在底,四散落,反而是地里最便宜的東西。
火搖曳閃爍,華撲面而來。
眾人雀無聲。
忽然,后的通道里傳來了腳步聲。
一群從未見過的陌生人從荔知剛剛經過的迷宮里走出。他們穿著親王扈從的甲胄,手里握著隨時都可出鞘的長劍,一臉戒備地看著謝蘭胥等人。
在他們后,頭戴金冠的謝韶走了出來,
謝韶往謝蘭胥后看了一眼,卻對那金燦燦的一片興趣不大。
他復雜難言的視線更久更深地留在荔知上。當他看向謝蘭胥時,眼中的神轉為冰冷。
謝韶冷冷道:
“瞞崔朝寶藏事實,妄圖一人獨吞。謝蘭胥,我就是現在殺了你,父皇也不會怪罪于我。”
謝蘭胥并不說話。
他微微垂頭,還揚起了角,似乎對謝韶的話不以為意。
“你來了。”他輕聲說。
猜你喜歡
-
完結481 章

睜眼亂葬崗,醫妃炸翻王爺心尖尖
【爽文虐渣+甜寵無虐+靈泉空間+武器庫】又嬌又颯戲精王妃vs病嬌禁欲超會撩王爺中西醫雙修天才軍醫蘇棠,左手手術刀出神入化,右手狙擊槍快狠準,一朝穿越亂葬崗,一顆炸彈落入美男懷中。嬌縱草包大小姐變身打人不手軟拽王妃。拳打渣爹,腳踢惡毒繼母,反手毒翻綠茶妹妹,虐渣不亦樂乎。可沒曾想美男王爺太黏人,她殺人,他遞刀,她下毒,他收尸,她睡覺,他爬床!白天蘇曉棠醫毒雙絕打臉不手軟,晚上卻可憐巴巴的靠在某個男人懷中。“王爺,手疼要吹吹。”君夜冥眼尾泛紅的抱著懷中的戲精女人,“糖糖,你甜化了我的心,不信?心掏出來...
87.9萬字8 71483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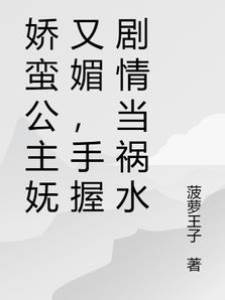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4507 -
完結337 章

重生后王妃嬌軟不可欺
京城人人傳說,杏云伯府被抱錯的五小姐就算回來也是廢了。還未出嫁就被歹人糟蹋,還鬧得滿城皆知,這樣一個殘花敗柳誰要?可一不留神的功夫,皇子、玩世不恭的世子、冷若冰霜的公子,全都爭搶著要給她下聘。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麼多好姻緣這位五小姐竟然一個都不嫁!她是不是瘋了?冠絕京華,億萬少女的夢,燕王陸云缺去下聘“那些人沒一個能打的,昭昭是在等本王!”宋昭挑眉,“你個克妻的老男人確定?”陸云缺擺出各種妖嬈姿勢,“娘子你記不記得,那晚的人就是本王?”宋昭瞪眼原來是這個孫子,坑她一輩子的仇人終于找到了。這輩子,她得連本帶利討回來了。
61.7萬字8.18 194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