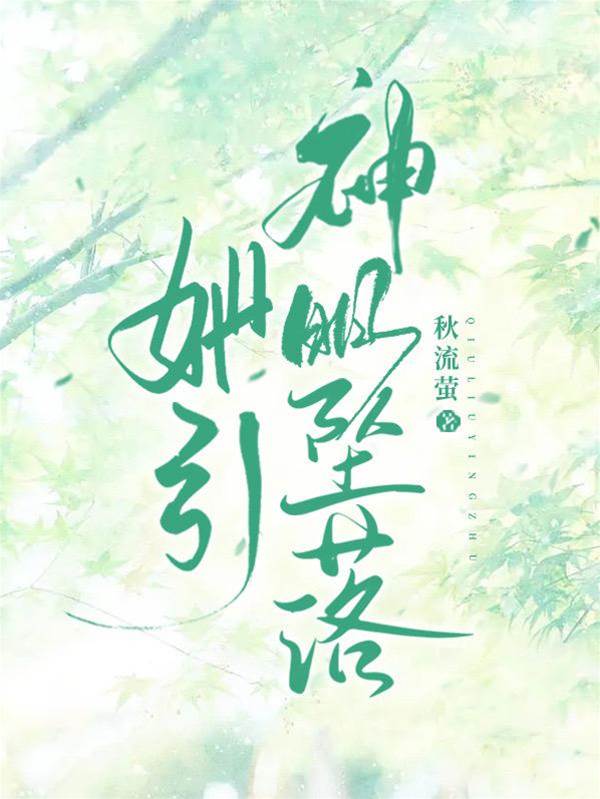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他的替身太太》 第29章 男人哭吧
祁淵母親阮如雪, 曾是一名歌手,年輕時紅極一時,然而很快退, 原因是被人金屋藏了,只給一個人唱歌去了。
而藏的那個人正是祁淵的父親祁景東。
可惜好景不長,在阮如雪有了孕, 夢想做祁太太的時候,祁景東出了真面目, 非但不肯娶,還譏笑的出。
阮如雪大打擊, 一氣之下離開了祁景東。
一個人生下祁淵后,阮如雪將自己的仇恨和全都傳輸給了兒子, 并為他回祁家想盡各種辦法。
但祁景東對這個兒子從不曾正眼瞧過一眼, 更不愿意接納他。
而阮如雪也因此越來越偏激,最終在祁淵14歲那年, 慘禍釀, 阮如雪以死相, 在滿城風雨中, 結束了自己仇恨的一生,也終于為祁淵博到一個認祖歸宗的名分。
療養院里那位銀發老太太正是阮如雪的母親,祁淵的外婆。
在阮如雪自殺后, 老太太也倍打擊, 越來越差,脾氣也越來越差。
祁淵曾把接在邊照顧,但老太太看見祁淵就生氣, 覺得是祁淵毀了兒的一生。
最后自己選擇來療養院, 覺得這里人多, 熱鬧,能讓心開朗。
可事實上古怪暴躁的脾氣,讓周圍的人不敢親近,而大家疏遠時,脾氣則變得更古怪暴躁,如此反復之后,的人際關系便陷進了一個詭異可怕的惡循環當中。
而現在幾乎已經達到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
沈逸矜和馮玲到餐廳門口的時候,里面地上、桌上到是打翻的飯菜,幾個工作人員站在邊上,大氣不敢出,目一致投在銀發老太太和年輕男人上。
Advertisement
老太太坐在餐桌前,中短的白發披散在臉上,沾了一片黃的油漬,可看不見也顧不上,臉上看起來扭曲又痛苦,雙手拉扯著祁淵的服,朝他又喊又,又嚷又哭。
祁淵面對面站在面前,由著胡鬧,只在鬧得停歇的時候,用紙巾給下眼淚,捋一捋的頭發。
這種形,進去用餐未免顯得太打擾,馮玲索倚著門等了等,眼里看去年輕男人,倒是漸漸生出了欣賞。
的視線里是祁淵的背影,男人個子很高,脊背拔寬闊,上的黑長恰到好地勾勒了他完比例的材,而他安老人的作,也顯示出他良好的修養和足夠的耐心。
馮玲轉頭對靠在墻上的沈逸矜說:“我一會去打聽一下他,給你介紹做男朋友怎麼樣?”
沈逸矜一聽,立馬收回游移的目,說:“不好。”
馮玲以為怕難為,鼓勵道:“別不好意思,喜歡就追,孩子也有追求的主權。”
“可他這一款,我不喜歡。”沈逸矜找了個借口。
“不喜歡?”馮玲詫異了下。
忘再大,卻還記得上次沈逸矜來,在臺遠距離地見過這個男人,那時候滿眼小星星,明明是喜歡的意思。
“人是會變的。”沈逸矜低下頭,控制自己的表。
有一刻,想告訴恩師,那男人是誰,和他有過什麼樣的關系,可眼下環境不太合適,遲疑了下,最終還是選擇了沉默。
馮玲看著,憑借這麼多年亦師亦母的關系,捕捉到了眼睫細微下的一抹憂傷。
嘆息了聲,將沈逸矜微涼的手拉在自己邊。
餐廳里,祁淵外婆終于哭得歇止,眾人走上前去準備收拾打掃,誰知外婆抓住祁淵又開始了新一的咒罵。
Advertisement
“你為什麼要給他做手?”外婆嚨都沙啞了,聲音卻一點也沒小,“你有機會分到他的產不就好了?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前途去賭?”
“你知不知道你是你媽拿命才把你博進祁家去的?你搞垮他們家啊,把他們家的錢全卷進自己口袋就好了啊,你救他干什麼?”
沈逸矜和馮玲站在門外,心驚膽跳,離著他們六、七米之遠都聽見了。
沈逸矜也大致聽明白了,祁淵外婆這是為自己兒不值,指著祁淵報仇雪恨,但祁淵令失了,祁淵對祁家沒有仇恨。
外婆抓住祁淵服的一角,使勁推搡拉扯,扯一團皺褶,邊拉邊罵,又邊罵邊哭。
祁淵抱住肩膀,看起來寬容又忍耐,一點脾氣也沒有,他說:“你要相信我,我做得都是有把握的事。”
他抓過老人的雙手,半蹲下:“你有時間為我瞎心,你為你自己多想想行不行?你看你,每次我來你都要把場面搞這樣?你到底還要不要我來?”
外婆手一送,眼珠子怒瞪:“你不想管我了是不是?你嫌棄我老太婆了是不是?”
忽然甩開祁淵的手,捶起自己的口嚎啕大,“我可憐的雪兒,為什麼不肯聽我的話,非要生下這樣的孽子,斷了前程,毀了一生,現在這個不孝兒替人家賣命,替人家著想,都不想管我了。”
祁淵:“……”
祁淵了眉心骨,心比窗外的雨還郁。
門口的兩人面面相覷,沈逸矜說:“我好像也不是很想吃的飯,要不我們還是去樓下普通食堂吧。”
馮玲也不想再進去了,點點頭說:“那走吧,下次再請你來吃。”
兩人穿過門前,往電梯走去,祁淵偏頭,抬眸間,瞥見那袂朝思暮想的影。
Advertisement
一小時后,終于把外婆安好,送回了房間。
祁淵走出門來,問邊的人:“太太走了嗎?”
對方回答:“還在馮老師屋里。”
祁淵猶疑了片刻,想著冒昧去打擾人家不太好,不如守株待兔等著沈逸矜。
他下樓到一樓大廳。
這棟樓不大,電梯下來,只有一個出口,祁淵走到門外,站在屋檐下,耐心等待。
梅雨季的雨沒有春雨那般纏綿,也沒有夏雨那樣的熱烈,更不似秋雨蕭瑟,冬雨冷冽,就是纏人,時而急時而疏,時而狂妄,又時而繾綣,令你恨不能,捉不。
祁淵看著那雨,心也像那雨霧一樣聚了來又散了去,沒辦法安定。
邊人看了下時間,低頭請示:“下午有個重要會議,先生再不走的話,可能要來不及了。”
祁淵回頭看了眼電梯口,有人上有人下,可就是不見他想見的人:“把會議改期。”
他心不在焉。
現在對他來說,再沒有比見上沈逸矜一面更重要的事。
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
邊人說:“先生,你先找個地方坐一會吧,我等著就行,太太下來了,我攔住。”
祁淵站著沒,反問:“一個想道歉的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邊人想了想,回道:“是誠意嗎?”
祁淵抬眸看向屋檐,點了點頭。
他現在就想給沈逸矜這樣一份誠意,誠意到讓到他認錯的態度,讓原諒他,跟他回家。
他甚至有想過,只要肯回家,他就承認自己上了,保證以后不再隨便疑心,給比以前更多的寵。
皇天不負有心人。
祁淵在屋檐下站了兩個多小時,沾染了一“誠意”的雨氣后,終于迎來了需要被他的主。
Advertisement
然而,然而。
沈逸矜出了電梯,手里提著傘,朝大門走來。
祁淵眉梢微不可查地挑起一喜,側過,眸微,用他那低沉的聲音喚了聲:“沈逸矜。”
他知道這是他的必殺技,沈逸矜從來都抵抗不住的。
可是此時,沈逸矜只是微微抬頭,朝他淡掃一眼,打開傘,走了出去。
的腳步幾乎沒有停頓,的微微抬頭,只是為了看天,淡掃他一眼,也似是掃過周圍景,無可避免地才掃過他的。
祁淵一時錯愕,怔怔地看著他期待已久的影漸漸離自己越走越遠。
屋檐下的雨凝聚滾落,比天上直接下下來得大很多,且涼如冰水,落進人心里,猶如寒里的寒,瞬間冰凍了整個人。
祁淵用幾近不確定的聲音,問邊的人:“太太看見我了嗎?”
邊人猶豫了幾秒:“應該看見了吧。”
他只是祁淵邊一個小跟班,只見過沈逸矜一二回,要說沈逸矜忽略他,他完全能理解,可是祁淵是沈逸矜結過婚的人,他們朝夕相過,更是同床共枕過,那眼神,怎麼好像沒看見人似的?
不可能看不見的。
祁淵恍過神來。
只是把他看了陌生人。
“快去老劉開車。”祁淵有點慌。
很快,汽車出了療養院大門,開上道路。
祁淵盯著車窗外,幾個林間彎道后,終于又見到那袂影。
青翠高大的竹林下,風過,雨傾斜,打在黑傘面上,那底下被吹的白角,單薄伶仃得像一朵孱弱的花。
無端端,讓人生出無限憐。
劉司機把車剎停在沈逸矜邊。
沈逸矜低頭看著泥水被胎碾過,濺上的管,就像眼睜睜看著一場事故的發生。
很,無能為力。
祁淵摁下車窗,放聲了聲:“沈逸矜。”
沈逸矜抬起頭頂的雨傘,挪步挪到路沿邊上,繼續往前走。
祁淵只好推開車門下車,卻沒料到,腳剛著地,一陣冷風過,竹林“嘩啦嘩啦”吹起波濤般的響聲,飛灑一片冰涼的豆雨。
祁淵猝不及防被淋了一,嚨口一窒,聲音變了腔調:“矜——矜。”
然而追隨沈逸矜的視線里,不等他走近,闖進來一輛車,停在了勞斯萊斯前面。
沈逸矜停下腳,那冰冷漠然的白像是忽然暖開了似的,朝那車里的人笑了下,拉開副駕駛的門,收了傘坐進去。
祁淵額上碎發,眉間,鼻尖,乃至下頜尖上都掛滿了雨滴,眼神犀利又空,像柱冰雕佇立,腳上再邁不一步。
車里,聞哲語看著后視鏡里漸漸拉距小點的勞斯萊斯,冷哼了聲:“矜矜,好樣的,千萬別對他心,這種人不值得。”
沈逸矜沒接話,低頭看了眼沾上泥點的管,又轉頭看去窗外,說:“先去一趟醫院,藥吃得差不多了,去仙溪鎮如果呆一個月的話,可能不夠吃。”
聞哲語看了一眼,皺了皺眉:“要不要和許醫生約一個深度治療。”
沈逸矜搖頭:“不要。”
聞哲語單手離開方向盤,推了下鼻梁上的金框眼鏡,想到了什麼,說:“如果你不喜歡許醫生,那我們換一個醫生。”
沈逸矜還是搖頭:“我沒事。”
前方出了山林,一片開闊,雨也小了很多。
沈逸矜說:“有些事靠不了別人,相信我,我能自己好起來的。”
聞哲語點頭,鼓勵道:“那是,我們矜矜是最棒的。”
沈逸矜笑:“哥,你別這麼夸人行不行?我不是小孩子了。”
聞哲語仰頭,笑了下:“矜矜長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是大孩子了。”
沈逸矜:“……”
翻了個大白眼丟過去。
到醫院,沒想到許醫生不在,只有一個實習醫生代坐班。
聞哲語給許醫生打了電話,才得知對方去了外地流學,要過兩天才回來,而他和沈逸矜的機票已經訂了明天飛楓城。
這下有點難辦。
許醫生電話里說:“如果急的話,我可以授權給我學生開藥方,祁時夢。我信任,你們也可以信任。”
聞哲語想了下,這是眼下最好的辦法,便答應了,把手機轉給了祁時夢。
祁時夢原本里嚼著口香糖,代坐班的任務就是刷手機,看小說,對人回復:“許醫生不在,有事請過兩天來。“
這下接過手機,聽許醫生說了幾句,立馬端正坐姿,拿了紙巾悄悄吐了口香糖,表認真了起來。
開了電腦,輸沈逸矜的就診id,調出的病歷,在新的記錄里按許醫生說得一個個敲上字,寫下藥方,打印出來。又拍照給許醫生,確認沒問題后,代他簽下了名字。
聞哲語接過方看了看,指著醫生簽名那,說:“請把你的名字也寫一下。”
祁時夢有點不爽,怕事被復雜化:“有許醫生的簽名就夠了。”
可聞哲語職業病,謹小慎微習慣了。
他朝祁時夢笑了下,方按在對方面前不,換了個措詞:“小姐姐長得漂亮又認真負責,給個機會,想看你的名字。”
他語氣溫和,說這樣的話一點輕佻之氣也沒有,加之他長相斯文,文質彬彬,白襯灰西,臉上一副金框眼鏡,怎麼看都是正經人,怎麼都不像調侃虛浪之人。
再多看幾眼,還有清冷貴公子的氣質。
祁時夢邊多得是狂蜂浪蝶,卻沒見過這麼一本正經撥人的,耳子一,拿起筆簽了自己的名字,臉上眼可見的紅了。
沈逸矜隔著辦公桌坐在對面,不計較簽名的事,但不太想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病,而祁時夢是祁時晏的妹妹,也就是祁淵的堂妹,很擔心祁時夢認出自己。
而的擔心一點也沒錯。
沈逸矜和聞哲語出了辦公室,祁時夢就打開手機,給祁時晏發了一條微信,問:【三,你說大哥之前那個帶回家的太太什麼名字?】
祁時晏回復:【怎麼了?】
祁時夢:【是不是沈逸矜?】
祁時晏回了個“對”的表:【你要干嘛?】
祁時夢發了一連串的“哈哈哈哈哈哈”表達興,轉手打開祁淵的微信,先發了一條鉆石手鏈的鏈接,再敲上一句話:【大哥,我有沈逸矜獨家,你要不要?】
猜你喜歡
-
完結431 章

萌寶歸來:爹地放開我媽咪
他冷血無情,隻懂強取豪奪!她被逼無奈,放下傲骨,與他糾葛,踏入豪門。五年後,她攜萌寶歸來,勢要雪恥前仇。萌寶狡詐呆萌,像極了他。“叔叔,你想做我爸比?可你好像不合格。”某男人俯視身邊的女人,“合不合格,隻有你媽咪說了算。”這個男人不但霸道,還寵妻入魔。
78.4萬字8 25363 -
完結955 章

先婚后愛:權少的迷糊小老婆
蘇煙怎麽也想不到交往了四年的男朋友會爲了前途而選擇另壹個世家女,既然這樣,那她選擇放手。 可是對方卻不依不饒,幾次出現在她面前秀恩愛!她忍讓,對方卻越發囂張。 蘇煙:“我已經有男朋友了。”誰知她在馬路上隨便找的男人竟然這麽優質,而且還全力配合她。 她感動的想以身相許,結果人家說,他需要壹個能洗衣做到拖地的人。 蘇煙傻兮兮的被帶回家,發現自己的老公是壹個經常出任務的軍人,而且她什麽都不用做,只要被寵愛就行了! 婆婆:“寶貝兒媳婦,這是婆婆炖了幾小時的湯,快喝。”公公:“妳那些客戶要敢欺負妳,妳就告訴我,我讓他們消失!”老公:“我老婆是我的,妳們誰也別想霸占!”………………婚前:蘇煙:“妳爲什麽幫我。”沈右:“我是軍人,爲人民服務是應該的。”婚後:蘇煙:“妳最喜歡吃什麽。”沈右:“吃妳。”【歡迎跳坑~】
242.7萬字8 42778 -
完結985 章
南方有喬木喬妤
父親年邁,哥哥姐姐相繼出事,24歲的喬家幺女喬妤臨危受命接管風雨飄搖的喬氏。為了保住喬氏,喬妤只好使盡渾身解數攀上南城只手遮天的大人物陸南城。 初見,她美目顧盼流兮, “陸總,您想睡我嗎?” 后來,她拿著手中的懷孕化驗單,囂張問著他, “陸總,娶不娶?” 男人英俊的面容逼近她,黑眸諱莫如深, “這麼迫切地想嫁給我,你確定我要的你能給的起?” 她笑靨如花,“我有什麼給不起?”
229.9萬字8 695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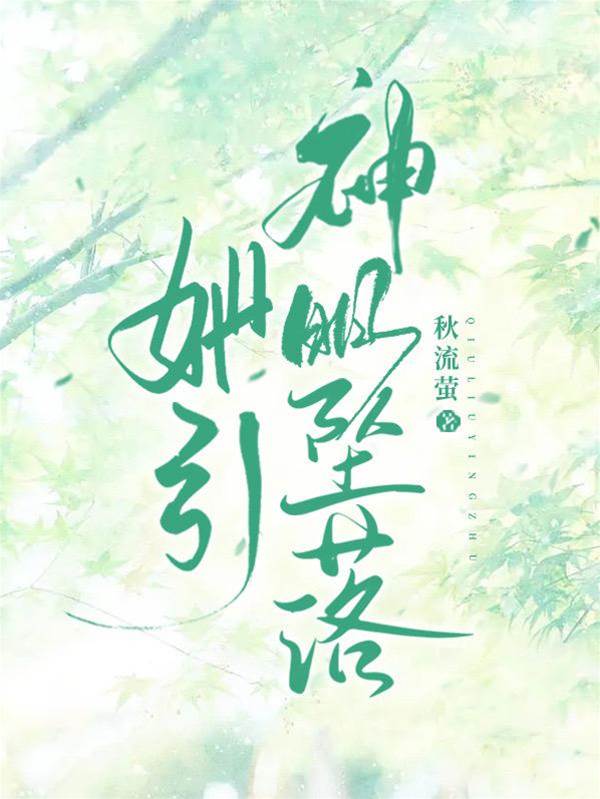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