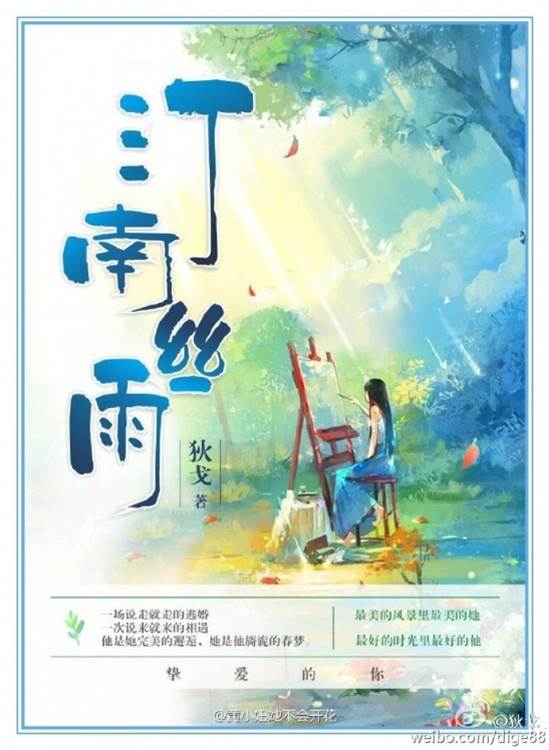《他的替身太太》 第38章 夜夜夜漫長
“……”
“那之后,聽說他每天收到的書都能塞滿一屜。”
夏薇說到這,緒回轉,又哀嘆了聲。
沈逸矜到的心,追問:“那你呢?你沒給他寫書嗎?”
“沒有。”夏薇把臉埋進枕頭里,“我太普通了,長得一般,績一般,我就蕓蕓生中普普通通的那一個,拿什麼給他寫書?”
沈逸矜安:“薇薇,你這是妄自菲薄,不試試你怎麼知道?”
夏薇哼了聲:“那是你不知道,他傷起人來的時候真的做得很絕。”
“怎麼?”
“我們學校進大門的主干道旁有一排梧桐樹,他可以在樹與樹之間拉上繩子,將所有生寫給他的書全部用夾子夾到上面去,拉滿好幾棵樹,場景壯觀,公開刑。”
沈逸矜啊了聲:“這麼絕?不喜歡也不用這麼傷人吧。”
“就是說啊。”夏薇捂了捂心口,想起來還后怕的樣子,“所以啊,好在我沒寫,很多生都哭了,但是也有很多前仆后繼的,反正我是沒那個勇氣去的。”
聯想到祁淵,沈逸矜同:“他們姓祁的,一個個真是自大又自負。”
夏薇說到這,話鋒一轉,問:“我今天聽祁時晏說,祁淵追你追到仙溪鎮去啦,還在那里辦了一場隆重的求婚,花了幾百萬,結果被你打了一頓,還哭了一場,被億萬民眾圍觀?”
“……”
“真的假的,我聽了笑死了。祁淵被你打,我是見識過了,被打到哭,你下手是有多狠啊?”
沈逸矜哭笑不得:“祁時晏跟祁淵關系可真好,這都能逮著機會替他賣慘。祁淵那哪里是求婚,明明是騙婚好嘛。”
“騙婚?”夏薇發出驚奇的聲,來了興致,“快說說,怎麼回事?”
Advertisement
沈逸矜頓了下:“我想想從哪里開始說。”
一向在別人面前很說自己的事,那樣有種把自己私藏的東西給別人檢閱的覺。
而別人不一定會給你有效的意見,更多的是得到你的賣弄或冷嘲熱諷的貶低。
不喜歡這樣的“別人”。
但夏薇不是別人,做室友這麼久,沈逸矜能到的善良與真誠,應該是個值得心的朋友。
沉思片刻,沈逸矜將仙溪鎮的事都說了出來。
夏薇聽著,一會“啊”一聲,一會“啊”一聲,聽到末尾,慨萬千了一番,用語重心長的口吻總結道:“此人值得嫁。”
沈逸矜:“……怎麼這麼說?”
夏薇翻了個,雙手手肘將自己上半支撐起來,面對閨,剖心似的分析了一通。
“首先,一個男人如果喜歡你,他可能會為你花錢,會做些事哄你開心,但是為你哭,全世界幾個男人會?”
“其次,男人的哭點和人不一樣。人的哭點低,只要一點點緒就會哭,但是男人不太容易,何況那個人是祁淵啊,就他現在的地位,財富和他的行事作風,哪一點符合他會哭的形象?”
“他如果不是真實,不是真的痛到了骨子里,是不會哭的。他是真的上你了,很很的那種。”
“啊——”夏薇說完,放下手肘,重新躺平床上,發出長長的一聲嘆,“我要是有個男人肯這樣為我哭,我當場就嫁了,原地結婚。”
沈逸矜半晌沒說話:“……”
正此時,夏薇手機響了下,是祁時晏將今晚的照片發了過來。
當時夏薇因為張,連著拍了很多張,祁時晏也沒挑,一腦地全發來了。
那手機鈴聲一聲接一聲的,堪比驟的心跳聲,激得夏薇不停地“啊啊啊”地狂,手里捧著手機,像捧著自己的小心臟。
Advertisement
沈逸矜趴在旁邊,看著,笑得差點岔氣。
等照片全接收到了,兩個人平復了下心,頭湊頭在被窩里一起看。
祁時晏那人平時很頑劣,今天陪他哥來,一心想給他哥掙分,很是收斂自己,一晚上正正經經的,都沒怎麼說話,倒是在拍照的時候,找到了點樂趣,出了自己的劣。
照片里,他兩只剪刀手故意在夏薇的腦袋兩側,扮的兔耳朵,還有故意做開槍的作對著夏薇腦袋的,更有一張夸張地張大了口,一副喪尸狀要咬夏薇的樣子。
夏薇當時就是被他這些搞怪作搞到張的。
“他真的是太會玩了。”夏薇看著照片,覺自己又被他拿了一遍,面上漲紅。
而照片里的另外一個男人,則和祁時晏完全相反,所有的照片幾乎都是一個表,也不,他所有的視線全都落在了沈逸矜上。
夏薇點評:“看,祁淵這深的眼神,讓我想到一句,‘人就在我面前,可我依然想’。啊啊啊,真的難以想象,他是祁淵啊,商界里都說心狠是他的代名詞,可誰知道他的另一面是這麼深?”
沈逸矜笑了下,說:“你不覺得用‘蠟像’來形容他更準確一點嗎?”
“蠟像?”夏薇大笑,“虧你想得出,矜矜,你太壞了。”
沈逸矜丟開的手機:“睡覺啦,很晚啦,明天還要上班呢。”
夏薇余味十足,可一想到明天上班,頓時垂頭喪氣:“嗚嗚,該死的星期一。”
沈逸矜附和:“我討厭星期一。”
“我不要上班。”
“我要咸魚躺。”
“我要嫁豪門。”
“……我、還是咸魚躺吧。”
夏薇:“來嘛,嫁豪門。”
Advertisement
沈逸矜:“來嘛,咸魚躺。”
“哈哈哈。”
“哈哈哈。”
窗外月如洗,風兒輕輕,吹起人的疲倦,催人眠。
夏薇開了燈睡不著,沈逸矜最后只亮了自己那側的床頭燈,一籠暗淡的昏黃,才夏薇睡著了。
耳邊的呼吸聲漸漸均勻,沈逸矜翻來覆去睡不著,悄悄起了。
出租屋小,除了自己的房間,也沒什麼地方可去,便走進了廚房。
還有兩罐啤酒沒喝完,沈逸矜打開一罐,一口氣灌下去一半。
靠在流理臺前,自己先前站的位置,抬頭間,似乎還能到祁淵就在面前,將擁在懷里,窒息般的錮。
他總是這樣,每次擁抱不用盡他的力量,似乎都不足以表達他的訴求。
仙溪鎮那天,祁淵哭了,是知道的,張熙后來還給發了照片,男人蹲在地上咬著拳頭淚流滿面,手背上咬破的痕目驚心,襯得他上的紅諷刺又悲涼。
當時那照片,看就看了,沒往深里想。
任誰為祁淵哭了這件事震驚,也是無于衷。
可今天聽夏薇這一二三的分析,多多有了些。
但是,那又能怎麼樣呢?
承認那段關系里,除了結束時不太好看,之前一直被照顧得很好,且兩個人相愉快,自己也很開心。
但是,只是將之當一場協議,一場做戲的假婚姻啊。
這樣的人怎麼可能真的和人發生,和人真的步婚姻?
連的干媽都會說,有病啊,從小吃藥的人,生不了孩子的。
祁淵,你去找別人不行嗎?
祁淵說:“不行。”
今夜注定是個無眠之夜。
他在家里和國外幾位心理學專家視頻,分析沈逸矜的病。
Advertisement
專家們表示與病人面對面接治療會更好,被祁淵否決了。
早在從仙溪鎮回來后,祁淵便通過祁時夢約見了許醫生,還去了療養院見了馮玲,再結合聞哲語說的,他全面掌握了沈逸矜的病,知道了的心防有多重,生活上是有多缺乏安全。
而他沒有辦法告訴,他在背后做得這些事,他怕嚇到,怕從此再不理他。
所以,他下了個決定,他要學心理學,自己治療沈逸矜。
電腦里有一份音頻資料包,是仙溪鎮那天的全記錄。其中大部分照片和視頻他都看過,唯獨一份最長最大的視頻他從沒點開過。
那是整場婚禮的突變,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件,也是他最后悔最想抹掉的記憶,以至于他一直沒法面對,沒能直面去接。
此時,他坐在書桌前,面對電腦,眼神凝視那個文件好一會后,手指終于了下,點擊了播放。
畫面里,子掀了自己的紅蓋頭,一紅嫁,溫婉華貴,急怒使臉上緋紅,眉心擰,言語出口時,一雙清絕的眸子里充滿了失,但看得出來,還顧著彼此的面,有所克制。
可在他雙手到時,像是到驚嚇般忽然瞳孔,緒隨之激。
看到這,祁淵按了暫停,支肘敲在自己額頭上,用力了眉心骨。
很明顯,沈逸矜從這里開始排斥他了,憎惡他的,而他卻不知其罪,還妄圖更近一步。
真是一步錯,滿盤皆輸。
再往后,沈逸矜那歇斯底里的哭泣和恐懼充斥了整個書房,祁淵覺自己像握了刀的劊子手,滿口悔恨,卻做著最讓人痛恨的事。
他當時為什麼不能多看看的反應,多為著想?
“我替結婚,替離婚,我們開開心心,好聚好散,不好嗎?你為什麼要那樣對我?”
“我沒了父母,沒有家,我住進你家時我有多開心,你知道嗎?可是,你為什麼要半夜趕我走?你知道我有多害怕無家可歸嗎?”
“為什麼?為什麼?你讓我陷極度的自我否認中,你知不知道?”
祁淵“嚯”一下站起,合上電腦屏幕,面目瞬間沉。
“替結婚,替離婚”,“無家可歸”,“自我否認”一個個字眼沖進他的耳,脹得他顱轟鳴。
字字如劍,像是挑開他脖頸上的脈,劇烈的疼痛伴著窒息一下子堵塞了他的嚨。
祁淵雙手撐在桌沿,艱難地呼吸,口腔里有腥味灌,那是他自己咬破了里的。
無!家!可!歸!
像昏昧世界里進一道,他終于看見了沈逸矜心最弱最恐懼的東西,但那一片卻被他傷害得模糊。
桌上青草綠的陶瓷杯還在,是他現在每天喝水用的杯子。
“祁先生,送你份禮。”
“我為什麼要你的禮?”
“因為有來有往嘛,你送我一個杯子,我也送你一個嘛。”
“我不需要。”
“需要。”
那時候的沈逸矜眉開眼笑,對他還抱有激。
他現在明白了,那是在激他給了一個“家”。
他們明明有著那麼好的過去,卻他的一念之差全毀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38 章
買一送一:首席萌寶俏媽咪
盛安然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陷害,和陌生男人過夜,還懷了孕! 她去醫院,卻告知有人下命,不準她流掉。 十月懷胎,盛安然生孩子九死一生,最後卻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抱走。 數年後她回國,手裡牽著漂亮的小男孩,冇想到卻遇到了正版。 男人拽著她的手臂,怒道:“你竟然敢偷走我的孩子?” 小男孩一把將男人推開,冷冷道:“不準你碰我媽咪,她是我的!”
116.1萬字8.18 310839 -
完結75 章

一見到你呀
1. 向歌當年追周行衍時,曾絞盡腦汁。 快追到手的時候,她拍屁股走人了。 時隔多年,兩個人久別重逢。 蒼天饒過誰,周行衍把她忘了。 2. 向歌愛吃垃圾食品,周行衍作為一個養生派自然向來是不讓她吃的。 終于某天晚上,兩人因為炸雞外賣發生了一次爭吵。 周行衍長睫斂著,語氣微沉:“你要是想氣死我,你就點。” 向歌聞言面上一喜,毫不猶豫直接就掏出手機來,打開APP迅速下單。 “叮鈴”一聲輕脆聲響回蕩在客廳里,支付完畢。 周行衍:“……” * 囂張骨妖艷賤貨x假正經高嶺之花 本文tag—— #十八線小模特逆襲之路##醫生大大你如此欺騙我感情為哪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那些年你造過的孽將來都是要還的##我就承認了我爭寵爭不過炸雞好吧# “一見到你呀。” ——我就想托馬斯全旋側身旋轉三周半接720度轉體后空翻劈著叉跟你接個吻。
21萬字8 9512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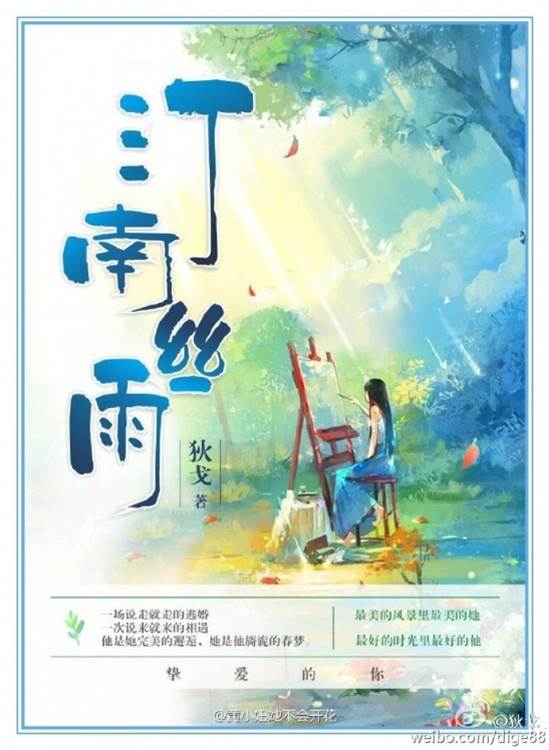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