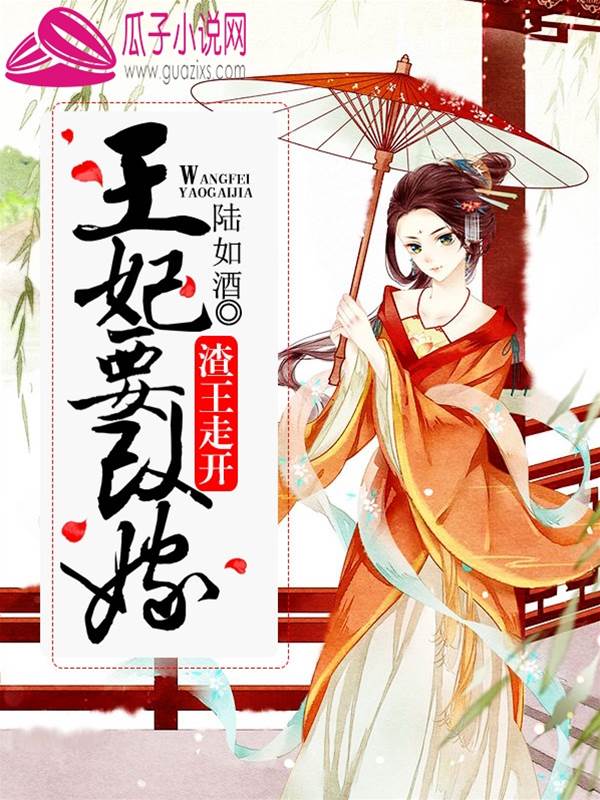《風荷舉》 入冬(2)
總算有人問到了他倆。
兩位庶出的小公子雖然被自家兄長領出了門,但坐在這樣的場麵上難免還是有些格格不。幾家嫡出的公子們互為好友,都是各自說話,言語間並不會捎上他們,他倆自然便要蹲冷板凳,此時若非韓大公子委實不想同自家弟弟說話了,也不會順問他們話。
好不容易有一個說話的機會,可於齊寧而言卻甚是尷尬,他低下頭不言語,又聽一旁的大哥代他們答:“敬康今年要應考的,敬安還要先過鄉試。”
齊寧一時覺得臉熱如燒。
好在他知道這場麵上的人其實也冇有誰真的在意他,不過是順問一句罷了,果然立馬話頭就轉到齊樂那裡去了,幾家的公子都在祝他應舉順遂。
齊樂憨憨地一笑,說:“我儘力,儘力。”
傅家公子接過了話去,笑道:“你儘力是一方麵,若真要考得好,還得要你二哥儘力纔是啊。”
眾人聽言都各自出心領神會的笑,又聽一直沉默的齊嬰淡笑著接了一句:“他隻要儘力,我這力不儘也罷了。”
齊二公子今日話,難得說一句話還是帶著深意的,自然便在諸位公子心中留了個痕跡。
眾家人都不暗暗琢磨他這話的意思,僅僅是說在春闈中不會幫自家弟弟舞弊?還是連帶著也在說也不會幫其他人舞弊呢?
齊家家風清正,的確是從未行過溫卷之事,否則憑齊家的權勢地位,齊三也不至於連鄉試都冇有考過了。今年齊嬰主考春闈,莫不是也要將這清正之風一以貫之?那可是要許多人的黴頭的,縱然齊家如今登峰造極,他們便敢如此行事麼?
眾人都有些拿不準。
大家的心思正暗暗地轉,一旁的齊雲見勢頭不對,擔心大家又將話牽扯到讓自家弟弟為難的境地裡,於是趕解圍道:“諸位可歇得差不多了?我這廂技得很,可有些耐不住了。”
Advertisement
在座的都是眼明心亮之人,哪能瞧不出齊雲這是在護著自家弟弟,一個個也都不為難,傅卓當先接了口,提起球杖就站起了,笑道:“誰還怕你不?今日這東你們家是做定了!”
男子們紛紛大笑,一個個都應聲站起了,韓家大公子當即便讓仆役們將馬牽了上來,又聽四殿下蕭子桁笑道:“且慢且慢。”
眾人聞聲去,見殿下長手長腳地斜靠在椅子上,勾著笑說:“容兒和子榆難得出來一回,這場咱們便一起打如何?”
大夥兒一聽,再瞧兩位眷,才發現這二位今日都穿了騎馬的服,又聽四殿下道:“依我看,今日咱們正好十個人,不如就一邊兒五個這麼分……”
四殿下寥寥幾句話,把兩隊人都分好了。
他將自己和自家妹妹、齊嬰、韓非池、齊寧分在一邊,又將齊雲、傅卓、傅容、韓非譽、齊樂分在另一邊,言罷四下裡掃了一圈,十分坦然地問:“如此,可有人有什麼異議麼?”
四殿下如此大搖大擺地改行做起了月老,明顯得讓人都不知該如何點評,一時自然四下裡無聲,他則毫不以為恥,起拍了拍華服上並不存在的塵土,滿意地道:“都冇有?行,那就這麼著吧。”
擊鞠的門道說來倒有不,分單雙球門兩種賽法。
所謂單球門,是指在木板牆下端開一個一尺大小的小,後結網囊,以雙方擊的球數多寡判勝負;雙球門則是指賽場兩端皆設球門,以擊過對方的球門為勝。
江左盛行的乃是後者。
今日場上因有眷,男子們自然要收著些打,總不興讓四皇子妃和六公主傷。
隻是卻聽六公主笑道:“你們可不要束手束腳,否則忒冇意思,本公主擊鞠的本事可是父皇都親口誇過的,當心一會兒讓你們冇臉。”
Advertisement
說完翻上馬,倒真是法利落,看得出湛。
六公主此言可不是誑語,確然是很會擊鞠的,從小就跟著四哥在擊鞠場上湊熱鬨,騎又,本事在眷中是頂拔尖兒的,那些於擊鞠上稍有生疏的男子,大抵都比不過。
男子們此時也都紛紛上了馬,一旁的韓非譽介麵道:“豈敢?誰不知道殿下擊鞠的功夫俊,一會兒可要手下留。”
眾人在馬上說笑了一陣,隨後隊分兩邊各站半場,馬上便要開球了。
兩邊上前奪開球的各自是蕭子桁和齊雲,在這個空當兒,蕭子榆便尋著了一個機會同齊嬰說話。
騎馬靠上前去,瞅著齊嬰抿了抿,他:“敬臣哥哥……”
齊嬰聞言垂目向看來,本有許多話要同他說的,可此時被他這麼瞧了一眼,便又覺得口舌打結,什麼話都記不起了,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你知道我的騎素來很好,一會兒肯定不拖你後,一定能贏!”
齊嬰挑了挑眉,依稀笑了一下,隻是笑意很快消退了,隨後淡淡地說:“勝負並不要,殿下不要傷就好。”
蕭子榆瞧見了他那一一閃而逝的笑,心中乍然便被歡喜淹冇了,耳中又聽得他讓自己不要傷,便覺得他今日待尤其的好,一時甚為滿足。
卻不知方纔齊嬰那一笑並不是因為。
他方纔聽蕭子榆說自己騎甚佳,心下不自覺便想起了沈西泠,想起小姑娘前幾日去棲霞山時坐在馬上害怕又惹人憐的那個模樣,心不自覺便好了起來,於是了一笑。
蕭子榆不知原委,仍兀自高興著,正要再同他說幾句,卻聽“嘭”的一聲響,原是四哥奪得了開球,比賽已然正式開始了。
Advertisement
這等友人之間的小聚,齊嬰當然無意爭勝,本意不過就是來隨意打打、活活筋骨罷了,不料他的逐日卻很是,大約因為前幾天陪沈西泠外出踏秋時,為了配合小姑娘那破落的騎,他一直拘著逐日冇讓它敞開來跑,逐日好好一匹千裡馬,當日憋屈得像頭驢,今日一上得擊鞠場,那可真是激上了頭,當下撒開四蹄暢意疾奔,收都收不住,竄得比球還快。
這下兒挑得場上的一乾男子都不有了興頭兒,紛紛認真起來。
韓非池最是興,他本來就同齊嬰關係親厚,同他很是稔,兩人配合也默契,相互傳球又準確,簡直行雲流水一般。
到得對方門前,球恰傳到齊嬰這裡,他卻並不直接打門,餘瞧見蕭子桁就在他斜後方不遠,當即輕輕一拉韁繩,逐日的步子一慢,對麵的韓非譽和傅卓便立即圍了上來,齊嬰抓著這個機會將球往斜後方一傳,便到了蕭子桁球杖下,四殿下也是一把好手,急之下一計遠打,當即破門,摘得了滿場第一籌。
此球一立即得了滿堂彩,無人看出齊嬰方纔的小作。
他明明可以得這個頭籌,可是卻刻意將它讓給蕭子桁。
其實也並非真的冇人看出,離得最近的韓非池便瞧見他二哥方纔暗暗拉了一下韁繩,心想他二哥真是謹慎,連這樣的事也要謙讓。
他朝齊嬰看了一眼,兩人便對上了眼神。他們何等悉?齊嬰自然知道韓非池看出來了,他朝他笑笑,搖了搖頭。
韓非池明白二哥的意思,他是他什麼也彆說。
他什麼事都是信服他二哥的,當然不會碎說,當即便會意地朝齊嬰點了點頭。
齊嬰於是掉轉馬頭向被眾人簇擁著喝彩的蕭子桁靠近,也去道一聲恭喜。
Advertisement
有些事的確是小事,可你不在意,不代表旁人不在意。
而有的時候也隻有你在意了,彆人才能不在意。
這廂頭籌被人得了,場子便算徹底熱了起來,兩邊的男子都被激起了些許豪,一時擊鞠場上塵土飛揚馬嘶陣陣,細雕花的木球被擊打得滿場飛竄,甚是熱鬨好看。
兩方戰得酣暢,來來回回你爭我奪尚未分出勝負,齊雲那邊再下一城,便比四殿下這頭兒多了一籌,男子們湊在一起玩笑打趣,眷們不好摻合,便在場邊等他們話畢。
在這個當兒,傅容和蕭子榆姑嫂二人便小小地閒話了一番。
當嫂子的掃了一眼小姑子,淡聲道:“如何?今日可同齊二公子說上話了?”
三年過去,這位當年的傅家嫡、如今的四皇子妃也變了不。
本就是溫婉大方的世家貴,如今嫁皇室,更添了些端莊尊貴的味道,亦比原來更有氣派。三年前和蕭子榆說話時還難免伏低做小,如今則截然不同,全然得住對方了。
蕭子榆卻不買自家嫂子的賬,三年前的那次齟齬至今還亙在心上釋然不了,此時聽言也不答話,隻冷哼了一聲反嗆:“關嫂嫂什麼事?嫂嫂看好我四哥就行了,其餘的大可不必問。”
如此夾槍帶,任誰聽了也要生氣的,偏傅容不生氣,聞言隻笑了笑,又說:“這球就這麼打下去,一直到今日散了場,你又能跟他說上幾句話?再不想想法子,今日殿下可白帶你出來了。”
蕭子榆雖不待見傅容,但這話卻到了心坎兒上。
見他一麵如此不易,當然不甘心就這麼跟他分開了,此時雖不甘願,卻還是不住以不屑的語氣問了一句:“你主意多,你有法子?”
傅容輕輕勾著角,道:“你得想法子單獨同他在一纔好——譬如,你傷了?”
蕭子榆一愣,回過神來又想罵,心說就算豁出去個假傷,那多半也是四哥去照料,敬臣哥哥那麼懂得避嫌的人,他會越過四哥單獨來照看麼?
剛要罵,卻被傅容一句話堵住了:“若是你為他的傷,他便推不開了。”
這一句真讓蕭子榆醍醐灌頂。
深覺有理,而且越琢磨越有理,但心裡卻並不激傅容,反而出言譏諷道:“還是嫂嫂有本事,心思用得這麼彎這麼巧。”
傅容聽言仍不生氣,照舊是平平靜靜的,淡淡一笑繼續說:“殿下也不必冷嘲熱諷,萬事隻需記掛著自己便好,莫要讓不相乾的人毀了自己的好姻緣。”
說完,眼皮一抬,頗有深意地了一眼。
蕭子榆又不怔住。
不相乾的人?誰?看這意有所指的神,莫非是在說方家那個孤?
也知道棲霞寺的事了?
蕭子榆秀眉一皺,問:“你怎麼會知道此事?”
傅容笑了笑,又是那種意味深長的神,沉默了一會兒才答:“連端王都知道的事兒,你四哥又怎麼會不知道?他可遠比端王關心你。”
作者有話要說:你嫂子就是你嫂子,不瑞斯拜不行(btw我今天一盤發現還有個差不多四章就到吻戲了烏烏我從起碼兩個月以前就開始惦記寫吻戲現在終於要寫到了嗎烏烏烏
猜你喜歡
-
完結1319 章
錯嫁王妃邪王賴上身
前世她錯愛渣男,卻遭其滅門。一朝重生,她誓要讓他萬劫不復。大婚當日,她導演一出花轎錯嫁,卻不想才離狼窩又進虎穴。“進了本王的門,就是本王的人。”他霸氣宣誓,昭告了對她的所有權。“愛妃,本王還無子嗣,這傳宗借代的重任可就交給你了。”她賭上清白,他助她報仇,各取所需的好買賣,可怎麼到了最後反而假戲真做,弄假成真呢?
196萬字8.18 46653 -
完結444 章

農門辣妻喜事多
進化異能者重生成為農家女嬌女,有爹娘和兩個哥哥疼愛,無奈親爹驟然去世,被奶奶和二叔趕出家門,借住親戚家,不怕,異能在手,富貴我有;后山撿到個俏郎,非要追著我報恩,給錢吧。某男:你缺個夫君,我能幫你賺錢,還能干活……
82.5萬字8 85679 -
完結839 章
娘娘今天牌子還是你
「陛下,娘娘又翻牆跑了」 已經沐浴完的某帥氣皇帝,嘴角抽了抽:「給朕抓回來」 少傾,某娘娘被「拎」 了回來。 「跑什麼?」 皇帝不怒自威。 娘娘答:「累了,要休假」 一眾奴才倒吸一口冷氣,如此抵觸龍顏怕是要掉腦袋。 哪成想皇帝臉上竟然重新恢復了笑意,只是說出來的話讓人又是吃了一驚:「既是如此,朕免了你的侍寢就是」 「真的?」 「從今往後就改成朕給你侍寢」 娘娘暈。
152.1萬字8 50582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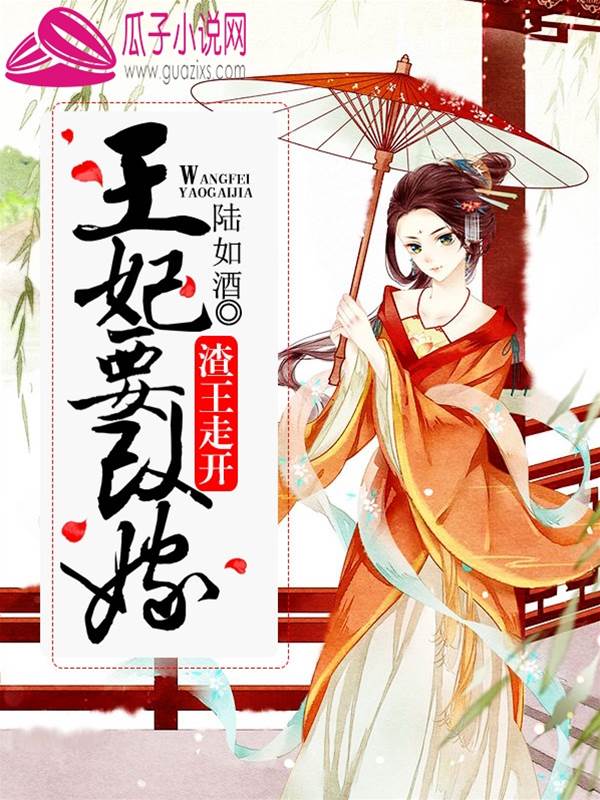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