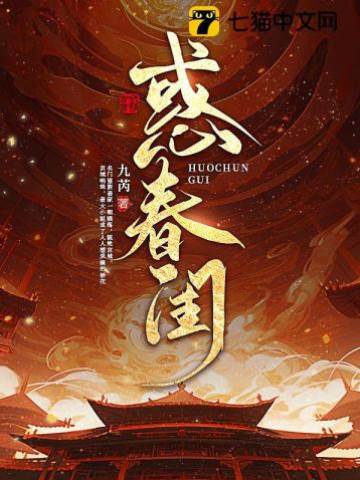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將軍打臉日常》 第28章 江暉成,我們退婚吧(女……
屋外的江大爺, 背心已經冒出了冷汗。
江暉為江府二公子,飽讀詩書,恪守禮儀, 一向慎言慎行,今兒個這是怎的了。
這還未親呢, 孩子都給搬出來了......
什麼恕難從命,他八是瘋了。
江大爺再也沒有忍住, 生怕江暉又說出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 一把推開了跟前的公公, 闖了進來, 進屋先對著上位的皇上和皇后行了跪禮。
“二弟剛從幽州回來,腦子是急糊涂了,還陛下, 娘娘開恩。”江大爺磕完頭, 起想拉著江暉出去,拽了一下沒拽,急得咬牙,張地瞅了一眼上位沉默著的兩人,只得小聲湊在江暉的耳邊道,“沈四姑娘是自個兒找了董太醫遞上的名字,不關陛下和娘娘的事......”
江暉的眼珠子這才了。
從收到醫者名單, 江暉便離開了幽州,花了三天三夜, 路上跑死了三匹馬, 才趕到皇宮,向皇上討要一個說法。
上的鎧甲被雪水侵,又被風吹干, 一狼狽不堪,面容也憔悴。
唯獨那雙眸子堅定深邃。
江大爺見他了過來,趁著皇上還未開口治罪,趕將人給拉了出去,“你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抵不過你今兒這番找死的言論......”
后書房好一陣安靜。
半晌,皇后終于回過神來,突地一聲笑,“當初陛下要娶我時,我問他,該怎麼辦,他說他一介書生怎敢同陛下相爭,江家勢單力薄,怕日后保護不了我,如今這不是也能好好地去保護人嗎。”
今兒他這一番話,可謂是將江家和他自己之前所有的功勞,打了個大大的折扣。
Advertisement
他就不怕連累了江家。
皇上轉過頭,目盯著皇后,臉上的神實在說不上好,“他江暉不將朕放在眼里,你也當朕是死了。”
皇后回頭,子一歪,也不分場合地歪在了皇上懷里,“人言道,宰相肚子能撐船,更何況陛下還是一國之主,陛下何時見過他如此著急過,不就是知道幽州八保不住了,心疼他未過門的小媳婦兒,從幽州到長安,只花了三日,就算是八百里加急,怕是也沒他跑得這麼快......”
皇上知道是什麼心思,“行了,朕要治他罪,也得等到幽州的事解決了再說。”
皇后當下在他臉上了一口,“陛下英明。”
**
江大爺一路拉著江暉快步走出了主殿,想起他說的那通混話,還心有余悸,忍不住一通念叨,“幽州的形勢當真如此不容樂觀?父親幾日前已經出發去接替你了,你怎的提前回來了,我聽說遼軍已經退了,幽州的那毒,到底是什麼況......”
江大爺實屬有一肚子的話要問,江暉卻一聲不吭。
走到殿外,江暉從槐明手中接過韁繩,才回頭看著江大爺道,“今兒我所言并非糊涂,幽州一事,我不打算再手,沈家人也不會前去。”
今生幽州如何,百姓如何,都同他沒有任何關系。
從幽州開始出現第一個患者開始,他便意識到了,前世的那場瘟疫,不知為何竟然提前了八年。
或許是因為自己在百花谷并沒有傷,提前接替薛家的人到了幽州,有了前世的記憶,也知道了三皇子的弱點在哪兒,只取了他的命。
卻不知道他越是想提前結束這一切,災難來得越快。
重來一回,還是沒能逃過,前世的那一場瘟疫。
Advertisement
如今幽州已經被他給封住了,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圍城,江暉又看了一眼跟前一臉驚愕的江大爺,沉聲道,“誰也救不了幽州。”
等江大爺反應過來,江暉已經翻上了馬,趕也從小廝手里接過韁繩,急急忙忙地跟上。
**
大安好了嫣姐兒,再趕回東院,沈煙冉已經不在那了。
屋里的小廝說,“沈姑娘適才在這打了個盹兒,醒來后似乎子有些不適,先回了院子。”
大一愣,這幾日天冷,莫不是今兒拉著出來,又凍著了?
大轉便去了隔壁的院子,才走了一半,后一丫鬟匆匆追了上來,遠遠地便喚了一聲,稟報道,“大爺和侯爺都回來了。”
自江暉被封為侯爺后,府上的下人們也慢慢地改了口。
大的腳步立馬頓住,掉頭就往前院趕。
幽州的消息,一個一個地傳出來,沒一個好的。
小叔子今兒突然趕回來,又急急地去了皇宮,怕是出了什麼事,若非大事,槐明不會往屋里帶信,讓大爺跟著一道過去。
等大到了前院,江暉已經進屋坐在了江夫人的旁。
倒也不似大心頭擔心的那般,兩人和悅地正說著話。
江大爺也在,坐在一旁默不作聲,見大進來了,抬頭了一眼,那眸子里的神倒是讓大的心頭又跳了起來。
“雖說我江家一門世代都是名門武將,可誰又能保證長盛不衰,花無百日紅,江家也總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在戰場上,先前你決心棄文從武,一心要耀江家的門楣時,我就同你說過了,為娘的心頭什麼都不盼,就盼著你和你大哥一家子平平安安,你三弟已經先下去了,你們要是再有個三長兩短,你我如何能安生?”
Advertisement
江夫人輕嘆了一聲,轉過頭又看了一眼一語不發的大爺,“哥兒說的也沒錯,要說我江家死在戰場上的祖先,十個手指頭也掰不過來,今兒說出來了也好,咱們橫豎就得罪這一回,什麼侯爺,將軍,江家祖祖輩輩還了當封爵的?這麼多年了,江家唯獨缺的就是一份安穩,這回等你父親回來,咱也去同林家好生說說,能不能讓江家先暫且歇歇......”
大聽得云里霧里的,可也知道是出了什麼事兒。
江大爺知道母親自來護著二弟,當下了鼻尖,笑著道,“母親,二弟剛才回來,先且更,有什麼事,過后咱再慢慢說。”
江夫人這才收了話頭,輕輕地拍了拍江暉的肩膀,“你先回東院,換裳,今兒你和冉姐兒的婚服都送府上來了,冉姐兒才試過,你嫂子說,得不可方,冉姐兒卻嫌棄你收藏好的那些珠子鑲嵌多了,說沉得慌,待會兒你收拾好了,便過去看看,就挨著你東院的那隔壁院子......”
江暉染了一路的風霜,一張臉笑起來,角扯得有些生。
“好。”
江暉起,從老夫人屋里出來,腳步穿過長廊,不覺快了起來。
自上次在芙蓉城一別,已經有四個多月了,也不知道是胖了還是瘦了。
那樣的人,吃東西不多,當也胖不到哪里去。
如今知道人就在自個兒的府上,此時離自己不過隔了幾個院廊,江暉角終是忍不住,掛著一道的笑容,抬頭往前方的屋檐上瞧了一眼,倒是想就這般尋過去,又怕見了自個兒的邋遢模樣。
腳步匆匆地回到東院,洗了個澡,換了一深藍錦緞長袍,外披褐大氅,再從院里出來,一干凈,英俊風流。
Advertisement
影穿過游廊,下了月門,映照在穿堂積起來的一層白雪上,泛出了稀薄的線。
江暉一步踏出去,從穿堂下來,腳步很快上了廂房的臺階,等上最后一步時,卻突地又慢了下來。
房門沒關,虛掩著。
立在門前的丫鬟,齊齊行禮,喚了一聲,“侯爺。”
江暉推門而。
屋的一道屏風繡的是一副山鳥圖,高山濃霧繚繞,鳥雀環繞著山頂盤旋。
一針一線繡得栩栩如生,江暉卻毫沒去注意,眸子過那細細的針線小孔,看著里頭那道約約的人影,慢慢地繞過了屏風。
沈煙冉一直坐在榻上,旁的榻幾還擱著剛試過還未還回去的嫁。
屋子里異常的安靜。
安杏原本跪在沈煙冉跟前,聽到門口丫鬟們的聲音,才起立了起來,欣喜地看向了江暉,還是習慣喚他一聲,“將軍。”
“下去吧。”
江暉早早就看見了跟前微微轉過一邊的半張側臉。
倒也沒變......
安杏出去掩好了門,江暉住心頭那快要跳出來的思念,緩步走到了偏過頭的那邊榻上,傾下子,笑了笑問道,“還習慣嗎?”
聲音低沉,又不失溫。
沈煙冉這才緩緩地抬起了頭。
早上沈煙冉起來,嫌悶,讓安杏將屋的窗口都撐開了一半,此時屋外的線照進來,清晰地落在那張瑩白的臉上。
眉眼如畫,瑩白干凈。
唯獨那雙眸子,與江暉離開芙蓉城時瞧見的有所不同。
清的瞳孔,如同飄進了一片雪花,化了寒水,在那眼底蔓延開來,霧蒙蒙的,卻又著讓人發的寒涼。
周遭一瞬安靜下來,聽不到任何聲音。
江暉眼皮子猛地一跳,圍城的那日,立在火爐邊上,同他說出“和離”時,便是如此看著他的。
平靜中帶了一抹清冷。
沒有半。
那道漠然平靜的目,曾經刻在江暉的腦子里,久久都揮之不去。
江暉角的笑容慢慢地凝在了邊,心口一點一點地收,不知不覺背心的一涼意,擴散至周。
卻又覺得荒唐。
不可能知道,怎麼可能知道......
江暉的角輕輕地了,眼里的慌明擺著顯了出來,卻還是強裝出了微笑,低聲問,“我給你的信都收到了嗎。”
“聽說芙蓉城下了一場大雪,你一路過來,路上當也不好走。”
“長安冷嗎?”
“母親可有帶你去長安城里逛過?你習慣了芙蓉城的口味,不知道吃不吃得慣長安的飯菜,長安的偏甜......”
江暉看著眼前那張毫完全沒有容的臉,語速漸漸的變快,最后終于被那眸子里的冷意和了然,得崩塌。
江暉努力地住心口的恐慌,目落下,看著榻幾上擱置的那套嫁,紅艷艷的芒刺進瞳仁,頭一滾,艱難地道,“嫂子說你今兒個試穿了嫁,很是好看,唯獨嫌棄上頭的珠子太過于沉重,我倒覺得嫁鑲些珠子好些,紅彤彤的珠子,像極了紅豆,我四去尋才尋了這些來,讓母親找了長安城里最好的工匠,都給你鑲在了嫁上。”
紅豆骰子安玲瓏,骨相思知不知。
前世他去幽州的那兩年,給他的一封信里,便寫上了這一句詩詞。
那是猶豫了好久,扔了又寫,寫了又扔,才鼓起勇氣,將信給了安杏,終究是寄了出去。
卻也如同以往的信件一般,石沉大海。
沈煙冉的眼瞼終于了,轉頭看著窗外的白雪,開口道,“將軍,你不該來找我。”
江暉的心口猛地一落。
這一句話徹底地碎了他心頭最后的一僥幸,也撕掉了他這輩子努力所飾的一切。
沈煙冉知道他比自己先記了起來。
是以,在百花谷,他才會認出自己。
也早早知道了在百花谷底咬他的那條蛇有毒。
卻又因為前世自己的死,心生了愧疚,他不得不再一次來補償自己,甚至去求皇上,要了一道他們的婚書。
其實沒必要......
如今終于知道,上輩子他之所以會中毒,是因為自己。
如此算來,救他并非有恩,而是自己欠了他。
好不容易,重新活過了一輩子,他不該再來找,沈煙冉抱歉地道,“我已經讓將軍委曲求全的一世,將軍記起這些時,就不應該再來找我,將軍應該好好地為自己活一回,而不過再被恩和愧疚所困,將軍心里應該知道,你其實并不欠我什......”
“我同你親,并非是恩。”江暉突地打斷他。
屋子里又是一陣安靜。
那話同前世八年兩人相敬如賓的日子相比,顯得蒼白又無力。
沈煙冉頓了一下,稍微換了換氣息,回過頭喚出了他的名字,“江暉,我們退婚吧。”
上輩子沒能及時放手,捆住了他也沒能放過自己。
重新活過,又怎可能再同自己過不去。
“將軍不必疚,前世我的死與將軍并沒有什麼關系,站在城樓上的那一刻,我心里已經不再喜歡將軍了,我能跳下去,也并非是為了將軍一人,而是為了江府,江府世代忠良,為大周立下過無數的汗馬功勞,我們還有兩個孩子,他們還是孩,不能因為你我的沖,日后讓他們永世都背負一個弒殺百姓的罪名,我也不怪將軍,我是孩子的娘,將軍自是想要救我,可那時只有我死了,局勢才能破,死之前,我也想過了,若真還有下輩子,我一定不要再遇到將軍,不遇上將軍,或許我們的結局就會完全不一樣。”
江暉的嚨一直繃得的,一口氣遲遲無法咽哽下去。
心口的疼痛劇烈,如同被一把利劍穿過,終究還是跌了噩夢之中。
“你答應過,會等我回來......”江暉著實沒繃住,聲音低沉沙啞,眸子里的一滴水珠落下來,滴在了他握住的拳心。
四個多月前,在芙蓉城沈家,確實答應過他。
可那算不了數。
沈煙冉偏過頭,又將目向了窗外,“上一世將軍的恩,于我而言便是一把割的刀子,今世將軍莫非又要用上一份愧疚,讓你我再次捆綁在一起,又去步了前世的后塵......”
猜你喜歡
-
完結869 章
重生之妖嬈毒後
這個是一個被渣男和渣女算計之後,奮起反擊,報復過後,卻意外重生,活出錦繡人生,收穫真愛的故事。蕭家嫡女,風華絕代,妖嬈嫵媚,癡戀太子。二人郎才女貌,乃是天作之合。十年夫妻,蕭紫語殫精極慮,傾盡蕭家一切,輔佐夫君,清除了一切障礙,終於登上了皇位。卻不料十年夫妻,十年恩愛,只是一場笑話。只是寧負天下人
407萬字8 84134 -
完結141 章

替嫁以后
瑩月出嫁了。 哦,錯了,是替嫁。 圍繞著她的替嫁,心計與心機開始輪番登場, 作為一群聰明人里唯一的一只小白兔, 瑩月安坐在宅斗界的底層,略捉急。
43.2萬字8.09 33001 -
完結816 章

回眸醫笑,朕的皇后惹不起
原本是現代一名好好的外科醫生,怎料穿到了一本古言書中,還好死不死的成了女主!哼哼,我可不是書里那個有受虐傾向的無能傻白甜,既然成了主角,那就掀他個天翻地覆吧!只是……這個帝王貌似對我有些別樣的“寵”啊!…
146.8萬字8 9032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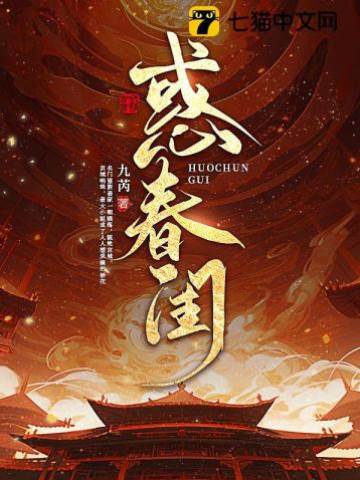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256 章

誘妻為寵/溺寵為妻
蘇語凝成親那日,鑼鼓喧天。 謝予安目送着大紅花轎擡着她進了大哥的院子,他竭力忽視着心口的窒悶,一遍遍地告訴自己——解脫了。 那個連他名字都叫不清楚的傻子,以後再也不會糾纏於他了。 直到有一日,他看到小傻子依偎在他大哥懷裏,羞赧細語道:“喜歡夫君。” 謝予安徹底繃斷了理智,她怎麼會懂什麼叫喜歡!她只是個傻子! 他終於後悔了,懷着卑劣、萬劫不復的心思,小心翼翼幾近哀求地喚她,妄想她能再如從前一般對他。 然而,從前那個時時追着他身後的小傻子,卻再也不肯施捨他一眼。 **** 人人都道蘇語凝是癡兒,可在謝蘊清眼中,她只是純稚的如同一張白紙。 而這張紙上該有什麼,皆由他說了算。 謝蘊清:“乖,叫夫君。” 蘇語凝懵懂的看着他,甜甜開口:“夫君。”
40.4萬字8.18 44669 -
連載2247 章

乖,叫皇叔
【重生】【高度甜寵】【男強女強】【雙向暗戀】重生后的虞清歡覺得,埋頭苦干不如抱人大腿,第一次見到長孫燾,她就擲地有聲地宣誓:“我要做你心尖尖上的人。” 大秦最有權勢的王不屑:“做本王的女人,要配得上本王才行。” 結果,虞清歡還沒勾勾小指頭,某人就把她寵成京城里最囂張的王妃,連皇后都要忌憚三分。 虞清歡:夫君,虞家的人欺負我。 長孫燾:虞相,我們談談。 虞清歡:夫君,皇后娘娘兇我。 長孫燾:皇嫂,你放肆了。 虞清歡:夫君,有人覬覦你的美色。 長孫燾:小歡歡乖,讓本王進屋給你跪釘子。
358.4萬字8 58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