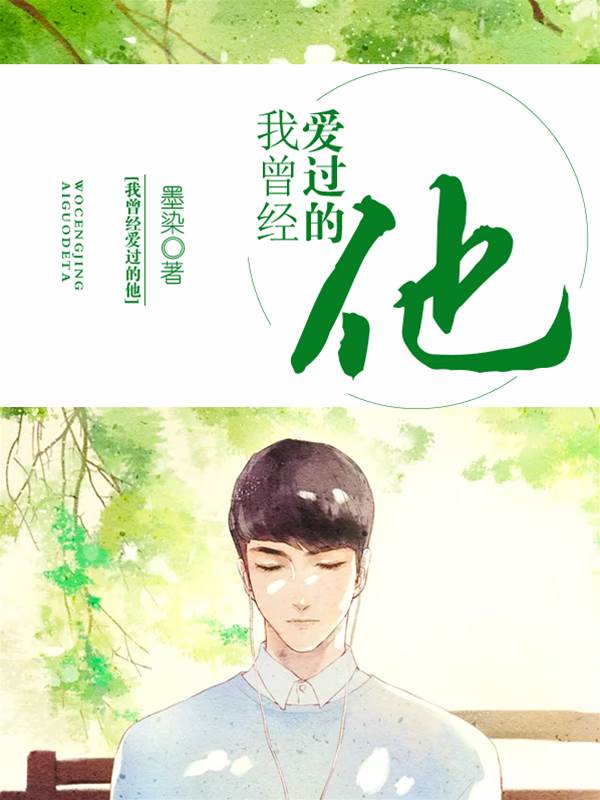《八零之改嫁隔壁老王》 第 130 章
林榮棠和王秀出去后,屋子里總算有了靜。
聲音很低,低到全都是氣音。
“走了,沒事了,咱繼續咱的。”人的聲音比水,比花。
“這,這行嗎,這萬一回來呢,不是撞上咱了!”男人著聲,戰戰兢兢的。
“你怕啥?你就這點膽子,你還是個男人嗎?”
“嫂子,我——”
“怎麼,你不想要我了?”
“我要,我當然要!”
人便笑了,幽暗的窗子,發出來窸窸窣窣的聲音。
“劉鐵柱,你這個傻瓜有心沒膽,你都要了我子,一次也是要,兩次也是要,怎麼就不敢了呢?”
“嫂子,我就是怕榮棠哥,他如果知道了,事就大了!”
人越發笑起來,笑得余音。
“你想要,就趕上,你不想要,就給我滾下炕。”
黑暗中,便有了男人呼哧的聲音,像一頭負重的老牛。
之后,猛地,傳來沉悶之聲,伴隨著的是人的一聲舒暢。
***********
林榮棠和自己娘說話,說了很久,才慢悠悠地回家。
回到自家胡同的時候,沈烈家已經安靜下來了。
他沉默地站在沈烈家大門口,里面并沒什麼靜。
也許是聽不到,也許是本沒有。
冬麥懷上了,肚子那麼大了,兩個人當然消停了,也不會有靜。
林榮棠想起之前他看到的,那個站在窗戶前半趴著的冬麥,一頭黑發像黑緞子一樣,在月亮底下發。
也許就是那樣的夜晚,就是那樣的沉迷,才有了沈烈的孩子吧。
他低下頭,走進了自家門,自家門前也沒什麼靜了。
他走進屋子,黑暗中,聽到了炕上有人氣的聲音。
他便拉了燈繩。
Advertisement
“啪”的一聲,屋子里明亮起來,他清楚地看到了那個人。
頭發散在白底藍花的布枕頭上,肩膀從被褥里半出來,上面有暗紅的痕跡,顯然是被人大力攥住留下的。
人顯然沒睡著,因為亮的突然刺激,閉著眼睛。
林榮棠走到了炕頭邊,低頭看著。
的有些發腫,眼下殘留著一些淚,不過臉上卻是愉悅滿足的,那是耗盡力后徹底松懈下來的舒暢。
林榮棠抬起手,指尖輕輕落在的上。
孫紅霞閉著眼睛,屏住了呼吸。
林榮棠定定地著墻上的年畫,那是送子觀音的年畫,現在依稀想起來,好像是之前和冬麥一起買的。
買這個的時候,冬麥笑得臉上發紅,單純青,好看得像野地里的梔子花。
林榮棠邊挽起一抹嘲諷的弧度,終于開口:“舒服嗎?”
孫紅霞沉默了一會,依然閉著眼睛,卻了:“舒服。”
林榮棠目緩慢地落在孫紅霞臉上:“那種事就那麼好嗎?”
孫紅霞陡然睜開了眼,坐起來,坐起來后,被子落,青自肩頭落下,半遮半掩間,肩頭殘留的痕跡明晃晃地刺眼。
輕笑:“好,特別好,沒經歷過,我都不知道原來這種事滋味這麼好,就是死了我都愿意,你說男人怎麼就這麼好呢!”
笑著林榮棠:“你這輩子,不能男人和人之間那麼的滋味,真是可惜了。”
林榮棠臉陡然鐵青,抬起手來,狠狠地給了孫紅霞一掌。
孫紅霞卻依然是笑:“你就算打死我,我都覺得值了,我也算是不白活一輩子了。”
只是當然也有些憾,擁有上一世的記憶,卻唯獨并沒有沈烈和自己的記憶,太憾了!
Advertisement
林榮棠出手,就去掐孫紅霞的脖子,他嘶聲道:“賤人,賤人,你可真是賤人,你們人都是賤人!冬麥賤,你也賤!你們離了男人就不行嗎?”
孫紅霞人都要不過氣來了,依然是笑:“怪不得冬麥非鬧著和你離婚,沈烈一看就好,和沈烈睡了后,人家冬麥才不稀罕你呢!”
孫紅霞說完這個,就咳起來,臉憋得通紅。
林榮棠卻放開了孫紅霞,他突然冷笑一聲,緩慢地道:“你以為我不能讓你快活嗎!”
**********
年后按理說冬麥應該回娘家,不過肚子不方便,也就省了,反倒是江春耕,大年初三那天,騎著車子過來了一趟。
沈烈自己手,簡單整治了一桌酒席,三個人吃吃喝喝的,沈烈和江春耕便提起將來的打算。
江春耕現在每天聽廣播,已經有些見識了,便提起來羊絨出口的事:“聽說那個能掙錢,還能給咱們國家掙外匯,再說現在干這行的越來越多了,首都絨毯廠還有上海紡織廠那里,供貨得多了,人家也開始挑了,咱與其和陵城的梳絨戶爭這個,不如想想別的出路,把咱的買賣做得更大!”
冬麥聽到這話,有些意外地看向自己哥哥。
想著自己娘之前還心哥哥再婚的事,但其實,哥哥現在眼界比以前開闊許多,想得周全了,心寬了,子也穩了。
結婚不結婚,對他來說倒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事,包括彭天銘那里,能不能走在一起,就看緣分,實在沒緣分,也就算了。
現在他要一心搞事業,勁頭上來了,那就好好干。
沈烈一聽,便笑了:“其實我也在想著這個事。現在咱們全國只有天津、蒙和新疆三家進出口公司有出口經營權,我打聽過了,天津和蒙做的是無絨,人家那個是純羊絨,分梳過后不帶的,新疆那家新疆土畜產進出口公司,主要是做過絨,只簡單用開機開,去了土和雜人家就直接賣。咱們要想在走出口這條路子,必須和人家搭上關系。我是琢磨著,天津和蒙那里,人家本來就是做無絨的,人家做得也很了,我們要去和人家談,沒什麼優勢,倒是可以利用新疆那邊的缺口,他們沒無絨,那我們給他們供,到時候一起合作,到時候他們益,咱們也沾。”
Advertisement
江春耕皺眉:“你剛才說,新疆那家新疆土畜產進出口公司?”
沈烈:“對。”
江春耕想了想:“之前我去首都絨毯廠送絨,當時一起住招待所的一個人,他被人家搶了提包,我幫著他一起追回來,當時他對我激的,要請我吃飯,我當時忙著趕火車,也就沒理,他給我留了聯系方式,說是以后過去新疆一定找他,我記得當時掃了一眼那紙條,好像那個人就是什麼新疆土畜產進出口公司的。”
沈烈聽了,眼睛亮了:“那回頭找找人家,對方不一定是管這個的,但關鍵是要搭上線,讓人家幫忙引薦引薦也行,認識個人,咱再慢慢談就好辦了,不然直接去找,人家本不搭理。”
江春耕:“那我趕回去,找找那個紙條,如果真是那個公司的,過兩天,我馬上坐火車過去新疆找人家去!”
沈烈:“行!”
兩個人又商量了一番,如果真和人家搭上線,那應該怎麼談,怎麼作,詳細地商量了一番,最后提到了廣會。
原來廣會是新中國立的時候就有的,當時要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些重要的建設資,比如化鋼材橡膠機械,當時這些都需要從國外進口,但是那個時候國家外匯匱乏,弄不到外匯,就不能買人家國外的資。
為了打破西方的封鎖,獲得外匯,五十年代的時候,廣東外貿系統就開始舉行小型的資出□□流會,獲取外匯,在之后的一些年,這個流會幾經沉浮辦辦停停的,一直到前幾年□□批準立了一個新部門做中國對外貿易中心,由新部門來承辦這個廣會,算是正式定下來,每年春天舉行廣會,大概持續二十天。
Advertisement
沈烈和江春耕既然瞄準了出口,如果能和新疆土畜產進出口公司搭上話,借他們的資格去參加這個廣會,到時候搞個大單子,那就賺大發了。
用沈烈的話說:“咱與其和陵城人在這里搶食吃,不如跳出去,掙外國人的錢,也給國家增加外匯!”
提起這個,自然又說起現在的國際形勢,國家外匯缺乏等等,聽得江春耕熱沸騰,越說越興,最后竟然酒也不喝了,騎著車子就往回趕,他要趕去找找那紙條,記得當時隨手揣兜里了,可別洗服的時候給洗爛了。
冬麥看這兩個人喝得歡實,便過去廚房里給他們端花生米去,誰知道進屋的時候,只剩下沈烈了,自己哥哥不見了。
納悶:“我哥呢?”
沈烈揚眉笑:“回去翻子去了。”
冬麥:“啊?”
沈烈這才解釋了這事,冬麥聽得好笑又好玩:“我哥可真心急啊!”
不過想想也對,其實哥哥本來就是一個急子。
笑嘆了聲:“我哥最近越來越有干勁了。”
當下沈烈起,收拾了殘羹冷炙,又去下了餃子,兩個人吃了,吃著時,冬麥卻突然想起來隔壁林榮棠家。
冬麥:“我昨天出門還看到孫紅霞了,當時遇到我,想和我說話,不過有別人,就走了,我瞧著那樣子,有點不對勁。”
沈烈蹙眉:“你現在肚子大著,和接,離遠點。”
冬麥:“放心好了,我肯定知道。”
沈烈點頭:“明天我再帶你去一趟陵城,檢查檢查,人家大夫說,咱這是雙胎,還是得注意,勤去醫院,你現在差不多快五個多月了,也該去看看了。”
冬麥想想也就點頭,還是謹慎一些好。
**************
本來是打算直接坐客車進城的,不過沈烈記起彭天銘那里有一批渣,自己不想分梳了,想轉給沈烈分梳,沈烈想著便干脆運過來,這樣可以開著小貨車去,冬麥坐在副駕駛座上,自己的車,也省得辛苦,累了可以躺著靠著。
村里有幾個想年后在陵城買東西的,也都趁機坐沈烈的小貨車,不過副駕駛座就那一個位置,其它人都坐在后車廂。
小貨車一路嘟嘟嘟地開,后車廂的人也不覺得冷,反而好玩的,覺得這小貨車比拖拉機拉風多了。
到了陵城后,沈烈把幾個村里人放下,就開著小貨車過去彭天銘的工廠了。
彭天銘這個人干起活來不要命的,過年時候梳絨機都沒停,沈烈冬麥到了,還在那里和工人商量開的事。
見到沈烈冬麥來了,忙下了口罩和防護服,過來和他們說話。
最近給首都絨毯廠供貨的太多了,僧多粥,彭天銘也覺得首都絨毯廠價太狠了,已經跑了一趟上海,上海那里國有紡織廠多,對羊絨需求量不小。
沈烈聽了,便給建議,又介紹了一個業務科科長的聯系方式:“我和他見過兩面,有什麼問題找他很方便。”
彭天銘自然激不盡:“除了上海,我現在也在想著和天津那邊接下,那邊的需求量也有一些,反正多條路走路。”
沈烈:“是,現在不人都要安裝梳絨機干這行,競爭越來越大,我們眼還是得放遠,平時有什麼消息,我們都互相知會一聲。”
彭天銘在首都人脈自然比自己強,而且聽說香港那邊也有些門路。
彭天銘:“那是自然。”
說話間,知道他們要來拉渣子,彭天銘便道:“你們先把貨車扔這里,我讓工人給你們裝車,正好我的桑塔納在工廠里,你們開著過去醫院吧,等你們回來,我估計也差不多給你裝好了。”
沈烈笑著說:“算了,你那桑塔納太貴了,我怕給你弄壞了,我們坐公車過去吧。”
彭天銘:“客氣什麼,鑰匙給你。”
沈烈見此,也就沒再推辭,拿了鑰匙,過去開桑塔納。
桑塔納在這個年代很貴,據說進口價是八萬,但是到了國,普遍售價都得要二十多萬。
一般一家能有個一萬塊就能被表彰了,二十多萬的桑塔納是什麼概念,普通人看到估計都要了。
沈烈先試了下,找了下覺,之后便開著緩緩出了工廠。
冬麥知道這桑塔納這麼貴,實在是有些心驚,自己和沈烈干了這麼長時間,滿打滿算的積蓄估計能有三十多萬,結果人家一輛車也二十多萬了。
沈烈:“等以后我們有錢了,也可以買一輛這種車。”
冬麥忙說:“我們現在有三十萬,我都覺得我們發大財了,這輩子做夢都想不到的錢,把咱所有家都換這麼一輛車坐在屁底下,想都不想敢想,還是算了。”
沈烈:“我是想將我們的羊絨出口,去掙外匯,你哥也是這個想法,你看他對這事比我上心,如果真了,咱有一天就可以開桑塔納了。”
冬麥:“我們還是腳踏實地,想想眼前吧。”
沈烈便笑了:“好,先去醫院看看。”
到了醫院,簡單地檢查了檢查,一切都好的,人家醫生說羊水充足,胎心也好,冬麥不太懂這些,沈烈也不懂,不過聽著人家大夫說好,也就放心了。
兩個人說著話,往外走,桑塔納就停在醫院外,誰知到了醫院外,就恰好見蘇聞州略扶著一個人,從醫院旁邊的門出來。
蘇聞州看到沈烈和冬麥,意外,之后便笑了:“你們這是做懷孕檢查?”
沈烈點頭:“是,蘇同志你這是?”
他這里說著話,冬麥的目卻落在蘇聞州邊的人上。
那個人現在也在看。
那是一個看上去四十左右的人,穿著一呢子大,圍著格子圍巾,烏黑的頭發輕盈地披散在肩頭,整個人的氣質嫻靜恬淡,一看就是出不凡。
不過冬麥看,不是因為一看就洋氣貴氣,而是因為長得——
長得和自己太像了。
確實太像了。
從看到后,冬麥便覺得,好像看到了另外一個自己,一個年紀大了后的自己。作者有話要說:注:本文廣會相關容參考了“廣會百度百科”。
另:
《西游記》中“他丈母:真真、、憐憐,都來撞天婚,配與你婿。”
《竇娥冤》中“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婿”
《白鹿原》中“白靈的心忽然跳起來,仿佛真的要見到自己的婿了”
這里的婿都特指的丈夫。
我前幾章中提到一句“孫紅霞的婿”其實也是這個意思,并不是bug,當然了這種會被大眾誤解的說法應該盡量用。
猜你喜歡
-
連載919 章
強勢萌寶:爹地彆自大
傳聞,夜氏總裁夜北梟心狠手辣,殘忍無情。雖然長了一張妖孽的臉,卻讓全城的女人退避三舍。可是,他最近卻纏上了一個女醫生:“你解釋一下,為什麽你兒子和我長得一模一樣?”女醫生擺弄著手裏的手術刀,漫不經心:“我兒子憑本事長的,與你有毛關系!”夜少見硬的不行來軟的,討好道:“我們這麽好的先天條件,不能浪費,不如強強聯手融合,再給兒子生個玩伴……”五歲的小正太扶額,表示一臉嫌棄。
92.8萬字8 27790 -
完結1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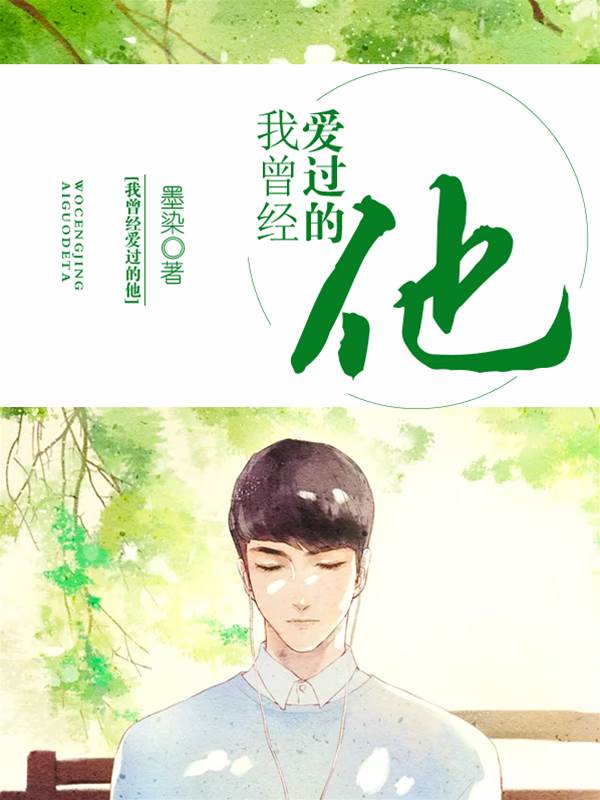
我曾經愛過的他
我為了躲避相親從飯局上溜走,以為可以躲過一劫,誰知竟然終究還是遇上我那所謂的未婚夫!可笑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卻隻有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裏。新婚之日我才發現他就是我的丈夫,被欺騙的感覺讓我痛苦,他卻說會永遠愛我......
33.5萬字8 10045 -
完結125 章

信不信我收了你
作品簡介(文案): 京都最近新聞很多。 號外一:聽說陳市長家那個被拐賣的小女兒找回來了,據說被賣到了深山溝裡,過的可苦了。 號外二:聽說陳市長家的小女兒是個傻的,天天說自己能看見鬼。 號外三:聽說陳市長家的小女兒強吻了樓部長家的三公子。(眾人驚恐臉:樓銘都敢惹!!) 陳魚把樓銘按在沙發裡親了好一陣。 陳魚問道:“感覺好點沒?” 樓銘瞇起眼:“丫頭,別逼我動心。” 陳魚懵逼臉———我只是在救人。 會抓鬼的小仙女VS溫柔腹黑病嬌大叔(大約) 其他作品: 《小藥包》、《重生在民政局門口》
44.9萬字8.08 12859 -
連載809 章

沖喜新娘:霍少天價小嬌妻
白家破產后,白曉嫻為拿回母親遺物、重振白家。自愿嫁給一個植物人。當眾人都在嘲諷她為了錢饑不擇食時,卻發現她被頂級豪門寵上了天。被欺負,婆婆撐腰,爺爺砸錢。而植物
168.3萬字8 399523 -
完結550 章

閃婚娶了個小祖宗,傅總拿命寵
【先婚後愛 雙潔 年齡差 甜寵 雙向奔赴】沐淺淺為了救老奶奶意外失明,三天就和老奶奶的孫子閃婚了!視力恢複前,沐淺淺每天都擔心,自己嫁給了一個沒車沒房的醜男。複明後,男人挑起她的下巴,薄唇微勾,“淺淺,對你老公這張臉還滿意嗎?”原來她男人不僅是絕世帥哥,還是千億豪門的繼承人!……傳聞中,傅家掌權人年近三十不近女色,不是身懷隱疾,就是取向異常。隻有沐淺淺知道,那位黏人又傲嬌,吃起醋來可怕得很。
97萬字8.18 596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