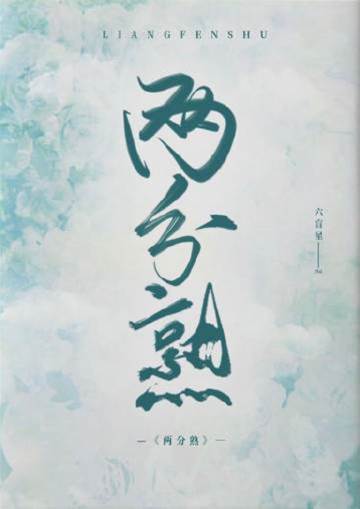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婚華正茂》 第799章 對不起,西川,對不起……
艾瑞克上前,一把扶穩蘇念恩。
“你喝多了。”
蘇念恩忽然道:
“其實除了手之外,我還有個辦法,長期租賃。”
艾瑞克道:“那點租金,夠解你燃眉之急?”
蘇念恩哭了。
不能。
就因為不能,所以,心底酸脹啊。
一愁、一酸,眼淚止不住的流。
這一哭,直把艾瑞克哭得不忍心了。
“你要實在舍不得出,我不買了行不行?別哭得好像被我欺負了一樣。”
蘇念恩立馬擺手,“不,出出!再加三個億?”
艾瑞克十分無奈,又好笑道:
“小姐,生意不是這樣談的。剛才我給你的報價,是我能做得了主,再加三個億,卡斯家族部走一遍,我們這合作大概率會失敗。”
“為什麼?”
艾瑞克道:“決定權不在我這,變數太大,能不能通過家族的審核,很難說。一個很大的弊端時,米瓊斯的地皮,在國際上不值錢。現在買來,只能囤著,這個事實你也清楚。”
如若有用,早就拿去利用了,何至于在那擺了這麼些年。
蘇念恩不想聽方理由。
“我守了你十八天,我救了你一條命,你這條命還不值三個億?”
艾瑞克很無奈,“公是公,私是私。公私不分,這生意沒法做,諾拉,別讓我為難。”
Advertisement
蘇念恩當然知道,在商言商,這也是的規矩。
生意上,從不講面。
不論對誰,一視同仁。
這是顧氏上下恨的原因。
可眼下,事關錢的問題。
若不臉皮厚點,幾個億啊!
“我救了你的命,你打算怎麼謝我?買我的地就不能給個漂亮的價?”
艾瑞克不得不順著的邏輯說:
“我現在買你的地,就已經是幫你。不然,我可以去任何正在發展中、發展潛力更大的國家去買地。我有錢,哪里都歡迎我。諾拉,因為你,我才讓步。”
蘇念恩擺擺手,“喝酒,喝酒。”
艾瑞克看著這焦急得有點了方寸的人,又很心疼。
“你的家族,萬不必推你一個人出來擋這一切。”
蘇念恩搖頭,“不,你不懂。”
如果不是,顧西川的江山早被人瓜分得殘羹都沒有。
而一家老小,只怕連條活路都沒有。
艾瑞克點頭,“我不懂,如果喝酒會讓你此刻好一點,那我陪你喝。”
蘇念恩拿出手機,點開錄音。
“錄音為證,請問艾瑞克·卡斯先生,您什麼時候與我簽訂買賣合約?”
艾瑞克道:“回亞特蘭斯,將這事排在第一位。”
蘇念恩滿足了,放心了。
Advertisement
心道:凌有救了。
至,保住了顧西川的一生心。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
現在,更懂這句話的意思。
可能心緒太沉,心太差。對于決定賣掉顧西川的地,心里很疚。
所以,在喝得飄乎乎的時候,竟然看到顧西川了。
他的氣息、他的聲音。
他的,。
抱著他,吻得難分難舍。
眼淚橫流,在心底里的疚、歉意,匯一句句哽咽難言的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沒能守住你的東西,對不起。”
“是我沒能力,我太弱。”
“對不起,西川,對不起……”
浮浮沉沉的一夜,看見了璀璨星河,看見了瀲滟四季,看見了驚心魄。看見了藏在心底里、平時不敢多想的男人。
那個,令一想心就會疼的男人,忽明忽暗的在眼前晃了一整夜。
*
清晨,亮刺眼的越窗而。
照亮了屋,大片灑,沖散了沉淀了一夜的清冷涼意,屋里這瞬間暖呼呼的。
落在艾瑞克臉上,亮的令他逐漸醒來。
很久,沒睡得這樣沉了。
片刻的遲疑后,他猛地撐起。
屋里,蘇念恩早已離開。
他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走的,甚至沒有一丁點察覺。
Advertisement
他生來警醒,在那次意外后,更加警覺。
但,今天,他徹底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的。
想想昨夜,艾瑞克心臟陣陣揪疼。
迷失了自己,可他沒有。
很多事,一點就著,一即發。
但他再能忍,面對,還是潰不軍。
艾瑞克穿戴整齊后,走出小旅店。
幾名仆人恭敬遞上他象征公爵份的帽子,為他穿戴好后,一行人上了車。
車上卡斯家族的一位掌權人,艾瑞克的叔叔仔細匯報了米瓊斯新政另擇他人的事。
“這是一場預謀,這可不能這麼算了。”
艾瑞克淡淡道:
“叔叔打算如何?”
萊德叔叔道:“新政一直表示出與我們合作的強烈,可事結果卻選了別人。我們卡斯家族可不是這麼好利用的。”
艾瑞克沒接話。
萊德叔叔憤怒道:
“一定要讓那個新王得到一點教訓!”
艾瑞克卻問:“布魯姆和新政選了誰?”
萊德叔叔卻搖頭,“我讓人查過那個人,從未聽過那麼一號人,不知道過往,沒公開來歷,甚至連是不是米瓊斯本土富商,還是國外的大氏族,都不清楚。新政對于這一次的合作,捂得很嚴實。”
艾瑞克挑眉,“哦?”
萊德叔叔快速看了眼艾瑞克,也不清楚公爵有沒有生氣,責怪他消息不靈通。
Advertisement
“公爵大人,我們懷疑,那一切只是新政放的煙霧彈。實際上,是布魯姆利用這次機會,將這個工程收回國有。新政不信任中國商人,自然也有理由不信任我們。”
艾瑞克緩緩點頭,“有道理。”
萊德叔叔發現公爵似乎沒有想象的那麼生氣,這個原本如探囊取的項目,現在落在別人頭上。看來……
“公爵大人,你是有別的打算?”
艾瑞克道:
“一步一步來,不著急。”
艾瑞克這話一出,萊德叔叔也不好再問。
只是這回國后,該如何向卡斯家族代?
到手的鴨子飛了,總得有個理由。
這理由自然不能是公爵大人被追殺,錯過了競標。如果推給新政,是新政放的煙霧彈,那一切都順理章了。
艾瑞克回到亞特蘭斯,前腳剛踏進都城大酒店,轉又離開了,沒告訴任何人。
他去了醉心居。
不是有生意要談麼?
躲什麼?
然而,到了醉心居卻沒見到蘇念恩。
猜你喜歡
-
完結1070 章

奉子成婚:古少,求離婚(又名:離婚時愛你)
新婚夜,他給她一紙協議,“孩子出生後,便離婚。” 可為什麼孩子出生後,彆說離婚,連離床都不能……
171萬字8 363842 -
完結46 章

你如星辰不可及
蘇清下意識的拿手摸了一下微隆的小腹,她還沒來得及站穩就被人甩在了衣櫃上。後腦勺的疼痛,讓她悶哼了—聲。
4.2萬字8 18329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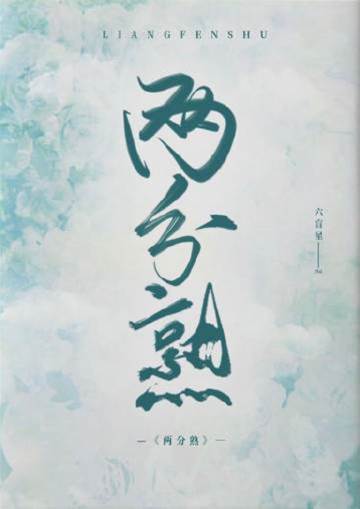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302 -
完結493 章
惡魔的寵愛
“以你的身材和技術,我認為隻值五毛錢,不過我沒零錢,不用找。”將一枚一塊的硬幣拍在床頭櫃上,喬錦挑釁地看著夜千塵。“好,很好!女人,很好!”夜千塵冷著臉,他夜千塵的第一次,竟然隻值五毛錢!再次見麵,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她是低到塵埃的花。一份價值兩億的契約,將她困在他身旁……
84.9萬字8 149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