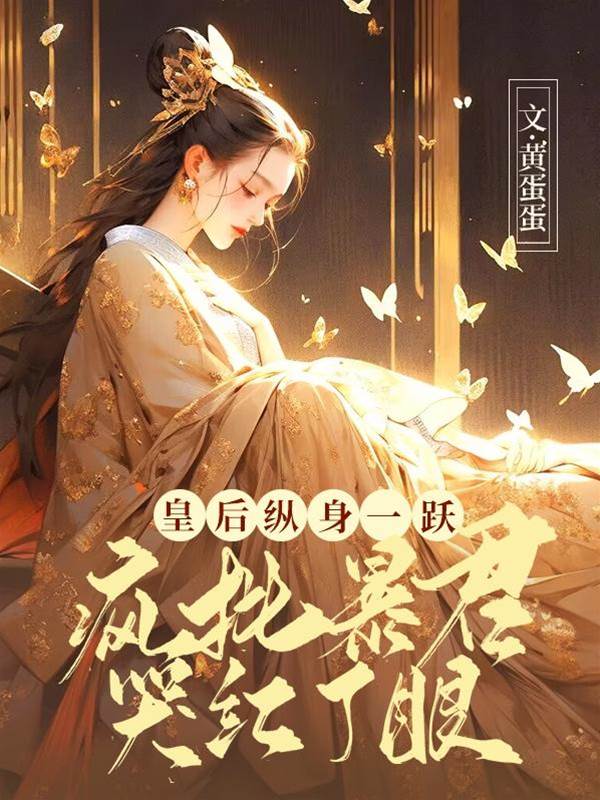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撩錯夫君后》 第102章
從林家到凈明寺,蘇眉都不曾問林以安是怎麼理二老爺的事,而是賴在他懷里,讓他給念話本。
聽著聽著,犯困還睡了一覺,睜眼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在后山的客院里,而林以安不知去向。
紫葵聽到里間有靜,穿過落地罩,就見到蘇眉穿好繡鞋往外邊來。
“三爺去凈無大師那了。”
“現在什麼時辰。”蘇眉大概猜測他的去向,側頭去看外邊已經黑黝黝的天。
“外頭看著黑,剛過酉中呢,似乎要下雨的樣子。”
紫葵話剛落,外頭真滴下雨點來,忽地一下,毫無預兆就下大了。
雨水打在屋頂上,噼噼啪啪,像有人跑上屋頂敲木魚。
“我去接你們老爺。”
蘇眉聽著雨聲,轉去找木屐雨,紫葵連忙跟著去翻箱籠。
一場大雨來得讓人措手不及,林以安走到一半便被困住了。
他這正好是寺院的后門,寺的和尚可能都躲雨去了,一時半會也沒見著能借傘的,索倚著門框賞雨。
幾盞昏黃的燈由遠而至,他牽一笑,不待人到跟前就小跑上前。
蘇眉打著傘,連忙給他遮住:“不是瞧見我了,還往雨里跑,是不是傻。”
邊說著,邊拿帕子來打的肩頭。
雨勢太大,他不過跑了五六步,連頭發都得半。
林以安輕輕握了手,抬抬下示意:“娘子來迎我,我來背娘子回去如何。”
蘇眉眼睛笑月牙,把傘遞給他,趴到他背上,然后再去接過傘。
石頭和紫葵一眾連忙在前邊打燈,把腳下的路照亮。
蘇眉在他背后著他穩健的步伐,想起一事,便趴在他耳邊說:“之前不是說欽天監算到二月天氣反常,今兒就下起這樣的大雨,還真是見,這就要應驗了?”
Advertisement
“究竟是老天爺心不佳,還是有人故意以訛傳訛煽人心,到現在還說不好。”林以安笑了一聲,“不過能測準天象,讓百姓們有個心理準備,也算欽天監的功德了。”
蘇眉明白他的意思。
早些年欽天監就犯了回大錯,下邊有人觀天象說恐有雪災,可正值部斗法,有人故意瞞報。結果那年還西北邊真的下了大雪,房屋倒塌,不百姓亦被活活凍死……這是**。
那批員,不派系,通通都給治罪,自那之后再沒有人敢瞞報天象,甚至還不約而同都往嚴重地報。
這些年再遇上天災,當地府才不至于又慌無措。
“煽人心……可能也占一半吧。”蘇眉從早年的事回神,再一琢磨,把這四個字又琢磨出更深一層的意思來了,“殷沁還沒有找著嗎?”
杜氏已經被趕出蘇家,再喊蘇沁肯定不合適了,杜氏夫君姓殷,蘇眉便喊回本名。
“不藏到生產后,是不會出現的。”林以安看了下頭頂的傘,“往后挪一挪,全潑你上了。”
蘇眉沒,神嚴肅道:“難道肚子里真是個男孩?”
可以用來再威脅太子,所以皇帝才將人藏那麼。
豫王雖然大逆不道,但如若太子也被皇帝構陷一個大逆不道,龍孫再當儲君,合合理。
皇帝真是……老謀深算。
林以安笑笑:“到了關鍵時候,那肯定就是個男孩。”
“太子殿下可真糟心。”
慨,他卻笑意更深了:“糟心什麼,太子殿下這幾日歡喜著呢,東宮有喜了。”
蘇眉一驚:“啊,太子妃……”說一半忙閉上,低了聲音,“現在還瞞著吧。”
“嗯,我先前號過脈。太子妃本又小,即便到六個月也不會多顯懷,能瞞到殷沁生產后。”他說著,顛了一下。
Advertisement
蘇眉哎喲一聲,吃吃笑著跟他咬耳朵:“所以我們以安哥哥是不是要多努力些。”
“也不知是誰不讓努力。”林以安一臉正經地說葷話,“牛都沒怕累呢……不過晚些也好,晚些你些苦。”
蘇眉到三月才十九,沒必要著急是真的,剛才他也就是那麼羨慕一下。
兩人邊走邊說,客院就在眼前了。
回到屋里,蘇眉讓打來熱水沐浴,去去寒。
把傘給他擋了一大半,后背還是潑了不雨,林以安拉著一塊兒泡在熱水里,還幫按位,讓愜意得趴在桶沿直哼哼。
等沐浴后,本來沒有困于的蘇眉沾著枕頭便睡著了,一夜好眠。
林以安和頸而眠,夢境里陸離奇。
同樣是他,經歷的卻是種種不同,夢里的最后一幕還讓他驚醒。
睜開眼,外邊已經天大亮。帳幔一片,他冷汗淋漓地探手向枕邊,發現邊沒有人,更是心驚地坐起。
“眉眉!”
“噯——”
糯的聲音從帳外傳來,林以安掀開帳子,便見到正歪著頭戴耳鐺,朝自己走來。
他張地盯著,知道察覺他的一樣,手去他額頭,他才覺到了真實。
夢里……離世了。
他無力挽留的無力和痛苦侵蝕著他心臟,即便是夢,那種覺亦真實得讓他害怕。
他去握著的手,手心汗津津的。
“夫君怎麼了,做噩夢了?”在他邊坐下,挨過去親了親他角。
林以安閉眼片刻,再睜開眼,面對鮮活的忽然明悟。
那個陸離奇的夢……是不是經歷過的那一世?
有些事和這世并不重合,甚至離得厲害,他就想起昨日凈無還與自己說的因果。
Advertisement
既然是因結果,那這世的結果必然不能再與前世一般,……嫁給自己了,而不是在病痛的折磨中離世。
他將擁進懷里,無比慶幸他們的緣分在這一世沒有被斬斷。
外邊的雨還在下著,直到中午才見小,到下午才徹底停歇,林以安領著蘇眉準備再去見見凈無,結果撲了個空。
小沙彌雙手合十與他們說凈無大師云游去了,就在雨剛停歇那會。
林以安和蘇眉面面相覷,小沙彌道:“師父給林施主留了話,師父說他昨夜參悟了林施主與蘇施主的一些因果。也正因如此,他想要塵世多行走,或許才能有所頓悟。”
“師父還說,兩位施主乃天作之合,這一世必然富貴喜樂。”
凈無云游,還給他們批了命,林以安謝過傳話的小沙彌,與蘇眉再去大殿上香,在后山的客院住了兩日才回的京城。
會試放榜要到四月,兩日回京倒不是因為科舉,而是見剛下過雨的天又開始有厚重云層下來,便早些回京城。
回到京城,林以安并沒有回林家,而是跟著蘇眉住到侯府。
蘇眉這個時候后知后覺,張地問他:“你跟國公爺說了什麼?”
林以安本也沒有想瞞,只是等父親的回答,見問起笑道:“你夫君這個時候再贅,岳父還收不。”
蘇眉就啐他一口:“你還想贅呢,爹爹說我蘇家的門不好進!”可玩鬧是玩鬧,很快便正了臉問,“你當真決定了?”
贅肯定是玩笑話,即便他愿意,還不愿意呢,但他是真的要離開林家。
這個時候離開林家,也不是不可,就是有點兒便宜了那些人。
“早就決定了,若不是要把我娘接出來,還怕你委屈,我肯定不會在林家親。”
Advertisement
林以安笑笑,對林家那些東西無所謂,“我會好好努力,給娘和你掙誥命。”
要把生母牌位也接出來,這就不是單純的兄弟分家,而是徹底離,自立門戶,他的這一支除了緣外不會再與衛國公府有聯系。
蘇眉聞言還是有些不滿:“反正該你的,我還是要給你討回來!你要再回林家議此事,把我帶上,我把算盤帶上!”
現在算盤打得可好了,沒有便宜他們的事。
林以安失笑,在上香,滿足地道:“他們占不了便宜。”
**
經歷了英王豫王一事后,朝堂似乎也就此平靜。
皇帝讓了一半權給太子,有時連早朝都不去了,任由太子掌政。
太子是能力的,樣樣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條,沒有出人使壞的日子,過得亦十分地快,一眨眼就到了放榜的日子。
這間林以安一直住在侯府,其中與衛國公涉了兩回,都沒能達意見一致。
衛國公還是希林以安只是分家,而不是連宗族都離去自立門戶,給了無數的條件,甚至連爵位都拿出來了。
林以安當著兩個兄長的面直言道:“我從來就不稀罕這個爵位,圣上最近力不濟,父親考慮的時間也就只有那麼兩三個月。”
衛國公聞言臉鐵青。
他怎麼能不明白小兒子的意思。皇帝不好,估計太子不久就要強行登基,等到太子登基,才是真正清算林家的時候。
長房都干了什麼,太子清楚得很,他再不同意,林以安勢必直接請太子手,那到時候就不是再這樣商議了。
最終,衛國公還是屈服了:“既然你意已決,為父便不再強求。等到那個時候,為父會親自去向殿下請罪,希看在先祖的份上,殿下能將功抵過,饒恕林家。”
“父親!”
林大老爺和林二老爺都白了臉。
這是……這是要拿爵位出去抵過!
林家爵位若是不保,這國公府也得收回,那他們……兩人心頭一凜,終于明白為何林以安沒有難為自己。
他不是不為難,而是知道他們往后都得落魄無法翻!
沒有了爵位的日子,讓習慣了權勢帶來好的兄弟二人都冷不丁打了個寒。
他們這些年算計的人,得罪過的人,恐怕要將他們活生生給拆了!
還有什麼能比日夜為命擔憂的恐懼更折磨人?!
作者有話要說:今天的更新~~晚安
————
猜你喜歡
-
完結752 章
太後孃娘今天洗白了嗎
(雙潔、甜寵、1v1)沈紅纓玩遊戲氪金成癮,卻不曾想穿到了自己玩的古風養崽小遊戲裡……成了小皇帝崽兒的惡毒繼母當朝太後,十八歲的太後實屬有點牛批,上有忠國公當我爹,下邊宰輔丞相都是自家叔伯,後頭還站了個定北大將軍是我外公!氪金大佬穿成手掌天下權的惡毒太後,人人都以為太後要謀朝篡位,但是沈紅纓隻想給自己洗白設定好好養崽,誰曾想竟引得宗室藩王癡情追隨,忠臣良將甘拜裙下;莫慌,我還能洗!容恒:“太後孃娘要洗何物?”沈紅纓:“……洗鴛鴦浴?”【小劇場片段】人人都說國師大人聖潔禁慾不可侵犯。卻見太後孃娘勾著國師大人的下巴滿目皆是笑意道:“真漂亮,想要。”容恒:……世人咒罵太後惡毒,仰仗權勢為所欲為。後來,燭火床榻間那人前聖潔禁慾的國師大人,如困獸般將她壓入牆角啞聲哀求:“既是想要,為何要逃。”【禁慾聖潔高嶺之花的國師x勢要把國師撩到腿軟的太後】
66.3萬字8 61973 -
完結555 章

新婚日,醫妃她炸翻王府!
【醫妃+雙強+替嫁+美食】一朝穿越成替嫁王妃,公雞拜堂?夫君嫌棄?小妾上門找茬?不怕,她用精湛的醫術虐渣,順道用廚藝俘獲夫君芳心。“娘子,今晚我想進屋睡。”“不要臉!”
102.3萬字8 9290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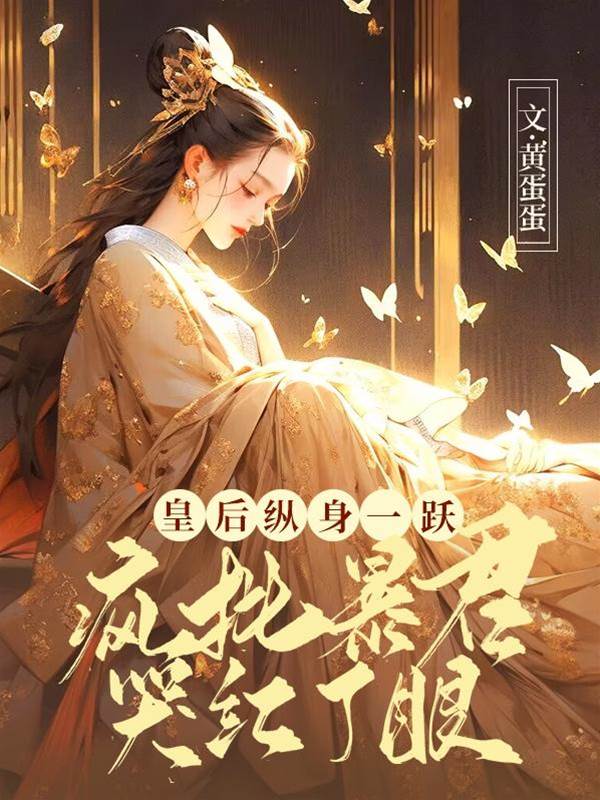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296 章

寵婢無雙/儲媚色
無雙十五歲便跟了龔拓,伺候着他從青蔥少年到如今的翩翩郎君。 外人都道她得了伯府世子寵愛,日子舒坦,不必起早貪黑的勞作。 只有無雙知曉那份小心翼翼,生怕踏錯一步。那份所謂的寵愛也是淺淺淡淡,龔拓的眼裏,她始終是個伺候人的奴婢。 韶華易逝,她不想這樣熬到白頭,琢磨着攢些錢出府,過平常日子,找個能接受自己的老實男人。 將這想法委婉提與龔拓,他淡淡一笑,並不迴應。 他的無雙自來溫順乖巧,如今這樣小心,不過是因爲家中爲他議親,她生出了些不安的小心思,太在意他罷了。好吃好住的,他不信她會走。 出使番邦前,他差人往她房裏送了不少東西,也算安撫。 半載之後,龔拓回來卻發現房中已空,家人告知,無雙已被人贖身帶走。 成親日,無雙一身火紅嫁衣站在空蕩蕩的喜堂,沒有賓客,更沒有她未來夫婿。 主座男人手捧一盞茶,丰神如玉一如往昔,淡淡望着她。 她雙腳忍不住後退,因爲氣恨而雙眼泛紅:世子,奴已經是自由身。 龔拓盯着那張嬌豔臉蛋兒,還記着手上捏住那截細腰的觸感,聞言氣笑:是嗎? 他養她這麼些年,出落成如今的模樣,可不是爲了便宜別人。
45.5萬字8.18 558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