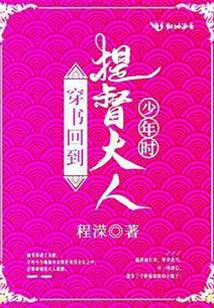《病嬌藩王寵妻日常》 第 65 章 病嬌
裴鳶將纖手垂於膝上,盈盈的剪水眸卻是不甚自然地垂了下來。
適才險些犯了大忌,臣下是不能直視帝王的,做此舉大有冒犯之意,幸而那楊皇後未瞧見和閼臨的眼神流,不然憑那善妒的子,定會對此事大做文章。
且裴鳶心知肚明,在這甘泉宮的宴上,有許多人其實都是存著看笑話的心態的。
當年司儼搶親於還是太子的閼臨,在場諸人卻都知曉,雖然潁國藩王勢大,但是太子卻不承奪妻這種奇恥大辱,可他卻到了先帝和裴太後的製,這才將此事強自忍了下來。
且遠王司儼似是有著料事如神的能力,他竟是預到太子即要失去理智,且會在他歸潁的途中設下埋伏,便提前離開了上京,僥幸逃了一劫。
而司儼這番來京的緣由,有的人認為是他狂妄,有的人則認為是金城一役後,潁軍元氣大損,暫時沒有同北軍戰的實力,所以他為諸侯王,帝王召之,他才不得不從。
裴鳶和司儼的一舉一行都備矚目,且裴鳶適才也清楚地看見,坐於主位上的閼臨竟是也同對視了片刻。
真是不該迷糊到,做出如此失常的舉。
裴鳶希坐於側司儼不要看到適才做的事。
人兒正這般想著,竟是驀地又覺,司儼適才明顯是想為夾菜的,可他卻又撂下了手中的筷箸。
裴鳶覺得奇怪時,亦覺自己的手背竟是突地一涼。
待再度垂下眼眸時,便見司儼已然用指骨分明的大手,覆住了的手。
男人握小手的力道漸重,亦將其漸漸地攥了掌心中,包覆手的過程中,也莫名帶著幾分占有的意味。
隨即,司儼牽引著的手,將其落在了他的上。
Advertisement
裴鳶麵微詫,待轉首急要觀察他的麵時,卻見司儼已然先轉,靠近了。
他微微傾,做出了要同耳語的態勢。
在宴上,夫人既是在側,那麽這參宴的客人若想同自己的妻子耳語幾句,再正常不過了。
閼臨正要執起酒爵,恰時撞見了裴鳶和司儼的親之舉,頓覺心頭被刺,即要飲酒的作也是微頓了一下。
楊皇後觀察細微,自是覺出了丈夫的異樣,便也循著閼臨的視線,看向了坐於上席的遠王夫婦。
其實很不願意承認,但司儼和裴鳶這對夫妻看上去,一個貌,一個英俊,兩個人確實很登對。
故而楊皇後斂去了眸的不豫,便微拎著華貴的寬袖,持筷為側的閼臨夾了塊他平日喜食的炙鹿脯,聲道:“陛下,您用些菜罷。”
見閼臨雖持起了玉筷,卻是稍顯嫌惡地將為他夾的那筷鹿脯撥到了玉盤的邊緣,隨即又將那筷箸撂到了筷枕上。喵喵尒説
楊皇後的麵一僵。
隨即,一難以言狀的意也蔓上了的心頭。
就知道,閼臨還是沒有忘記裴鳶。
裴鳶如今已經嫁為人婦,且也定是被那遠王睡過了,可縱是如此,閼臨還是惦記著別人的妻子!
而坐於上席的裴鳶自是未能覺出楊皇後的目在看向時,竟是帶了些怨毒的恨意。
人兒隻覺耳一,隨即,隻聽司儼嗓音低沉地同耳語道:“鳶鳶,一會無論發生什麽事,你都不要怕,我會護好你的。”
裴鳶溫馴地點了點頭,小聲地回道:“嗯。”
心中的擔憂也漸漸消弭。
覺司儼應是沒發現看閼臨的事。
雖然司儼從未明確地同說過,但是裴鳶卻也知曉,他其實是很在意這些事的,他在意同閼臨險要定下的婚約,甚至連靠近的親生兄長都難以忍。
Advertisement
皇帝閼臨的心中雖然如被針刺,卻也是存著理智的,他知他今日設此宴的目的,不是用來糾結裴鳶和司儼之間到底有多親的。
便從主案起,亦命側的宮婢持著青銅酒,在一眾諸侯微詫的神下,緩步走向了位於司儼對麵席位上的六安國國君,閼治。
閼治的地位在同姓諸侯王之中最尊,若按輩分,閼臨還得稱他一聲叔父。
帝王親自走到席下為諸侯王敬酒,看似是對其予以貴重的禮遇,但卻又讓人覺,他明顯是要拿這帝位來對其施以威懾和製。
此時此刻,若要湊近那宮婢持的黯漆托盤,便能看見,那青銅酒之旁,竟是躺著一枚銜靈芝飾樣的金製耳鐺。
可那凰形狀的耳鐺,雕工雖致異常,卻又詭異地斷了鳥頭。
這隻耳鐺是甄王後的之。
閼臨的意味再明顯不過了,他這是要閼治做出選擇。
若他喝下了他賜他的酒,便代表他同意削藩,亦會出兵權。
若閼治不喝,就代表他選擇了放棄甄王後的命。
當然,閼臨肯定不會選擇在宴上就對甄王後誅之。
甄王後已經被他和楊皇後控製住了,若閼治不允削藩一事,他於宴罷隨時都可取甄王後的命。
反正甄王後本就患有疾,他亦大可以為的死訊尋個暴斃的由頭。
閼臨算準,他那叔父閼治是個敦厚的人,且他妻如命,定不會舍棄甄王後的命。
且他也並非是要廢他們這些藩王的王位,隻是要削些封地,再褫奪他們手中的軍權而已。
閼治和其他藩王,好歹還有個可世襲的王位,往後餘生也能盡富貴榮華。
宮婢已於這時持起酒,在帝王的三足酒爵中倒滿了醇酒,閼臨將其接過後,便對六安國國君道:“叔父,朕敬你一杯。”
Advertisement
在場的所有人都以為六安國國君會起持酒爵,儀態從容地同帝王對飲。
卻未料到,電火石之剎之間,大殿卻傳出了瓷碎地的哐當之聲。
眾人皆驚。
隻見東平國國君閼閎竟是猛地將前的玉盤拋擲在案,他亦順勢持起了離他手邊最近的一塊碎瓷。
這些國君的後雖都立侍著佩刀的侍從,可此事發生得過急,也太過出人意料,他們還未反應過來,卻見閼閎已然持著那個碎瓷片,走到了閼臨的後,亦將其鋒利的鋸邊抵在了帝王的咽。
閼閎不僅年輕氣盛,也是先帝的幾個皇子中,武藝最強的,閼臨雖也習武,卻並不是閼閎的對手。
皇帝的近侍宦見狀,立即便用尖銳的嗓子聲道:“逆王要弒君,還不快護駕!!!”
侍從蜂擁而至,刀出劍鞘的森然之音使人不寒而栗。
弓/弩手在大殿中卻不敢施展手腳,因為閼閎離閼臨的距離太近,縱是箭再高的人,也難免會誤傷到帝王。
裴鳶自是被這種場麵駭道了,司儼麵淡然地攥著的手,低聲道:“別怕。”
東平國國君閼閎這時嗬斥那些侍從道:“孤看你們誰敢靠近!”
話落,閼閎又將那碎瓷近了閼臨的皮。
六安國國君閼治這時終於起,他嗓音平和,對著前的兩位小侄道:“陛下,東平國國君想必是醉了,這才做出了如此冒犯的舉。而今之際,不如我們各退一步。先帝甫一登基,便將這六個郡國的王位分封給了臣和在場的諸位閼氏子孫。先帝英明,他做此舉之意,為的就是防止各地豪強會對中央皇朝有威脅。若您偏要削藩,違背先帝之意,自會有損大梁江山的闔閭興旺,還忘陛下慎重決定。”
Advertisement
閼臨本以為隻有閼閎這麽個沉不住氣的,會行這種要威脅帝王的險招,卻未料到,閼治竟是也同閼閎勾結到一了!
這兩個國君,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讓他這個帝王手足無措。
閼閎複又對前的閼臨威脅道:“臣已派東平國的大將控製住了另兩個郡國,再加上六安國的幾萬兵員,也能湊個十餘萬的大軍。”
若真按閼閎所說,在西有虎視眈眈的潁國,在北亦用兇悍的匈奴,再加上上京之東,這幾個作的藩國,那閼臨即要麵對的便將是被三麵夾擊的困境。
閼臨毫都未預料到,這些小藩竟是也能欺侮到他的頭上來。
而他,卻不得不做出妥協之舉。
他亦未猜到,真正擺布這些國君的人,竟是這其中唯一的異王,司儼。
******
及至黃昏人定之時,潁國的輿仗隊已在歸程的途中。
皇帝這次非但未功削藩,竟還折了個史大夫進去,為了平息諸王的憤怒,閼臨不得不說自己是那史大夫的挑撥,這才了削藩的念頭。
裴鳶卻覺,若不是上京的軍隊剛同匈奴打完仗,仍需休作一段時日,閼臨此番是不會放過那幾個他放棄削藩的諸侯王的。
這幾個國君竟是做出了這種舉,那朝廷將來也定會派兵去攻伐各國。
但是無論如何,這番閼臨並未得逞,此番他本想通過削小藩,來對司儼施以威懾,可卻不僅未能功,反倒還被司儼看了笑話去。
和司儼終於離了險境,且輿仗隊也已接近金城的城池,即將進潁境。
駿馬揚頸微嘶,伴著呼嘯的積北之風,其音稍顯淒厲。
裴鳶卻於這時覺得異常疲累,人在高度張過後,力也自會如都被/走一般,再加之乘的這輛馬車也是稍有顛簸,便想在歸潁的途中憩一小會兒。
故而人兒用纖手掩住了瓣,模樣慵地打了個哈欠。
司儼用餘瞥見裴鳶的舉後,便低聲問道:“困了?”
“嗯。”
“靠我懷裏睡一會。”
話落,司儼便出了左臂,攬著側人兒的纖腰,讓的小腦袋靠在了他的肩膀。
裴鳶屬實困倦,人亦因此而遲鈍,毫都未覺出,男人周已然散出了愈發濃重的鷙氣場,隻神溫馴乖巧地靠著他,亦將濃的長睫垂於薄的眼瞼,很快便陷了昏睡之中。
人兒並未完全睡下,仍尚存著幾分淺淺的意識,卻聽圈著腰肢的男人嗓音低沉地問:“鳶鳶,你在白日的宴上,是不是看他了?”
裴鳶地唔了一聲,隨即糯糯地問道:“看誰呀?”
“閼臨。”
司儼聲音微沉,這番,他竟是連皇帝二字都不稱了。
裴鳶意識迷糊,亦未覺察出司儼對閼臨的稱呼有何不對勁,隻懵懵地如實回道:“嗯…就隻看了他一眼。”
司儼聽罷,眸一黯。
一眼?
一眼也不行。
裴鳶的神態帶著對男人的眷和依賴,正要往司儼的懷裏靠去,卻覺男人的手臂,竟是驀地鬆開了的腰肢。
於這時,也終於覺察出了司儼的異樣。
隨即便覺,自己的彎竟是被他用臂擔了起來,人兒因而睜開了雙目,待驚詫地低呼一聲後,便跌坐在了男人修長且結實的雙上。
裴鳶懵然無措地看向司儼時,他已然漸漸傾,卻隻是在的眉心輕輕地落了一吻。
覺出了男人薄的微涼後,裴鳶卻覺,司儼分明待異常的溫珍重,卻又莫名讓覺得有些悚然不安。
故而裴鳶眨了眨眼,同司儼的睫亦相在了一。
司儼漸漸抬首,薄亦離開了人兒的眉心,男人冕冠上的七旒珠串亦在隨著他起的作微微撞,其後那雙好看的眼睛深邃且清冷,令一,就會深深地淪陷。
可是,裴鳶卻於適才,看到了他眼裏閃過的那抹,極端又帶著病態的鷙之。
但是當再度向他的雙眸時,卻又覺得,他看的眼神分明是異常平靜的。
裴鳶隻覺,此時此刻的覺,就如在雨布的海麵上,乘著搖搖墜的一葉扁舟。
雲翳雖重,天卻仍未降雨,海麵也隻是微起漣漪。
不知何時會狂風大作,但能夠肯定的是,這海麵早晚會掀起洶.湧的巨浪,亦會沉這深深的海底。
這深海之底亦如司儼的心。
海的表麵就算再平靜,你卻永遠都不知道,它的裏麵到底都掩藏著什麽。
。您提供大神嫵梵的病藩王寵妻日常
猜你喜歡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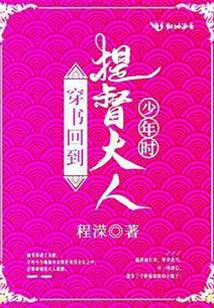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1 -
完結1044 章
法醫王妃別動刀
九王妃慕容諾有個+∞的膽子,你送她花,她看不上眼,你送她豪宅金山,她提不起勁兒,你讓她去驗尸,她鞋都不穿就沖在最前面!身為皇室顏值天花板的九王爺沐清風就很看不慣她,從來沒給過好臉色,寧可抱著卷宗睡覺也不回家。全王府都認定這對包辦婚姻要崩,直到有一晚慕容諾喝醉了,非要脫了沐......清風的衣服,在他身上畫內臟結構圖。蹲墻角的阿巧:完了,王妃肯定要被轟出來了!蹲窗下的伍叁七:王爺怎麼乖乖脫了,等一下……王妃怎麼也脫了?!!!
150.6萬字8 67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