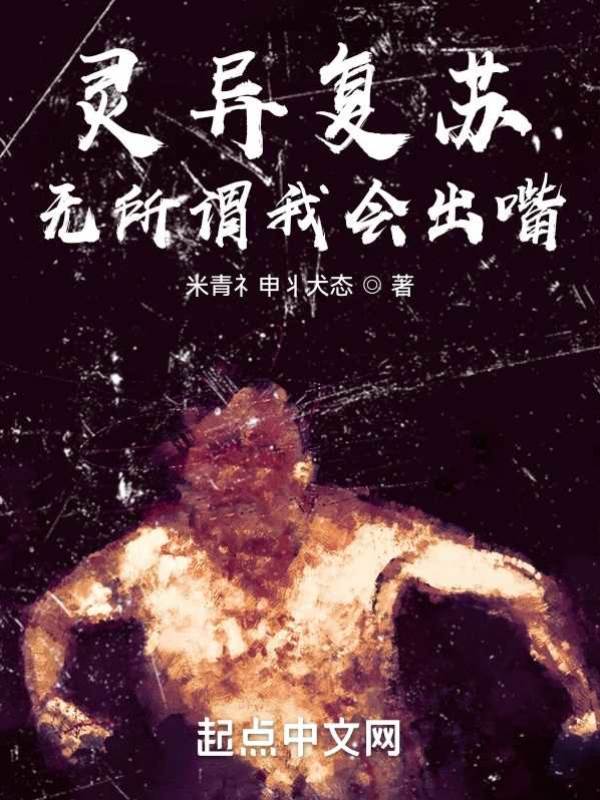《生死追緝》 第十五章 刑滿釋放的目標
「今日,我市將軍山碎案一審開庭……」這樣的題目並不能在浩如煙海的網路世界中博得足夠多的關注度。但下面某位網友的留言,吸引了男人的注意:「偵破這件案子的是市局的刑偵支隊長夏朗,他和這件案子的辯護律師陳妙言是男朋友關係,擺明了是想替嫌疑人罪啊!」
真有意思!這個男人似乎是發現了新大陸,他後仰在了座椅上,點上了一支煙,輕輕吸了一口,如鷹隼般的銳利目盯了顯示上那「夏朗」兩個字,角出了一詭譎的笑容。
什麼神探,不過是假公濟私,徒有虛名而已,就讓我揭掉你偽善的面吧!隨著他的緒漸漸興,一大口白的煙霧從裡噴了出來。
夏朗冷不丁地打了一個寒,左右看看。
「你幹嘛呢?」畢煒忽然詫異地看著他。
夏朗搖了搖頭:「哦,沒什麼,可能是空調溫度有點兒低了。」
此時,兩人正在一家洗浴中心做足療。畢煒讓自己的足療師把空調的溫度調高一點兒。
這時候的溫度舒服多了,畢煒愜意地閉著眼睛,著足底按。
夏朗笑著問道:「這麼好的事應該找老蘇來一起!」
哪知,畢煒卻睜開了眼睛搖了搖頭:「他?還是算了吧。再有趣的事被他摻和了也就變得沒趣了。」
夏朗不好就這件事發表意見,只是說道:「哎呀,還是你懂得生活呀!」
畢煒無奈地說道:「我不嫖不賭,總得學會放鬆自己吧?不過這事你可不能告訴你嫂子,要不然還以為我嫖娼了。」
「哎,我聽說你那時候在離火市,因為嫖娼被嫂子抓過,有這回事嗎?」
Advertisement
畢煒笑道:「胡說八道,我那是去查案子了。你不是也進過派出所嗎?」
夏朗當初因為梁玲的案子去了那種地方,卻被陳妙言舉報了,想不到他和畢煒的經歷竟然會有如此的相同。
45分鐘的足療時間結束了,兩位足療師走後,夏朗和畢煒忍不住聊起了案子。
畢煒拿了條熱巾了手,點上了一支香煙,吸了一口后說道:「也不知道技那邊幹什麼吃的,一點兒線索都沒有。」
他的這句話說完后,許久都沒有聽到夏朗的回應。扭頭一看,這位暫調過來的支隊長正皺著眉頭髮愣。
「想什麼呢?」畢煒丟了一條巾過去。
夏朗醒過神來:「你說什麼警察死了比前局長還要轟?」
畢煒乍一聽到這個問題,也沉默了。據之前的推測看,兇手對於自己下手目標的標準越來越高。王子朝是一個退休的前局長,也的確是個貪。甚至他死後,警察隊伍里都有人在拍手稱快。他的死,使得這個兇手的「名」空前高漲,這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會激起他的「榮譽」。下一個目標,只會比王子朝要高,比他的影響還大。
這一點,畢煒之前就已經想過了。不過這一次他又加了一點:「應該是一個位高權重且有污點的警察!」
「學長……」夏朗突然打了一個激靈。
畢煒被打斷了他:「肯定不是省廳的那些人,我太了解那幾個人了,一個個都兩袖清風,恨不得自己就是包青天、就是海瑞。來這兒之前我都查過了,都乾淨得很。不過……」他突然話鋒一轉:「我也不是沒有目標。」說完,從懷裡拿出了一張照片拍在了桌子上。
Advertisement
夏朗接過來,只見照片上是一個年逾花甲的人,雖然穿著乾淨得,卻滿臉的油膩,臉上帶著明的市儈,照片上的此人正笑著,只是笑容讓人覺得很假、很不舒服。
「這個人賀炳炎,原來是省城明華區公安局的局長,因為貪污進去了,判了八年,明天放出來!」他說完,端起了桌上的茶喝了一口。
夏朗聽完他的介紹,又重新低頭看著照片,心中不免揣測:這個人前一個殺的是前市公安局局長,這一次會選擇賀炳炎這樣一個「小小的區分局局長」下手嗎?何況賀炳炎坐了八年牢,也算是惡有惡報了。這個人會是下一目標?
畢煒看他的神,已經猜到了他的想法,說道:「我也想到了,這個人比起王子朝的影響力不算什麼,但是除了他,我也想不到別人了。反正明天這老東西就出獄了,我們去接他!」說完,他也不管夏朗再有什麼樣的意見,躺下去瞇上了眼睛。
第二天,省城下了2019年的第一場雨夾雪,看來天氣預報也有不準的時候。雨水夾雜著小冰粒砸在了車前窗,噼噼啪啪地作響。畢煒在車裡點了一支煙,皺著眉頭看著車窗外。雨水無地沖刷著車窗,形了一道水簾,順著車窗流下來,模糊了視線。
畢煒覷著目看到了不遠那個背影,他嘆了口氣,按了兩聲喇叭。那個背影聽到了,失地轉回來,走到了跟前,拉開副駕駛的門鑽了進來。他拉掉了連帽,出了夏朗那英俊的面龐。
畢煒說道:「還有半個多小時呢,你著什麼急啊?這第一監獄的監獄長老龐,那是出了名的嫉惡如仇,寧肯晚放一小時,也絕不早放五分鐘。」
Advertisement
興許是被煙霧繚繞的香煙嗆到了,夏朗咳嗽了兩聲后說道:「真希這個賀炳炎是兇手鎖定的目標。」言外之意,省得警方折騰了。
「我也一樣啊,說句實話,這種禍國殃民的老王八蛋就算是死在我面前,我心裡也毫無波瀾,沒準兒還得去慶祝一番呢!」
話音未落,就見從遠駛來了幾輛豪車,賓士寶馬奧迪A8,每一輛的價值都不下百萬。這幾輛車在路邊停穩后,從車上下來了幾個人,這些人有的西服革履,有的戴著大金鏈子,無一不散發著暴發戶的俗氣。
畢煒見到這一幕,冷笑一聲:「瞧見沒,不用咱們來接,有人來啦!」
夏朗心裡也清楚,這些人都是賀炳炎的「朋友」,一個落馬的貪邊能有幾個朋友?一定是過他「照顧」的了。他拿出了陳妙言送給他的電子煙,狠狠地吸了一口。
畢煒說道:「這些人,全都是在局子里掛了號的,沒想到還這麼猖狂。得嘞,我得好好看清楚都有誰,回頭一個個收拾了他們!」
雨夾雪下得更了,那幾個人有的熬不住,回到車裡等著了。有幾個年輕人撐起了傘,眼穿地盯著監獄的大門。這架勢,哪裡像是在等一個刑滿釋放的貪,倒像是一個個的夫石。
良久之後,那扇灰的大鐵門終於有了靜,隨著一陣嘈雜刺耳的開鎖聲,旁邊那扇小鐵門終於打開了。回到車裡的幾個人趕忙鑽了出來,站在外面等候的那幾個人趕丟掉了手裡的香煙,快步走了過去。
一個蹣跚著腳步的影從門裡慢慢走了出來。
Advertisement
「走!」畢煒和夏朗急忙下了車。
走近了才發現,這人七十多歲的年紀了,頭髮全白,材較照片上瘦了許多,臉上一副飽經風霜的樣子,沒有了虛偽的笑容。厚鏡片後面的那雙眼睛也失去了彩,只剩下了一片混沌。
那群人三兩步迎上去:「賀局,我們來接你了,這麼多年你委屈啦!」乍一見到這些人,賀炳炎激得都說不出話來了。
畢煒和夏朗正往那邊快步走過去,忽然看到,從東邊快步走過來了一個人,穿著黑的衝鋒,拉起了帽子,迅速地靠近了賀炳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