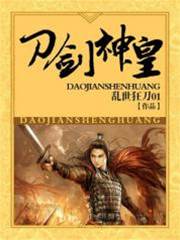《財神春花》 第 90 章 常鱗凡介
并沒有人理會他。藺長思的視線從吳王臉上掃過,渙散陌生,如同霜雪。
他開口了:
“這一世,我注定是多病多愁,父母失心,而不得,注定要親手殺死我心的子。他們說,這是為我編排好的話本子,注定不能掙的命運。”
吳王聽得明白,上前兩步,扯住霍善袖:
“道尊,長思當年是你親手所救,他這條命來得不易!……神尊若有差遣,本王親自手便是,求你們……放過長思吧!”
霍善面無表:“神尊既已安排,便是只能由世子下手。王爺,你難道不相信神尊麼?”
吳王面若枯葉,悲聲道:
“……所有罪孽都是本王一人所為,也應由本王一力承擔!但長思自仁厚純善,連螞蟻都未踩死過一只,他的手上,怎能沾染他人的?何況……這是他喜歡了多年的姑娘,若是死在他手上,今后他回憶起來,如何自?”
Advertisement
霍善冷聲道:“王爺,神尊也是為汴陵萬民的福祉著想!莫說犧牲你一個兒子,就是將你我捆在一起燒了,又有何惜?”
吳王愕然變。還說什麼,地面忽然劇烈晃,有碎石撲簌簌從頂落下,連神像也輕微地晃了一晃,驀地發出炸響。
幾人大驚,再看向神像的基座,竟然出現了一道深深的裂。
霍善以金錢劍杵地,方才站穩,倏然醒悟過來:“是斷妄司!他們果真要破陣!”
錢仁冷笑:“斷妄司那幾個年輕人,才修行了幾年?拿什麼破陣?”
然而接踵而來的第二次地震吞沒了他的話音,神像再度搖晃起來。
接著再一聲炸裂,神像的基座上出現了第二道裂。
一道黑不知從何冒出來,落地化作灰的鼠仙,跪地抱拳:
“神尊,斷妄司在澄心觀起了水陣,將桃花汛引了方家巷子!”
霍善恍然驚:“神尊,金遇水則沉,他們是要用桃花汛沖破陣缺!”
Advertisement
錢仁大喝一聲:“休要驚慌!”
“聚金法陣破了又如何?只要談東樵找不到我的原,又能奈我何?只要藺長思親手殺了長孫春花,雙雙應劫,兩墮仙之便都是我的!”
霍善一怔。
錢仁哪里還顧及得了他的想法,高叱一聲:
“藺長思!你還不手,更待何時?”
霍善與吳王雙雙變。
藺長思平板地應了一聲,玉石般清的劍與眉心平齊,聲若寒霜:
“春花,你我這段孽緣,便做個了斷罷。”
春花要閃避,腳下卻如灌了重鉛般彈不得,只得眼看著劍尖朝心口刺來。
長劍穿帛,——“篤”地刺!
一縷碎發從春花鬢邊飄然落下。
藺長思的長劍在及左前,瞬間挑高了兩寸。劍風刺破肩上外,挾著冷冽的怒意繼續向后,直刺神龕之上,神像的心臟。
白玉帶上,掛著一個墜著七絡子的連理枝紋銀香囊,微微搖晃。
Advertisement
神像中劍之,殷紅的線汨汨地流了出來。
一團黑霧自神像之中出,在半空中翻騰扭曲,如同一條被扎了七寸的黑蟒。整個窟中都回著錢仁痛苦的咆哮。
“本尊明明對你用了裂魂之!你善魂已失,只余惡魂,怎會不差遣?”
半個魂兒飄然落在春花肩上,對耳語了一聲:“莫怕。”
盛著另外半個魂兒的藺長思收回沾著鮮的長劍,一手執劍,一手攬住春花左肩,將護在后。他雙眸清明,仰首道:
“我確實中了裂魂之。但——”
“不論是哪一半兒的藺長思,都記得要守護長孫春花,從無悔改。”
錢仁的神識在空中大笑起來:
“你以為,刺中了本尊的神識,就能傷了本尊麼?”
巨大的安樂壺破土而出,沖垮了神龕、火燭、布幔和砂石。風渦自壺口而起,黑霧如逃命的蚯蚓般竄壺口。
Advertisement
風渦擴大,霍善道尊雖目不能視,心知不好,一手將金錢劍深土,另一手扯住吳王。
一時間土石紛紛飛起,藺長思抓住春花上臂,手中長劍楔墻壁,但那墻上土皮如泥灰一般,頃刻便剝去了一大塊。藺長思低呼一聲不好,只得攬春花,兩人順著風渦,盤旋了一圈,便沒壺中,不見了。
安樂壺立刻封死,凌空而出,穿窟,破空而去。
與此同時,神像的基座裂開了第三道裂,在霍善和吳王的驚呼中,轟然倒塌。
猜你喜歡
-
完結1257 章
修真界敗類
臭名昭著的死刑犯,死後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這裡沒有四個輪子的賓士,有四個蹄子的寶馬。天上沒有飛機,有在天上飛的仙人。沒有手機電話也沒關係,有千裡傳音……這個世界太瘋狂,前世隻有書裡和電視上才能看到的修真者,在這裡不是幻想,而是真實的存在。死刑犯想,既然來了就要好好活下去,上輩子有過做神仙的夢想,那是不可能滴,這輩子打死也要過把癮……神仙姐姐,我來了!
325.4萬字8 21839 -
完結136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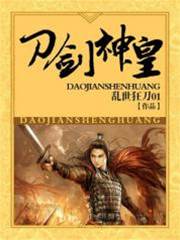
刀劍神皇
「坑爹啊,這麼說來,我真是的穿越了?而且還附身在了一個和我同名同姓並且長的一模一樣的少年的身上?」丁浩坐在洗劍池邊,低頭看著手中一柄破破爛爛的黑鐵鏽劍,又看著水中倒映出來的那張英俊清秀的麵孔,已經呆了一個多時辰,還有點兒難以置信。
332.9萬字8 28914 -
完結1884 章

紫星大帝
修真界巔峰強者飛升通道被神秘黑手擊殺,重生低等位面修武界,卷土重來,斬荊披棘,重返巔峰!紫星神體降臨,天下唯我獨尊!…
347.5萬字8 1716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