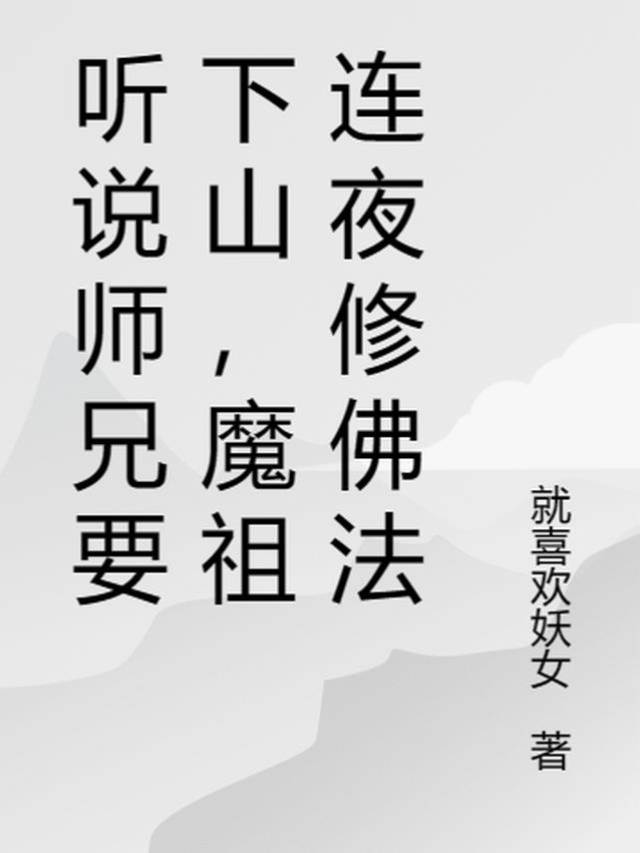《搖歡》 第五十一章
余香惟恐搖歡那壞脾氣能把才見過的那位貌又俊俏的和尚當下酒菜吃了,牽著神行草匆匆沿著原路返回。
神行草邁著小短,跟得有些吃力,他著氣,一手按著下一刻似乎就會被風吹跑的小氈帽,氣吁吁:“余香,小蠢龍不會有事的。”
余香空瞥了他一眼,嗔道:“我擔心的是那和尚。”
神行草:“……”他竟無言以對。
這說起來得怪小蠢龍不良龍的形象實在太過深人心,他心里嘀咕著,目穿過重重朱紅的廊柱向閉著大門的那間房,幽幽地嘆了口氣,希帝君別惱余香才好。
疾步走到房門口,余香在上豎指示意神行草不要發出聲音,自己先側耳覆在門上聽了聽。
房間里安靜得可聞呼吸聲,那呼吸聲且輕且徐,細辯之下唯有一道呼吸聲。
余香臉古怪地了眼也學趴在門邊聽墻角的神行草,心想:“和尚真被吃了?”
神行草聽到的心聲,面凝重地搖搖頭。
他這幾日辛娘葷段子的影響,已開竅了不,當下腦子里閃過雜七雜八的畫面,默默紅了臉。
他掩耳盜鈴般捂住臉,只出的耳朵,使勁地聽門的靜。
里面那道呼吸聲不管是輕是重,都如同能心弦一樣,聽得他浮想聯翩。
難怪小蠢龍以前那麼喜歡聽墻角……真的還蠻好玩的啊。
屋。
搖歡和和尚大眼瞪小眼的瞪了許久,終于因為眼睛發酸先眨了眼睛。
著酸的眼睛,敏的聽覺里頓時出現了不遠余香和神行草的腳步聲。原本也未在意,只那腳步聲走到了門口卻突然停了下來。
搖歡是聽墻角的個中翹楚,一聽這靜心下便已了然,屏息斂氣后用神識往外蔓延開。
Advertisement
余香平日里是匿氣息的好手,只這會匆忙并沒有多加掩飾,再者搖歡和相已久,早已悉的氣息,神識一探便知這兩人正趴在門邊,也不知道要干什麼。
悄悄地從敞開的一扇偏窗翻出去,踩著屋頂落下來,小步挪到門邊的位置,也把耳朵了上去。
余香這才察覺到有人靠近,不耐煩地看去時,一眼便看到搖歡賊眉鼠眼地在聽墻角。那表……真是讓人覺得白瞎了那一張致的臉。
這個念頭剛閃過,便回過神來,嚇得往后退了一大步,指著又了閉著的房門,有些不敢置信:“你你……你怎麼不在里面?”
搖歡了神行草的小氈帽,似笑非笑地看著,雖未開口一言,可那眼神卻比那些未出口的話更讓人覺得尷尬。
余香頓時囧得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擺了,抬眼覷著搖歡,為難地連句解釋都不知如何開口。
神行草仰頭看了看余香,又轉頭了搖歡,推著余香往后退了一步,他著小板把人護在后,擰著他的小眉,抿了抿,一臉認真:“我擔心你把和尚當唐僧吃了,所以才讓余香來看看,你不要瞪了。”
搖歡“嘿”了聲,還未來得及等擼起袖子,鎖骨間那條石頭項鏈驀然一燙,那灼熱如同從火堆里濺出的火星,落在皮上微微的刺痛。
有些愣神地出戴在脖子上的項鏈,不知所措地看向余香:“它……突然燙了。”
話落,房門“吱呀”一聲輕響,尋川推開門,幽邃如墨般化不開的雙眸定定地看向辛府的西北角,低沉的聲音就如風過山時的嗡鳴,一字一句都如手中項鏈一樣灼燙:“那個方向出事了。”
Advertisement
搖歡循著他的目看去,臉頓時一變。
認得那個地方!
那里是姜易養病的雅靜小院,因在辛府的偏遠角落,又有竹林遮擋,就如同和辛府隔開的獨立小院。
那個方向……只能是姜易出事了。
“我去看看。”丟下這句話,搖歡便風而起,忽的想到什麼,扭頭看向面沉重的余香和神行草,叮囑道:“府中來了個道士,你們就留在房。余香,幫我看著些他。”
后半句話,輕了語氣,大概自己也不習慣,很快板起臉毫不憐惜地了一下神行草的小氈帽,在沒有停留,風而去。
神行草被余香攬到側,神有些怔忪地著搖歡離去的方向。那青的背影似還有殘影留在那,看得他忽然心生悲涼。
他眼前似看到了幾千年前,也有這樣一抹頭也不回的影,在他面前轉而去。
此后,他等了很久。
日出,他便坐在池邊向離開的方向,日落,他枕著漫天星宿同眠。就這樣等了不知道多年,把歲月都熬老了,然后等來了一個死的消息。
他無意識地握余香的手,用力的手指關節都有些發白,微抿著的有些發青,就那樣直直盯著離開的方向。
直到頭頂一暖,他才恍然仰起頭。
原本還在站在門口的和尚不知何時走到了他的后,手掌落在他的小氈帽上,像搖歡剛才那樣,輕輕地了他。
神行草眨了眨眼,依賴地抱住尋川。
眼底那些潤被他小心地掩起,唯有殘留的幾分恐懼仍被尋川看在了眼里。
他手中佛珠垂下來,堪堪掛在虎口,念珠撞的聲音清脆,伴著他安的聲音一同響起:“我過去看看,不用擔心。”
Advertisement
神行草用力地點點頭,這才松開他,乖乖地站到余香旁,看著他一步步遠去。
他看似走得慢,實則是地而行,幾步已走了十里,只能遙遙地看見他的背影漸漸后院那曲折的廊檐下。
他回過神,仰頭看著明明知道他有,卻依舊什麼也不問的余香,囁嚅了幾次才懊惱道:“我回淵,以后……可以不用每次開口時都猶豫很久要我什麼了。”
他并不是沒有名字,只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忘了而已。
從離開無名山開始,他的腦中便漸漸開始浮現一些殘影片段,就如破碎的鏡面,四分五裂并不相連,更別提湊回一面完整的鏡子。
他起初還以為是自己能夠預知別人的前世和來生,直到那些殘影漸漸清晰,每一幕里都有搖歡的影,他才明白。那些,是他曾忘卻的記憶。
他是長在瑤池邊的神行草,瑤池化靈,他也有了神識,認了搖歡為主。
后搖歡遇劫險些灰飛煙滅只留下一縷殘魂,他也差一點便消散在這塵世里,是帝君取瑤池之壤重新栽回了他,后隨塑骨重生的搖歡一起到了無名山里。
只是這些他都不記得了,他沉眠了千年,直到隨搖歡出了無名山,他那些記憶才漸漸蘇醒。
他的記憶里或是搖歡似喜似嗔看著他,或是從碧波無垠的瑤池里破水而出時,又或是低眉淺笑眉目安然的模樣,一幀幀如同漸漸拼湊回的鏡面,雖還殘缺卻找回了大半。
而那些還未記起的記憶碎片,正以幾不可查的速度在一點點復原,連同他漸漸蘇醒的能力。
那日。
帝君離開去九重天外前,他在門口等待帝君。
幾天前他已經意識到這些如同夢境一般的殘影是他歷經的回憶,他困擾了許久,還是決定問問帝君。
Advertisement
先不說帝君上古龍神,從上古時期活到現在,就是個現的答疑解的先生。更因為回淵能記起的碎片里不止一次出現過帝君的影。
作為他邊唯一可能知道所有事的人,問他是最簡單快捷的辦法。
帝君并未告訴他當年發生了什麼事,只是了他的腦袋,那眉宇間的惆悵連他都被染了。
“我原本以為會慢慢想起以前的事,不料……”他輕嘆一聲,微攏的眉心看得回淵心口都揪了起來。
“你前世便認了搖歡為主,也注定和一直牽連。當年事你會漸漸想起的,我不再提起。”尋川低頭看著他,勾著角笑了笑,只那眼神似過他看向了別。
他乖乖地等著帝君繼續說下去,等了片刻也沒再等到他開口。
就在他覺得帝君不會再提及此事時,才在他離開前,聽他說:“我等了很多年,耐心地等那縷魂魄能想起前世。大概是覺得自己活不了,才在魂飛魄散前把記憶留給了你。
可怎麼不想想,獨留我一人記得,對我何其殘忍?”
帝君雖是埋怨,可那眼里的意卻厚重得連他也不敢再直視,就像是這些沉淀的歲月里,他把所有都藏在了這雙眼里。
回淵猶豫良久,抿著輕輕地拉住了他的指尖,那涼意如同冬日的冰泉,浸其中只覺涼意徹骨:“帝君你別傷心,我會全部想起來,講給搖歡聽。”
他會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起來,然后告訴。
只是這份期待在當時帝君的笑而不語里漸漸就因想起的往事太過沉重而慢慢消磨。
這輩子那麼沒心沒肺的小蠢龍,原來也會用至深。
前世:
回淵托腮著在瑤池里撈小銀魚的搖歡,氣鼓鼓地又瞪了一眼坐在一旁面帶笑意的男人。
就是這個人,自從被搖歡撿回來后日日和他爭寵。
不是表演百花齊開,就是用法化些小銀魚給搖歡捉著玩,不就是欺負他沒見過世面嗎!
哼,不服!
尋川察覺到回淵的怒意,邊笑意更深。
他指尖輕彈,池水周圍的花瓣無風自舞,有不花瓣隨之飄零著落下,如同盛大的花雨,花瓣落在水面上鋪了一層,層層疊疊的隨著水波來回漾。
回淵瞪大眼,一打滾拍拍屁站起來,張開手對在水中嬉戲的搖歡道:“姐姐,我想泡花瓣澡。”
捉魚捉得正認真的人聞聲回頭,白皙的手臂撥出水紋,一息之間便游到岸邊,把他抱下水來。正回到池中繼續捉魚,似想起什麼,回頭看向尋川,笑意盈盈道:“不許再欺負回淵,吃醋也不行。”
猜你喜歡
-
完結151 章

財神春花
兩個莫得感情的老神仙在人間動感情的故事~神仙日子漫漫長,不搞事情心發慌。北辰元君與財神春花在寒池畔私會偷情,被一群小仙娥逮了個正著。長生天帝下詔,將他二人雙雙貶下凡間,歷劫思過。此時正是大運皇朝天下,太平盛世已過百年,暗潮洶涌,妖孽叢生。汴陵城中長孫家得了一位女公子,出世之時口含一枝金報春,驚得產婆打翻了水盆。長孫老太爺大筆一揮,取名曰:長孫春花。長孫春花只有一生,財神春花卻有無窮無盡的歲月。
42.4萬字8 21070 -
連載45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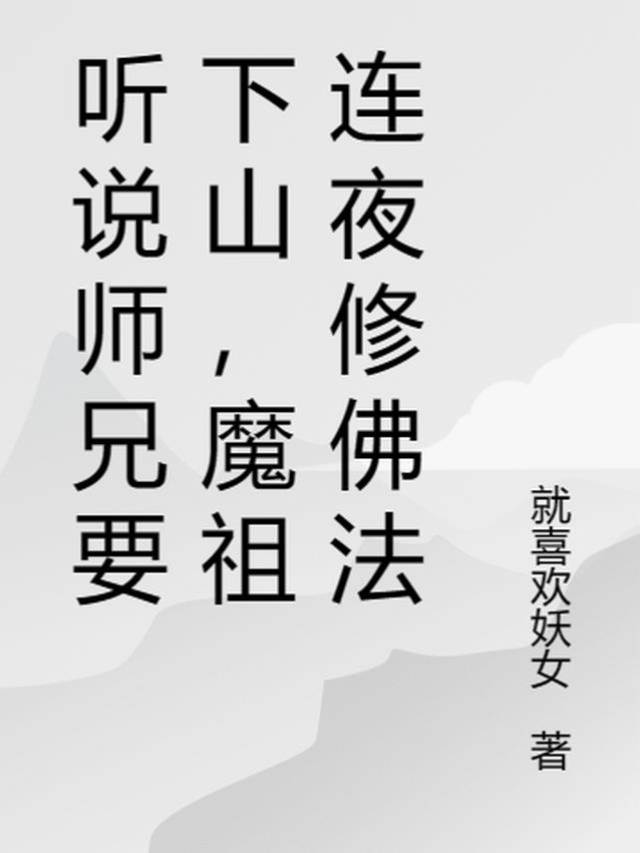
聽說師兄要下山,魔祖連夜修佛法
王慧天,自卑的無靈根患者,劍術通神。自他下山起,世間無安寧!魔祖:“啥?他要下山?快取我袈裟來。”妖族:“該死,我兒肉嫩,快將他躲起來。”禁地:“今日大掃除,明日全體保持靜默,膽敢違令者,扔到山上去”向天地討封,向鬼神要錢。燒一塊錢的香,求百萬元造化。今日不保佑我,明日馬踏仙界……
85.6萬字8.18 130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