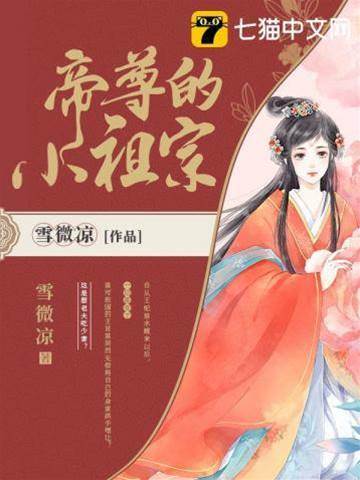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危宮驚夢》 第122章
第122章
命題是有書院最德高重的老夫子所出,無非是先楹聯後填詩。與那其他學子的全投不同,那位玉冠書生倒是有種信步閒庭的從容之,總是第一個收筆,然後便是再抬起頭,目炯炯地向聶清麟。
那熱切的目,就連一旁的邵公主都是有些抵擋不住了,只恨不得展開手裡的巾帕,替妹妹將臉兒遮擋住,免得被那小登徒子用眼兒輕薄了。
不過聶清麟倒是不大在意,落落大方的與他四目相對,最後竟是那看起來心高氣傲的年先是微微紅了臉。白淨的臉頰染上些微的紅霞,當真是上好胭脂也調配不出的顔。
聶清麟將骨扇在座椅的扶手上輕輕敲了敲,角含笑,心裡又是不由得想到:「那隻鮫犬尚未如此荒**時,是否也是有過這般會臉紅的青蔥年紀。」思緒流轉間,突然發現一旁的姐姐目警惕地眼著自己,便微斂了笑意問道:「姐姐為何這般看我?」
聽永安公主這麼一問,八皇姐戰戰兢兢地說:「妹妹臉上的表,好像那搶親的潘府三……」
聶清麟聞言表一垮,姐姐眼拙,倒是哪裡像潘家的外甥?不過倒是小心翼翼收起了挑釁的眼神,母妃一族已經出了不檢點的浪子,總是不好再出個調戲年的浪啊!
幾比試下來,高臺上的三十餘名各個書院選拔出來的學子,便是只剩下五名爭得前三甲了。而那位玉冠書生一直拔得頭籌。最後比試填詩畫時,那玉冠書生又是第一個畫完,並題詩。
待得他的那副遠山重樓圖高高掛起時,引得翻墨樓裡的看客們紛紛贊嘆。
聶清麟也了過去,一眼看出這年仿的是「振林」先生的畫風,筆力講究頓挫有力,凸顯大氣的神韻。
Advertisement
世間振林的筆墨流傳度沒有其他幾位才子廣泛。所以世人皆是不多見本尊的風采。可是聶清麟卻是耳讀目染著,自然能一眼看出這畫雖好,可惜……還是筆力欠了幾分火候。
不過已經是難得的青年才俊,將來必大。最後比試的結果,本次詩會的頭甲是那位頭戴金冠的年,聶清麟這才聽到他名喚隋輕塵。這時,樓下花車評選出了新花魁將一捧獻花安置到了樓上垂下來的籃子中,在街市上衆人的歡笑聲中將由繩子拽了上去。
按照以往的慣例,頭甲了鮮花綉球後,便是要拆解開來,分發給樓中雲英未嫁的府宅小姐們。當然,若是特別屬意哪位小姐,也可以將鮮花綉球盡數奉上,不過此間便冒了風險,若是小姐極其家人不肯接,那麼便有了被婉言謝絕,臉面盡失的風險。
可那年卻幷沒有接過花魁奉上的鮮花綉球,反而是提筆在紙上畫了一株含苞待放的水仙,未等墨跡幹,便走下高臺,舉手將那副畫遞向了聶清麟。
「佳人本當配鮮花,可惜那捧花是過了俗人之手,沾染了紅塵濁氣,不知小姐是否肯笑納這株水中仙子?」說完便是勢在必得地看向了聶清麟。
要知道這位年可是臨安城有的外兼修,家世顯赫的年才俊。他是定居江南的忠轅侯的嫡孫,將來定會繼承爵位,也是這次詩會的熱門佳婿人選。不過這年一向自視甚高,對詩會招婿的環節嗤之以鼻,想想也是,這樣的家底殷厚的侯門怎麼可能娶一個商賈之家的子爲妻?
可是沒想到,他居然出乎衆人意料,主對一位子示好。這般大膽行徑頓時惹得周圍一片嘩然,大家都是小聲議論著不知這位幸運的子是哪家的千金。
Advertisement
聶清麟看著那年的明明目熱切,可是又強自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淡然,不覺心裡微微一笑,眼看著他舉著那張畫紙卻半晌不得回應而臉變得有些尷尬,終於是出手來接過了那張水仙圖。
自己本是匿名登上翻墨樓,占了位置總是要應一應節日的習俗爲好,免得攪了大家的興。果然當接過水仙圖後,那年的一對眼複有明亮,整個翻墨樓裡的人也在竊竊私語,議論著那侯爺府的小公子會不會過後去那位神子的家中提親。
而隋輕塵也是想問一問佳人的府邸在何,還未待他開口。二位佳人已經是起要離開包廂準備率先離開翻墨樓了。
他不由得心裡一急,便也追了上去。可是沒想到二位佳人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卻是站住了。只見在樓梯樓穩穩地站著一位男子,形高大,手柱玉石拐杖,杖把上是一隻著尖牙的虎頭,一白束腰錦衫更是凸顯出男子的濃眉眼,這位英俊男子滿的肅殺之氣將這翻墨樓裡歡愉的氣氛一下子湮滅了不。也許是因爲男子臉頰一側明顯的浮起疤痕,猶如一條蛟龍盤踞在臉側,讓本來俊的臉龐增添了說不出的邪氣,
聶清麟沒想到他竟是會這般毫無預兆的,在闊別數月後出現在了這翻墨樓上,他的臉……竟是怎麼了?
「你怎麼來了,你的臉……」
太傅聞言,眼暗沉,將臉微微側轉似乎在回避著的視綫:「了些意外之傷,已經無妨……看得正是興起時,小姐卻是要走了?」
看他的形分明是來了有一會了,也不知自己方才與那年目傳的模樣眼了幾分。
二人相對,竟是有些生疏尷尬。跟在後麵的單鐵花與魯豫達一見,正要向太傅施禮。可是衛冷侯卻開口道:「這位小姐走得甚是匆忙,在下也有一花相贈,還請小姐留步。
Advertisement
說著他順手拿起了懸掛在側的一隻素白的燈籠。這些燈籠原本是等著書生們比試完畢後,由他們題圖著,到了夜晚裝飾門廊之用。不過衛侯倒是順手拿來當它是作畫的白紙了。也沒用筆,出長指沾著一旁小幾上擺放的特質繪燈顔料畫了一支迎風傲雪的寒梅。
在燈上
作畫與在紙上不同。因爲燈麵褶皺凹凸不平,更是考驗畫者功底。太傅卻是手指微微移輕點,不大會便是畫好了一株寒梅。
這株梅花乍一看平淡無奇,可是很快便發現了其中的妙,那梅花在凹凸的紙麵上因爲角度的不同,竟是觀賞出了不同的花期。產品從側麵去看,好似含苞未放,從正面看,卻已經是花瓣盡開。這等有竹的構圖功底,任何一個對書畫略通皮的人都會嘆服家絕。
這下子人群沸騰開了,紛紛贊嘆這妙的畫工,此時見了著寒梅,回頭再去想翻墨樓裡其他書生的畫作,那些略帶稚氣的手筆當真了湖中水仙--有些孤芳自欣賞的意味了。
尤其是那隋輕塵,更是覺得有些打擊。他一力模仿著振林筆墨,怎麼會認不出這才是歸宗的本家之筆?原本見了這神已久的書畫大家,該是滿心的歡喜,可是這位振林竟是有些與自己搶奪佳人之意,怎麼能不讓他心生懊惱?
這位茂林先生雖有才華,可是方才在拿取燈籠時,腳步踉蹌,竟是個瘸子!而且那臉雖然俊,可是臉側帶疤,這樣的男子雖然是有才華,到底還是配不上這如花的絕佳人!
想到這隋輕塵頓時自信滿滿,將剛剛認出茂林筆墨的震撼清減下了不。
如此看來,他還有機會!
聶清麟慢慢地手接過了龍燈,算是給了太傅大人面子便饒過太傅,徑直離開了翻墨樓。隋輕塵還想攔住去問佳人的芳名,可是卻被這個黑的冷男子攔住,只是被他瞪著,竟是突然覺到他滿的狠獰殺氣,一時間竟是震懾得一也不敢,待到回過神來,樓梯口已經是空空如也……
Advertisement
聶清麟下了樓後,便上了馬車,邵公主怯怯地問方才那個黑男子是誰,聶清麟臉未變說道:「那位是惹不起,躲不了的瘟神。」
可是當馬車回到別館時,瘟神竟然是已經先到了,坐在廳堂裡臉如同化不開的沉墨。只一揮手門邊揮開了閒雜人等。
聶清麟走在一張椅子前慢慢坐下,還是忍不住瞟了他放置在椅側的那拐杖:「太傅久未見面,別來無恙?」
太傅薄微啓,冷聲說道:「看來沒有本侯,公主也是過得安好,今兒若是本侯未曾到場,公主豈不是要與那黃口小兒共譜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話了?」
聶清麟收攏了目,濃黑的睫低垂說道:「有太傅專寵匈奴公主的佳話在前,別的俱了俗事,只是不知道太傅此來,有何貴幹?」
衛侯皺著眉:「你這又是哪裡聽來的,本侯什麼時候專寵什麼匈奴公主了?」
聶清麟略覺詫異地抬起頭:「太傅忘真大,難道匈奴格爾番部的公主在這短短數月也了昨日黃花了不?」
衛冷侯微微挑眉似乎有些恍然:「還道你爲何數月不給本侯發來一封書信,竟是帶著氣兒出的京城,那格爾番部的公主一早就許配給了安邦侯的長子,二人郎才貌正可就一番友邦佳話,難道在公主的眼裡,本侯就是這般不挑食嗎?」
聞言,聶清麟呆愣了片刻,小臉慢慢垂下,太傅見狀甚是滿意,只當小子已經是知錯了,便是和緩了語氣,出手道:「竟是這般的能拈閒醋,還不到本侯這來,讓本侯看看小果兒是否清減了?」
聶清麟慢慢抬起了頭,可是臉上的表卻不是他所想的那樣窘迫加:「原來是這樣,幸好有安邦侯的公子肯提太傅分憂,不過國事勞,太傅若是沒有別的事,還請盡快返回京城,免得耽誤了大事。」說著竟是起徑直要離去。
「站住!」太傅的火氣到底是沒有製住,一下子便是發了出來,他日夜兼程趕往江南,滿心以爲再見面的時候佳人會綿地投懷裡,以藉相思之苦。可是哪裡想到,循著的行程興衝衝地趕到翻墨樓上,卻是見到了那人含笑與那個黃年傳的模樣。一手不流的墨寶,兒還沒有長全就妄想勾搭他衛冷侯的人!
這一聲中氣十足,便是個大漢也要被嚇得雙一,可是那個小人卻是依然穩穩地往外走去。氣得衛冷侯站起了,拄著拐杖幾步搶在了的面前,拉住了的胳膊道:「公主倒是在江南養了心膽了!既然都說了是誤會,你又是在生著什麼悶氣?」
聶清麟苦笑道:「清麟無仗無恃,不敢生太傅的悶氣,只是突然想明白了自己爲何總是患得患失,太傅乃人中俊杰,世間子趨之若鶩。可清麟並不是能守住瑰寶的猛將,與其每日擔心何日會失去,倒不如從來未曾擁有。這數月的分離也足以證明,太傅也幷非是離不得清麟……你我相識以來,經歷得誤會波折太多,可是我也能會到太傅待我真,我亦爲太傅,了真,然濃便有清淡時,清麟乃人間至俗子,若是真到了那天,必定是不得關煎熬之苦,倒不如太傅憐惜,便是在有之時且放了手,讓清麟長居江南,免了煎熬苦惱……」
太傅聞言,氣得青筋已經是蹦起老高,這小子口口聲聲著自己,卻又是轉說要自己放手,以前因他重傷而傷心流淚的模樣猶在眼前,可是轉眼的功夫卻是冷漠得不聞不問。
這是多麼狠的心腸?虧得他還擔心一旦知曉,必定擔心得食不下咽,終日以淚洗麵。現在看來,倒是存了盼著自己早死的心思,然後便是可以自由地與那些個年輕稚的年郎們眉來眼去。這等不守婦道的子,便是浸了豬籠也不解恨。
猜你喜歡
-
完結1860 章

鳳唳江山
戰功赫赫的太子妃重生成廢柴醜女,精分世子強寵不成反被虐。
331.5萬字8 22400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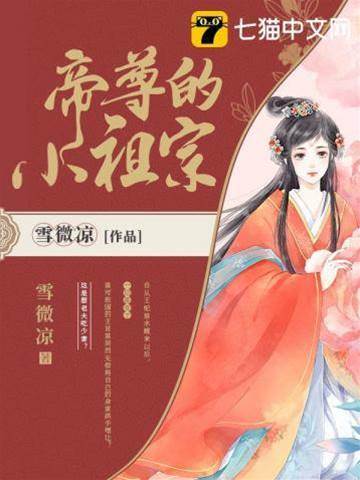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917 章
失寵王妃
墨府二小姐墨柔柔癡傻膽怯,上不得臺面,被太子退婚,淪為了京城笑柄。正當眾人以為她嫁不出去之時,京城首富之子蘇九生和蜀王朱元若爭相求娶。最后蜀王抱得美人歸。蜀王的求娶打亂了墨柔柔的計劃,于是她天天對著蜀王搞事情。成親前,她找人給蜀王施美人計,敗壞他名聲;成親時,她找人搶婚,搶了蜀王,讓他淪為笑柄;成親后,她天天作妖,每天都想著怎麼失寵。蜀王說:“失寵是不可能失寵的,我家王妃有點傻,得寵著。”
111.4萬字8 14385 -
完結578 章

毒醫凰后:妖孽世子霸道寵
癡心錯付,血染佛堂,她是名門嫡女,卻被未婚夫庶妹亂棍打死。 再睜眼……她是華夏鬼醫聖手,心狠手辣的殺手女王,身負毒王系統,一根銀針,活死人,肉白骨;一雙冷眸,穿人骨,懾人心。 當她穿越成了她……一毀渣男天子夢,二踩庶妹成小妾,三送后媽七隻鴨,四虐親爹睜眼瞎……古代生活風生水起,只是暗「賤」 易躲,明、騷、難、防! 他是腹黑神秘的妖孽世子,傲氣孤高,不停撩騷。 當他遇見她……「天下江山為聘,地鋪十里紅妝,我娶你」 「歷史有多遠,請你滾多遠! 關門,放狗」 他上前一步,將她打橫抱起,壓倒在床,邪魅一笑:「一起滾,滾出歷史新高度」
114.9萬字8 451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