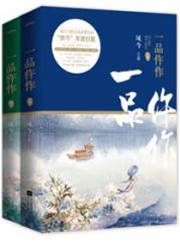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締婚》 第70章 第 70 章
那位大爺上衙去了。
項宜沒怎麼貪睡,早早起洗漱了一番,先去西院看了懷孕的弟妹,在院門口就看見譚建和楊蓁拉著手耳畔低語,只好笑著走了,又去瞧了瞧妹妹。
春夏之,不春花已次第凋謝,只有項寧的院子還春景依舊。
說自己昨晚睡得很好,讓項宜不用擔心,只是問了一句。
「也不曉得寓哥兒一個人在外院習慣不習慣?」
項宜有心讓弟妹分隔開,便道自己一會去看看,讓別心。
「你的腳還沒好利索,莫要走許多路,就在院中好好養傷吧。」
妹妹乖巧,自然是應了,項宜就去了前院,看到項寓早早就起了,這會已經寫好了一篇文章了。
見來了,規矩行禮,似是想問一句什麼,但到底沒問,項宜也沒說,只道附近有書肆,項寓閑來無事可以過去轉一轉。
年低著頭應了,沉默了許多。
項宜心下嘆氣回了正院,有些瑣事須得料理,先理了幾件事,就有針線房的人過來拿了些料子來給挑選。
「是大爺吩咐奴婢們給夫人做夏的料子,夫人選幾匹,奴婢們儘快趕製出來。」
項宜頓了一頓,沒想到那位大爺還記掛著這些事。
順著他的好意挑了幾匹,順便替他也挑了幾匹,最後留下一批青的薄料,「這匹留下吧。」
年節前後,給他做的春裳,他隔兩日就要上一次,明明是新卻穿的有些舊了,這些天熱了起來,也時不時要穿一穿。
既然如此,那再給他做件夏裳吧。
項宜剛讓人把料子留了下來,拿出他的舊比量著裁剪了一會,就見門房的小廝送了一封不知名的信過來。
項宜打開,看到了裡面的殘信,看到最大的那片紙上的字跡,指尖都了一。
Advertisement
把所有含有字跡的紙都拼了拼,定定地看完,腦中哄了起來。
如果此信是真,那麼這封信是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提醒他可以在朝中安排人手,與寫信人的人手一道,掀起一樁「證據確鑿」的貪腐大案。他們把這件案子坐實,讓那個陷在貪腐風波里的人,再不能翻。
這封被燒卻又沒有完全燒毀的信里,那個被針對的人,名字出現在了被燒得發黃的紙片邊緣——項直淵。
房中靜悄悄的,項宜坐在桌案前,看著這封殘信的碎片,一沒,心下卻一下比一下跳的快起來。
是誰送了這封信,又想做什麼?
可惜送信的人並不想讓知道,把信送到手上就消失無影了。
項宜一直都知道父親是被人冤枉的,可是什麼人做的呢?
當時質疑他彈劾他的人太多了,甚至都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而這封殘信並不完整,只是當又細細把信看了一遍,卻在兩個碎紙片上,看到了暗紅的印章痕跡。
這是寫信的人在落款留下來的印,若能破解出來,立刻就能知道寫信人的份。
當即把這兩片含有印章的紙片單獨拿了出來。
印跡在發黃的紙頁上有些不好辨認了,可項宜最擅的就是制印。
仔細將兩片紙張上的印跡描繪了下來,按照制印的技法,沉下心來勾勒了一番。
那殘缺不可辨的印跡,一下就清晰了起來。
而當那個印章上的三個字出現在筆下。
項宜心裡已經有了預,可還是在看到這三個字的時候,渾有些發涼——
昌明林。
昌明林氏,四大世家之首,林大夫人的婆家,項宜前些日才去應邀春宴的林家。
同樣的,也是譚家最的姻親,譚廷的姑父姑母家。
Advertisement
房中一時間靜到讓人發慌。
項宜在那三個字上,看了許久。
信是被不知名的人,特特送到手上來的。
若是料定了能看出「昌明林」的玄機,那麼送到手上,是想離間譚家和林家,或者想要想離間和譚家大爺呢?
而這封信,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項宜不知道,只是恰巧在這個時候,項寓從外院過來了。
弟弟年,項宜沒準備告訴他,將信收了起來才見了他,卻聽見他道。
「大哥聽說我們搬來了譚家,想請我們去酒樓聚一聚。」
確實有些日子沒有見到大哥了。
只是項宜想到顧衍盛,想到他說過,這些年在調查他伯父顧先英葬火場的事同時,也在暗中調查父親的冤案。
項宜立時應了,讓人了項寧,自己也換了一裳,同譚建和楊蓁打了聲招呼,帶著弟弟妹妹出了門去。
顧衍盛定的地方總是偏僻,不過項宜也沒有避諱譚家人,很快就到了。
兄妹四人有些時候沒見面了。
但顧衍盛見了他們姐弟三個,三人中只有了傷的那個還一如往常,另外的姐弟兩人不知怎麼,一個遠山黛眉間攏著愁緒,另一個垂著眼簾沉默無語。
「這是怎麼了?」
他驚奇地問了一句,才見那兩人回了些神。
顧衍盛看了看項宜,又看了看項寓,先笑著問了項寓。
「被書院的先生罵了?」
他這麼說了,項寧也跟在一旁眨著眼睛問了項寓。
「對呀,阿寓你這兩天怎麼了?我又惹你生氣了嗎?」
項寓默默看了一眼,卻又在澄澈的眼睛里,立刻收回了目。
「同你沒什麼關係。」
「那同什麼有關係呀?」追著問。
項寓不想說話了,夾了一塊豌豆糕放到碗里。
「吃飯吧。」
Advertisement
他不說,顧衍盛也不好勉強,倒是又著意瞧了瞧項宜,他也夾了一塊豌豆糕到項宜碗中。
他笑了一聲,特朝向了項宜。
「都先吃飯吧,有什麼事吃完飯說。」
項宜自然不能當著弟妹的面說話,便也收了心思吃飯了。
吃飯完,兄弟姐妹四人先淺淺聊了幾句,項宜便同項寧道,附近有個花圃,讓過去瞧瞧,順便了項寓,道是另一個方向有家書肆,讓他過去看看書。
會試已經結束了,不時就要出榜,近來京城書肆里儘是文人墨客,項寓去看看也好。
項寓看了看項寧,又看了看自己長姐,只好應了。
兩人前腳一走,顧衍盛便倚在椅背上,瞧了他們一眼。
「這兩人是怎麼了?」
項宜了眉心。
項寧的份,連義兄也是不知道的,不便詳說,但想了想,問了另一件事。
「大哥近來可查到了與父親有關的事?」
一問,顧衍盛就歪頭看了一眼。
他道還真的有,「當時朝中義父之事一出,彈劾的人看似多而雜,實則似有控一般,言論甚是有序,所謂的證據也一個接一個地拿出來,讓為義父平反的人措手不及。我近來在留意那些彈劾義父之人的升遷調派,多有些眉目了。」
項宜一聽,便直起了子。
「是不是......和林氏有關?」
話音落地,顧衍盛就認真看了一眼,「宜珍知道什麼了?」
項宜立刻將那封殘信拿了出來,把信給顧衍盛看完,最後指尖點在了兩片碎紙的印跡上。
「這落款印,是昌明林氏了。」
顧衍盛臉上的笑意收了回去,眉頭輕皺。
「是誰給宜珍的?」
他問了,卻見項宜搖了頭。
「不知。」
顧衍盛聽得愣了一下,倏然又笑了起來。
Advertisement
「這可就有意思了。」
不遠的街道上時不時有人聲車馬聲傳來,但這偏僻酒樓的雅間里卻十二分的安靜。
項宜嘆了口氣,「不知道送信的人想做什麼?」
此事已過六七年,手中有此信的人六七年都沒有送過來,眼下突然送來,又能是什麼意思。
不由想到了譚廷,輕輕咬了咬。
「大爺還不知道這件事。」
顧衍盛看了一眼,問了一句。
「宜珍要告訴他嗎?」
項宜默了一默,聲音略有些低。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我想......」
說著,抬起了頭來。
「我想,我早晚是要告訴他,把話說明的。」
這般表了態,顧衍盛默默看著,一時沒有說話。
待譚廷,真的不一樣了。
如果事是真,那麼和林家再不能共下去了。
譚廷夾在和林家之間,若是之前,一定是想著兩人好聚好散,而離開譚家之後,這樣的局面就瓦解了。
但現在,要跟譚廷說清楚了。
如此信任那位譚家宗子嗎?
半晌,顧衍盛才開了口。
「宜珍可以晚些再告訴譚家大爺。」
項宜看過去,見義兄笑了一下。
「這封信是否為真,我們首先得證實一下。」
他指著殘信上提及的兩個名字。
「這兩人都參與了彈劾義父的事,但在當時並沒有出頭,可信上卻特特提及了。如果此信為真,那麼這兩人恐怕在其中有重要作用,我去查實一番,也就知道真假了。」
他說著,微微頓了頓,才又道了一句。
「譚家大爺到底是世家的宗子,是林家的姻親,世家之間的關係盤錯節,宜珍不若等我們查到了實證,再告知他不晚。」
項宜聽了沉默了半晌。
不認為那位大爺會參與林家對他父親的惡行,但誠如義兄所說,譚家是林家的姻親,而世家之間的關係盤錯節。
他們得了這消息,暫時不想打草驚蛇。
窗外的車馬聲遠遠近近地在耳邊,一時有些喧鬧。
項宜看著手中的殘信,點了點頭,應了下來。
顧衍盛看著,輕輕拍了拍的肩頭。
「宜珍不要因此焦慮,大哥有消息會告訴你的。」
「多謝大哥。」
*
下晌,譚廷下衙回了家,就聽說項宜帶著弟弟妹妹出門去的事了,他問了一句,蕭觀過來小聲回了他。
「大爺,夫人今日去見了顧道長。」
顧道士。
譚廷眼皮莫名跳了一下,返回正院的步子都快了些許。
正院,項宜在窗下做針線,剛把今日給他做夏裳的料裁剪好,這會剛調配了線穿了針。
他腳步匆忙地進了房中,還把項宜嚇了一跳。
「大爺下衙了?」見他腳步匆忙,「是有什麼事嗎?」
譚廷定睛看了看坐在窗下的妻子,見安然一如平常,稍稍鬆了口氣,腳步進屋坐到了側。
他說沒事,從茶幾上拿了的茶杯,喝了口茶。
項宜沒察覺,卻不由地想起那封殘信的事,也不知道義兄那便須得幾日能查出來。
餘在邊的男人上微落,暗暗嘆了口氣。
如果真是林家所為,告訴了他,他又準備如何呢。
曉得他待同從前再不相同的,他也是想跟做夫妻的,但那到底是幫襯他良多的林家......
項宜思緒重了起來,手下的針線也有些做的心不在焉了。
微微有些變化,譚廷便看了出來。
方才他看,還以為這次去見那道士只是如常小聚而已,可當下看起來,卻好似不太一樣了。
他想起蕭觀說的話,蕭觀說用完飯後,項寧和項寓都有一段時候離開了雅間,只剩下和那顧道士在雅間說話。
譚廷心下一跳,見這會又走了神似得,低著頭手下針線都慢了起來,不由便問了一句。
「宜珍今日見舅兄了?」
項宜本也沒瞞他,順著他的話點了點頭。
譚廷又問了一句,「我沒能去,不知道宜珍同舅兄都聊了些什麼?」
他這般問了,算是問得頗為明確的。
他跟說過,他們是夫妻,能同顧衍盛說得話,也總該能告訴他吧。
他問了,看著,卻見飛快地看了自己一眼,若不是他看著,幾乎都不會察覺。
而他卻聽見道。
「沒說什麼,尋常吃飯罷了。」
話音落地,整間正房都陷了凝滯之中。
譚廷頓了一下,低了低頭,莫名地,竟然有些想笑。
「是嗎?」
他嗓音寡淡了許多。
項宜還以為他上衙一日,有些累了,便起了來。
「妾伺候大爺換裳吧。」
這些日子以來,譚廷多半都不需要伺候的,但今日卻沒有拒絕,低聲道了一句。
「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754 章

肥婆種田:山裡相公太腹黑
一朝穿越到古代,塗新月發現自己成了死肥婆。不僅又胖又傻,還被表妹和未婚夫聯手設計,嫁給了村裡最窮的書生!沒事,她可是21世紀的特種兵軍醫!還有靈泉在手!渣男背叛?一巴掌啪啪啪打臉!極品親戚?一腳送她們上一天!說她醜的?她搖身一變美瞎對方的眼!隻是,她本想安靜的種種田,發家致富。那俊俏的小相公為何像打了雞血,不僅夜裡猛如狼,還一不小心權傾了朝野……
314.9萬字8.25 731118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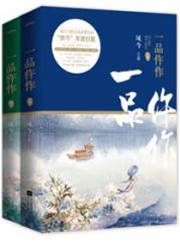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7668 -
連載287 章

世子嫌棄,嫡女重生後轉嫁攝政王
雲念一直以為自己是爹娘最寵愛的人,直到表妹住進了家裏,她看著爹爹對她稱讚有加,看著母親為她換了雲念最愛的海棠花,看著竹馬對她噓寒問暖,暗衛對她死心塌地,看著哥哥為了她鞭打自己,看著未婚夫對她述說愛意,她哭鬧著去爭去搶,換來的是責罵禁閉,還有被淩遲的絕望痛苦。 重來一世,她再也不要爭搶了,爹爹娘親,竹馬暗衛,未婚夫和哥哥,她統統不要了,表妹想要就拿去,她隻想好好活下去,再找到上一輩子給自己收屍的恩人,然後報答他, 隻是恩人為何用那樣炙熱的眼神看她,為何哄著她看河燈看煙火,還說喜歡她。為何前世傷害她的人們又悲傷地看著她,懇求她別離開,說後悔了求原諒,她才不要原諒,今生她隻要一個人。 衛青玨是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從未有人敢正眼看他,可為何這個小女子看他的眼神如此不成體統,難道是喜歡他? 罷了,這嬌柔又難養的女子也隻有他能消受了,不如收到自己身邊,成全她的心願,可當他問雲念擇婿標準時,她竟然說自己的暗衛就很不錯, 衛青玨把雲念堵在牆角,眼底是深沉熾熱的占有欲,他看她兔子一樣微紅的眼睛,咬牙威脅:“你敢嫁別人試試,我看誰不知死活敢娶我的王後。”
52.8萬字8.18 50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