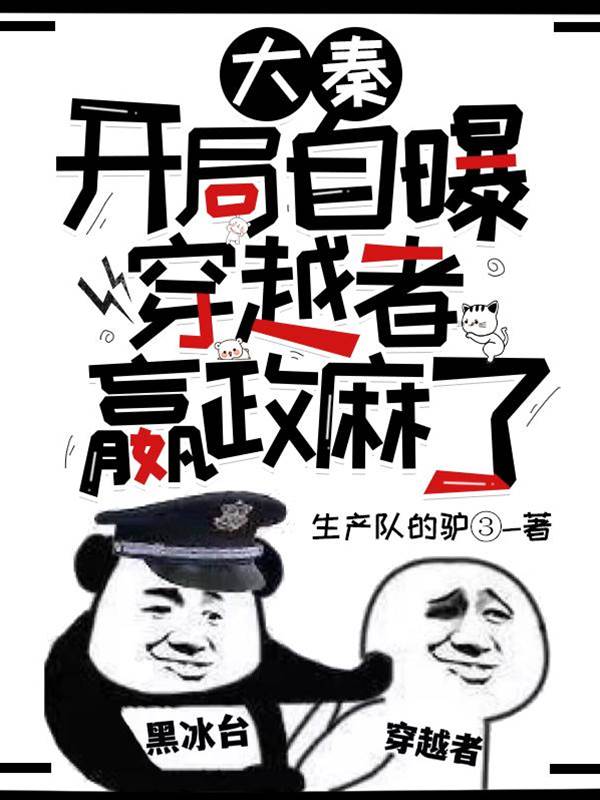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渡佛》 第132章 一百三十二章
♂nbsp;
衡玉睡醒午覺,
起綰發時,才發現了悟為雕的那梔子花木簪從中間部分斷裂開了。
木簪是用普通木料雕琢而,一戴便是數十年時間,
木料本早就有些脆了,
縱使一直小心護著,
還是斷了。
衡玉將斷兩截的木簪收起來,赤腳走下床。
本就是冰靈,溫比尋常人要低上不。
這些日子里,的溫下降得更厲害。現在赤腳踩在地板上,竟是地板反向傳來暖意。
衡玉走到香爐邊,往已經燃盡的爐里重新丟一塊雪松香。
這種清淺而干凈的味道彌漫開來,
緩解大腦的錐痛。
但余瞥見那盆忘憂草時,衡玉的大腦又開始疼起來。
窗臺上,
忘憂草迎風招展,
開出熾盛而紅艷的花。
它通淺綠,
葉片呈鋸齒狀,
生長得格外神,
任哪一個不知的人路過一瞧,定會覺得這盆花的主人把它照料得極好。
其實衡玉沒怎麼照料它,
除了從不忘記每月澆灌一次,
絕大多數時候,
都是扔在那里把它當作不存在。
——只不過是越殘忍澆灌出來的植株越人罷了。
“花期差不多了,還有半個月就能結果功了吧。”
衡玉注視著忘憂草,心底盤算起剩余的時間。
思索時,
用牙齒慢慢咬掉刀鞘,鋒利的刀刃映出平靜的容貌。湊得近了,衡玉仿佛能嗅到刀刃上殘存的淡淡腥味。
右手要握筆寫字畫陣,
每一次都是劃破自己的左手手掌。
一年零兩個月,十四次澆灌,反反復復,即使是最好的丹藥也再也消不去掌心的刀疤。
現在是第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
Advertisement
鮮從流出來,衡玉溫漸漸降低。
攥服,聞著空氣中彌散開的濃烈雪松香,才覺得好許多。
當收手時,臉早已煞白,而花盆里盛開的忘憂花朵已經凋零,只剩下一顆青未的果子。
抹干凈刀刃后,衡玉將匕首歸刀鞘里。
沉默著吞服丹藥,用細絹給自己包扎傷口,遮擋住那格外猙獰的傷口。
頭疼得似乎更厲害了,還帶著失過多的暈眩。衡玉下不適,走到桌案前,用沒傷的右手研墨。
提起筆展開信紙,衡玉思索著要寫什麼。
“……罷了,先給他介紹下忘憂果吧。”
很快,空白的信紙落下第一行字:【忘憂果的作用】
只字沒提忘憂果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只是娓娓將服用忘憂果后會發生何事告知了悟。
寫到‘忘’二字時,有些恍惚,一滴墨濺落在信紙上迅速暈染開,讓原本漂亮的一頁字變得有些臟。
衡玉瞧著不順眼,將紙張作一團,重新展開書寫。
介紹完忘憂草的作用后,衡玉安靜站了很久。
淡薄的秋斜照戶。
衡玉垂下眼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才發現自己這短短一年居然瘦削不。
用力咳了兩聲,開始給了悟寫信。
原本想老老實實遵循寫信格式,但實在太累了,失過多讓這個元嬰修士也格外不好。于是衡玉干脆直奔主題。。
[服下忘憂果,度過劫。]
開篇第一句話,衡玉便如此寫道。
語氣強,過于堅決。
[我曾機緣巧合下得過佛祖指點,并與他有過如下對話。
-你覺得這世上有永遠正確的人嗎?
-沒有……即使是劍祖、陣祖這般先賢。
Advertisement
-但絕大多數時候,他們的話都是正確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思路,是窮盡漫長歲月探尋出來的。也許花上同樣漫長的時間,后人能找出不同的解決思路,但那耗的時間太長了。不破不立。
與佛祖這番對話后,我曾于無定宗見過你。
你看,局勢越來越嚴峻,佛門信徒、你的師弟、無定宗長老、你的師祖他們都在質疑你都在你,佛祖降下指引,現在連我也決定放下你,你再沒有堅持的理由了]
寫完這些后,衡玉猛地丟掉手中的筆。
渾都著疲倦,力氣仿佛被全部剝奪,連走回床榻都沒辦法。于是蜷到桌子底下,背脊抵著桌子沉沉睡過去。
夢里都是驚濤駭浪,睡得格外不踏實,不自覺蹙起眉心。
-
封印地清冷而幽寂,這數千上萬年來從未變過。
了悟坐在秋千上翻閱佛經。
他算著時間,過幾日就該離開封印地趕回宗門,進玄佛鏡里面試煉。
正在想著后續的安排時,了悟應到十幾里地外有修士的靈力波。
那抹靈力波屬于師弟了鶴,了悟便沒有過多關注。
小半刻鐘后,腳步聲在了悟院子外響起,很快,已經晉結丹期的了鶴走進院子里了悟行禮。
“怎麼突然過來了,是要送什麼東西過來嗎?”了悟問道。
了鶴將兩個儲袋遞給了悟:“這是靜守祖師命我送來給師兄的。”
看著那兩個儲袋,了悟微微一愣。
他從中察覺到兩種不同的靈力波——其中一個是主的,另一個,是他的。
也就是說,他當時千里迢迢送去合歡宗的儲袋,并沒有拆開看過,現在全部原封不還給了他。
莫名地,他想到一種可能。
Advertisement
這種可能讓他覺得自己的心尖被針刺到了。
綿的疼蔓延開來,便有了如墜冰窖之。
“師兄……”了鶴見他遲遲不接,茫然抬眼看去。
了悟沉默著,沒有失態的接過儲袋:“多謝。”指著一空的廂房,“你遠道而來,進里面歇息一晚,明日再啟程回宗門吧。”
了鶴被他的氣勢所,只得順著他的話。
等院子空下來后,了悟坐回秋千上,先將自己送去的儲袋里的東西取出來。
——里面沒任何名貴的東西,只有一蝴蝶形狀的玉簪。
簪子尾部蝴蝶振翅飛、栩栩如生。
玉簪格外致,可以看出雕刻者的用心程度。
他捧著玉簪枯坐很久,再開口時聲音喑啞低沉下來:“這只簪子果然還是雕得不夠好看。”
不夠好的東西是不應該給那位姑娘的。
了悟將玉簪收起來,取出另一個儲袋里的東西。
里面的東西也很簡單,一個木盒、一封書信。
他最先慢慢撕開信封,將里面的薄薄兩頁紙展開。
紙上的字跡格外悉。
他看得很慢很慢,慢到足以將紙上的每一個字都深深印刻心底。
吃力地將兩張信紙閱讀完,了悟打開木盒。
紅潤而飽滿的忘憂果安安靜靜躺在里面,看起來格外多鮮,似乎是正在人將它直接服下。
“忘憂果……”
了悟垂首闔目,神里的忍與痛苦格外扎眼。
“你怎麼把它種了出來,這一年多來,你就一直在著這種煎熬嗎……”
-
香爐里,雪松香燃得格外旺盛。
衡玉坐在桌案前寫字。這段時間,對測魔陣法的研究有了突破進展,現在正在整理自己這段時間的研究果。
寫字寫得累了,衡玉放下筆活手腕,正要再提筆寫字,有人站在院子外抬手敲擊那扇閉的木窗。
Advertisement
衡玉微愣,起將木窗支起來。
舞正準備大笑朝打招呼,瞧見的模樣愣了下,先前打好的腹稿全部咽下:“你好像瘦了。”又聞了下那飄逸出來的雪松香,“你熏的什麼香,燃得也太多了吧,味道有點重。”
“是瘦了些。燃的是安神一類的香,我需要借它來靜神。”衡玉點頭直接承認,移開話題問道,“你出關了?”
“這個問題還用問嗎!”舞控訴,“我現在出現在你眼前就是最好的答案。”
衡玉角上揚,又說:“你是怎麼進我院子的。”
“小白讓我進來的啊。”舞得意洋洋道,“出關得早不如出關得巧,今晚是一年一度的花燈節,怎麼樣,要不要出門一塊兒去逛逛?”
又到花燈節了嗎?
衡玉原想拒絕,但轉念一想,這一年多時間連自己的院子都很踏出去,現在事塵埃落定,也該出去走走了。
到的拒絕便咽下,衡玉改口道:“好啊。”
-
衡玉坐在梳妝鏡前。
原本不想上妝,但難得熱鬧,又有一眾師妹們跟在旁邊,若是表現出自己的哀愁與憔悴,反倒影響了其他人玩鬧的興致。
這沒有必要。
衡玉慢慢用螺子黛描眉,再往蒼白的上點抹胭脂。
銅鏡清晰映出的容貌。
修真者容貌難衰,和前一次參加花燈節時變化不大,只是比上回瘦了很多,瞧著反倒沒有先時艷。
換上青長,戴好面,衡玉出門去和舞他們匯合。
殘斜照,華燈初上。
漂亮的燈籠早已掛滿街道兩側。
和師妹們一塊兒用過晚飯后,衡玉提著一盞燈籠慢慢走著。
這個點已是夜,各種形制的燈籠全部燃燒起來,昏黃的燈將衡玉籠罩住,清清楚楚照出的容貌。
衡玉走得有些慢,不知不覺間就和師妹們分道揚鑣。
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便順著人流一路走到街尾。
街尾這邊沒什麼人煙,自然也沒掛有燈籠,天際的月亮投照下月,勉勉強強讓街尾沒那麼昏暗。
衡玉在原地站了片刻,覺得無聊便轉,要折返回熱鬧猜燈謎。
轉的剎那,看到,街尾暗那棵高大的榕樹旁,靜靜立著一個悉的人。
他站在燈火闌珊,不知注視了多久。
兩人目撞上時,他輕輕朝微笑。
衡玉的肩膀下意識抖起來,呼吸不自覺急促。
想直接轉離開,可在這一刻,猶如失去自己對的把控一般,無論如何都挪不步子。
“你瘦了許多。”
了悟從暗走出來,來到面前時自然而然手接過燈籠。
衡玉反應過來時,原本提在手里的燈籠已經被他接了過去。那燈籠燃燒的燭映出他的容貌,衡玉又仔細打量他幾眼:“怎麼過來了。”
了悟說:“擔心你。”
“我有什麼可擔心的。”衡玉揚眉,“吃好喝好,還跟著師妹們一塊兒來花燈節玩。反倒是你在宗門里備眾人異樣的目。而且,按理來說你該恨我的絕才是。”
了悟沒說話。
他只是手牽起的右手,將的掌心攤開。
瞧著沒有傷痕,他松開的右手,就要去牽的左手。
“了悟!”衡玉像是惱了般,往后退開一步,“我已經決定放棄你了,你又何必再來見我擾彼此的思緒。”
了悟沒別的緒,他輕聲哄道:“讓貧僧看看你的左手手心好不好?”
這一刻,兩人的相模式仿佛顛倒過來般。在退,在不安,而他溫地哄。
衡玉眉間仿佛浸著三分冷意。
微微擰著眉注視了悟,很顯然,他知道忘憂果是如何培養出來的。
見沒應,卻也沒走,了悟便不做強求。他將燈籠往上提了些,目先是在那張半面木質面上停留片刻,才移到下:“主瘦了很多。”
“我現在已經是宗門長老。”
了悟笑,順著的話說:“長老。”
衡玉眉梢微挑:“……你不會是被刺激得黑化了吧。”
黑化?
了悟從字面理解這個詞的意思,慢慢搖頭。
“那你還這麼心平氣和與我對話。”
“你吻貧僧一下,貧僧就告訴你原因。”了悟含笑說。
衡玉轉走人,連燈籠也懶得搶回來。
但才往外走了兩步,就被了悟攥住袖子:“貧僧會服下忘憂果。千里迢迢從封印地趕來此,長老連些許時間都不愿意空出來嗎?”
猜你喜歡
-
完結444 章

七零炮灰小辣妻
陸清清一覺睡醒來到了七零年代,懷裏躺了個崽子張嘴就喊娘。 可崽子他爹要離婚,大嫂二哥要分家,剩下個三哥是傻瓜....... 陸清清扶額,她這是穿到了死對頭寫的破書裏! 好巧不巧,她還有她全家,都是書裏的無名小炮灰..... 炮灰? 誓死不做! 七零小傻妻,身揣空間金手指,腳踩極品力虐渣,帶領全家翻身逆襲!
85.2萬字8 100968 -
完結94 章

穿成女兒奴大佬的前妻
江柔第一次看到那個男人是在審訊室里。落魄、沉默、陰鷙.狠辣的眼神,嘴角嘲諷的笑,但這人無疑又是好看的,哪怕已經四十了,眼角染上了細紋,依舊俊美非凡,很難想象他年輕那會兒是什麼模樣。這人叫黎宵,是警方追蹤了十一年的逃犯,這次能將他逮捕歸案,也…
37.7萬字8 10596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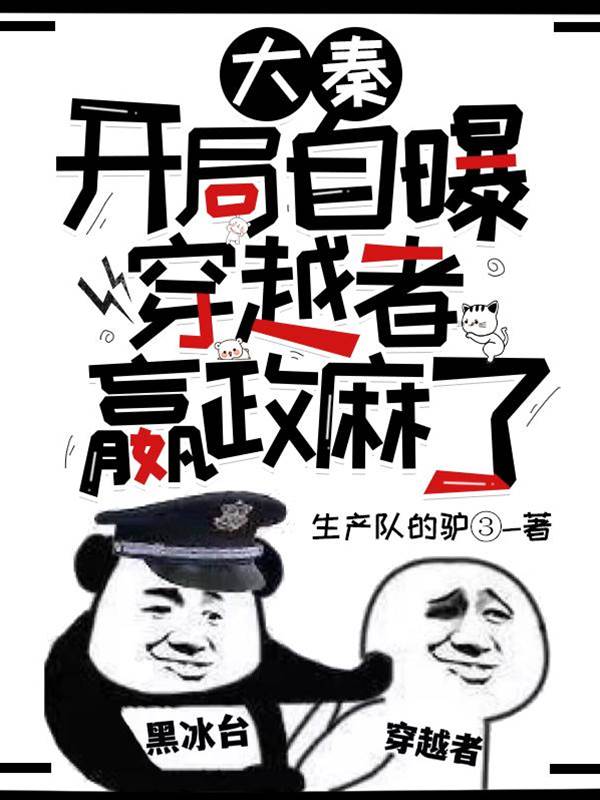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1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