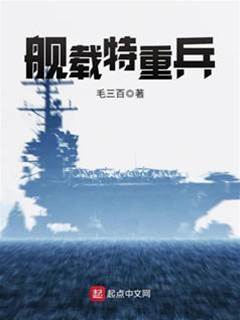《北宋穿越指南》 0064【大鬧縣衙】
兩個灰公人,執仗守在縣衙門口。
見數百弓手怒氣沖沖走來,起初并未在意,還以為他們只是路過。
直到朱銘走向大門,二人連忙上前:“朱都頭,可有事求見縣尊?你們走偏門便是,今日縣尊不辦公,正門這里走不通的。”
“有吏克扣弓手口糧,我們是來鬧糧的,”朱銘一把將其推開,呵斥道,“閃一邊去,莫要我們手!”
誰不曉得向知縣昨日發了橫財?
誰又不知那筆橫財,是朱都頭幫忙帶回來的?
在衙役們眼中,朱銘絕對是向知縣的心腹紅人。更何況,還有三百多弓手同來,這兩個看門的本不敢阻攔。
“快進去報信,要出子了!”
朱銘帶人快步往里走,突然想起自己不認識路,隨手抓了個打雜的:“戶案在哪邊辦公?快快帶路!”
弓手們的錢糧,自然該到縣尉司去領。
但縣尉一直由祝主簿兼任,如今已涼了。縣尉司那些管事兒的,也是祝主簿的親信,一并被弓手們干死。
今天鬧糧,只能找戶案司。
何司是白二郎的親信,他接到消息有些慌,三步并作兩步往外走,剛踏出門檻就跟朱銘撞上。
朱銘一把揪住其領,問道:“哪個是戶案何司?”
何司連忙套近乎:“俺就是何司,俺是白押司的人。”
“我管你是誰的人,”朱銘怒喝道,“弓手拼命殺賊,你卻克扣錢糧。每天吃兩頓稀的,如何還有力氣練?”
何司辯解道:“俺也是按慣例發糧……啊!”
沒等這貨說完,朱銘一拳頭就砸過去,喝問道:“你真是按例發糧?”
這拳打在何司臉上,他頭昏眼花道:“真是按……哎喲!”
朱銘又是一拳頭,何司的鼻都流出來。
Advertisement
“打得好!”
“打死這賊廝,他讓俺吃沙子!”
見到何司被打出,弓手們歡呼喝彩,恨不得自己也上去來一下。
“縣尊仁百姓、恤士卒,誰不知道他是個好?”朱銘開始扣帽子了,“你這鳥人,欺上瞞下,定將縣尊撥發的錢糧克扣了!我且問你,明日弓手伙食,吃干的還是稀的?”
何司是真怕了,忙不迭說:“干的,明日吃干的……啊!莫打了,莫打了,好漢饒命!”
朱銘連扇幾個耳,又問:“飯里還摻不摻沙子?”
“不摻,不摻,”何司害怕繼續被打,飛快喊道,“俺讓糧庫發好米,都是大白米,好漢饒俺一命!”
“廢!”
朱銘一腳將其踹翻在地,大步踏進戶案辦公室,指著里面的文吏說:“今日只略施懲戒,誰敢再克扣錢糧,我先把他打得半死,再拖去縣尊面前評理!爾等可都聽見了?”
“聽見了,聽見了。”
幾個文吏連忙答應,生怕自己說得太慢,也被這姓朱的胖揍一頓。
朱銘這才作罷,轉喊道:“我們走,回校場練去!”
“練去!”
“俺聽朱都頭的!”
“今天真個痛快,朱都頭是條漢子。”
“換作是俺,便把這賊打死!”
“……”
弓手們心暢快無比,七八舌吼起來,在縣衙六案班房前喊得震天響。
便是旁邊的禮案、吏案,文吏們都嚇得面如土。他們一句話也不敢說,只趴在門后看,害怕弓手沖進來見人就打。
陳子翼跟朱銘一樣沒心沒肺,不怕把事鬧大,拍手笑贊道:“朱兄弟好手段,真個威風凜凜,得空了一起吃酒去!”
“等滅了賊寇再吃酒。”
朱銘往外走幾步,忽然想起個事兒,回頭質問何司:“縣尉司兵不堪用,我們買了些竹子鍋蓋,縣尊已答應撥錢來,為何現在都沒見到?”
Advertisement
何司捂著臉連連后退,指向縣衙大堂另一側,驚恐道:“已經撥錢了,在兵案那邊。”
朱銘當即擼起袖子,朝兵案班房走去。
兵案的胡司慌忙大喊:“錢,快拿錢來!”
不等朱銘走近,胡司已捧錢迎上,屈賠笑道:“錢在這里,俺本想下午送去,不料朱都頭上午便來了。”
“就這些?”
朱銘掃視一眼,雖然沒細數,但頂多有兩三百錢。
胡司忙說:“戶案只給了這多。”
“嗯?”朱銘轉看向何司。
何司早已鼻青臉腫,尖道:“還有的,還有的,快快取錢來!”
好不容易湊足一貫,朱銘不甚滿意:“當我是來討飯的乞丐?”
何司嚇得兩,語氣中甚至帶著哭聲:“好漢容秉,縣尊只撥了這麼多。”
“我卻不信,恐怕還有。”朱銘舉起拳頭。
何司慌忙忙喊:“有,好漢要多有多!”
朱銘把拳頭散開,變掌說:“五貫才夠。”
“便是五貫,快快給錢!”何司朝著戶案文吏們吼。
朱銘吩咐白勝:“帶人去拿錢。”
白崇武早就聞訊趕來,一直站在暗冷眼旁觀。
等朱銘要帶著弓手離開,白崇武才笑盈盈走出來。他的綽號是“笑面虎”,見誰都笑臉相迎。
“朱都頭慢走,”白崇武笑著拱手說,“錢糧之事,都是誤會,或許下面哪個小吏克扣了。”
朱銘一改之前的囂張暴躁,瞬間變得溫文爾雅,他甚至把擼起的袖子放下來,如同士子一般作揖:“白二哥既然這般說,那就定是場誤會。”
白崇武拉著朱銘的手:“俺送賢弟出去。”
“請。”朱銘謙讓道。
一直把朱銘禮送出縣衙,白崇武這才折返回,六案司齊刷刷迎上來,請求白崇武嚴懲朱銘和一眾弓手。
Advertisement
被打得最慘的何司,鼻孔里還塞著草紙止,哭哭啼啼告狀道:“二哥,這姓朱的欺人太甚,萬萬不能輕易放過。”
白崇武收起笑容,問道:“你們可知,那些弓手日夜練,是要去剿滅黑風寨的賊寇?”
“俺知道。”司們回答。
白崇武咬牙切齒,瞪著六案司,厲聲說道:“你們可知,黑風寨賊人劫掠俺家,俺九十歲的老祖母歿了!”
“知……知道。”司們全部低頭,不敢與白二郎對視。
白崇武雙眼通紅,嘶聲怒吼道:“弓手要給俺老祖母報仇,爾等竟敢克扣錢糧。此事傳出去,那些不明真相的,還以為是俺在授意。俺什麼了?俺便是那不孝子孫!滾!全都滾!”
幾個司連忙退下,他們是真不占理。
其中還有兩人,是老白員外親手提拔的。弓手要給他們恩主的親媽報仇,他們卻還手弄錢,傳出去全是不忠不孝之輩,比貪污軍糧的質更為惡劣!
話雖如此,但他們依舊怨恨朱銘。
尤其是被當眾暴打的何司,那麼多人看著,他必然為笑料,跟社死沒啥區別。
白崇武怒氣沖沖回自己辦公室,坐著沉思良久,突然自言自語:“這個朱大郎,還真沒看出來,年紀輕輕便是那般豪強人。”
朱銘的做法,在白崇武看來,簡直匪夷所思。
一個臨時任命的白都頭,敢帶著隨時可能解散的弓手,直接沖進縣衙暴打司,強行索要被克扣的錢糧。
他就不怕事后被人報復?
聯想到昨天向知縣發了筆橫財,全程由朱銘帶人幫忙,白崇武心里生出一個念頭。
朱銘……投靠了向知縣!
祝主簿已經死了,向知縣若想掌控縣衙,就要跟衙吏們正面撞上。
向知縣手底下沒人,必須借助外力。而朱銘和那群弓手就是外力,雖然隨時可能解散隊伍,但向知縣一聲令下就能重新召集。
Advertisement
說不定,今天朱銘大鬧縣衙,也是向知縣在暗中授意!
白崇武覺得自己想明白了,他已經猜到了真相。
由于宋代嚴地方私聘幕僚,知縣邊連個師爺都沒有,發展到南宋就徹底失控,掌權的衙吏被呼作“立地知縣”(明清師爺,不是電視劇里那樣拿把折扇只出主意。掛號師爺掌管文書,刑名師爺斷案判獄,錢谷師爺征稅管錢,這樣才能控制縣衙。誰敢在宋朝這麼做,可以告他意圖謀反。嗯,金兵南下時除外,岳飛手下就有一堆幕僚)。
北宋的地方狀況,雖然不如南宋糟糕,但從哲宗朝開始就一路下。
知縣不攬權還好,衙吏們非常配合,并在配合當中欺上瞞下、大撈好。一旦知縣想要攬權,或者想干什麼正事兒,就要跟衙吏們發激烈沖突。
白崇武認為,朱銘是向知縣的一把刀,是懸在衙吏們頭頂的一把刀。
唉,雖死了一個祝主簿,恐怕縣衙依舊難以安穩。
大家和和氣氣,一起撈錢多好,何必要打打殺殺呢?
猜你喜歡
-
完結552 章
我不想長生不死啊
時至今日,大唐帝國已經達到了國力的巔峰,萬邦來朝,萬國納貢。當萬國使者帶著滿滿誠意,來聆聽帶領大唐走向巔峰的皇帝李城發言時……各國使者:“尊敬的大唐皇帝,請問您是如何帶領大唐走向巔峰的?”李城:“特麼的,誰再說朕帶領的,朕把他頭卸了!都說了,朕那都是在敗大唐國力!”各國使者:“我們都懂,都懂……”【已有完本百萬字
94.5萬字8 9795 -
連載1100 章
顛覆了這是皇帝聊天羣
陳通最近加入了一個奇怪的聊天羣。動不動就聊歷史大事,起的名字也很中二。大秦真龍,雖遠必誅,千古李二,人妻之友,基建狂魔,反神先鋒,幻海之心等等一系列中二的網名。千古李二:陳通,唐太宗應該算是千古一帝吧?陳通:你怕不是誤解了千古兩字?比起殷紂王這種蓋世雄主來說,他都差得遠,頂多算是個盛世明君。“什麼?紂王也能算是聖賢之君?”“紂王你瞭解嗎?隋煬帝你懂嗎?不懂請不要黑。”“誰第一個向神權發起抗爭?”“誰真正做到了依法治國?”“誰才真正使得南北貫通,打破階層固化?”“知道什麼纔是真正的歷史嗎?誰纔是在皇帝這個職業中的頂級大佬嗎》?”“始夏,烈商,禮周,霸秦,強漢,弱晉,雄隋,盛唐,婦(富)宋,猛元,硬明....瞭解下。”顛覆你心中的千古一帝。大秦真龍:“知寡人者,陳通也,不裝了,攤牌了,........把寡人的太阿劍給陳通砸核桃吃吧!”
318.7萬字8 16876 -
完結7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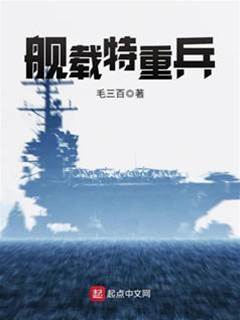
艦載特重兵
每當我們船遇到十級風浪的時候,我戰友不會有絲毫的擔憂,因爲他們知道船上還有我。
133.2萬字8 7383 -
連載990 章

北宋大官人
穿越到大宋,我竟然成了西門慶。可以把金蓮娶回家,但是絕對不能被武鬆殺掉!
163.6萬字8 7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