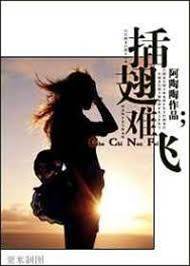《總有老師要請家長》 96、96
滾|灼的呼吸撲到臉上,陸知喬覺得,偏了偏頭,下倏地被捉住,一輕的力道迫使轉回臉。
臉微微熱,祁言的挨了上來。
陸知喬繃著腰,忽而有些張,不是因為頰邊的吻,而是祁言提到的“見爸媽”,口像著塊石頭,悶悶的,不過氣。
兩人在一起不到半個月,還未嚐夠歡愉甜的熱滋味,就要見家長,怎麽都太快了些。況且,在心裏,祁總仍然是祁總,冷不丁要轉變“祁言父親”,甚至自己也要喊一聲“爸”,終歸是不習慣。
臉上出猶豫的表。
祁言覺出緒,似是意料之中,笑著安:“沒關係,如果你沒準備好就不急,我跟他們等一段時間。”
“嗯。”陸知喬點頭,往邊靠了靠,“再等等吧,我覺得太快了。”
“好。”
覺今的陸知喬格外,妝容化得致可人,多一分濃豔,一分寡淡,不濃不淡剛好,尤其帶著橘調的紅棕口紅,襯得雙潤,頗有氣場。
穿了件墨藍半袖襯衫,不變的立領款式,扣子仍舊扣到最上麵一顆,遮得嚴嚴實實。可越是遮掩著,就越惹人窺探裏麵的。
祁言盯著領|子,眼神不熱起來。
車裏冷氣開得很足,卻不夠製心底的火,鼻尖香氣更是催生出忍的念想,下一秒,祁言探向前,如同趁勢發起進攻的猛,攫住了那片。
“唔——”
陸知喬猝不及防被圈住,立刻便了,後腦險些要撞到車窗,一隻手卻及時托在後麵護住。
閉上眼,任由這人造次。
油巧克力香味暈開了,祁言又糊滿口紅,渾不在意,昨晚不得盡興,今可要討回來。
“言言——”
Advertisement
陸知喬低哼一聲,捉住祁言的手,偏頭躲開,“現在不行”
還以為這人隻是親一親,打鬧,誰知越來越得寸進尺,不安生。雖然是在車裏,但寫字樓外麵人來人往,稍不留神就會被人瞧見,沒有安全,尤其經過昨晚那事,害怕。
“嗯?那就是以後行了?”祁言立時停下來,揚了揚眉,裏不忘調|戲。
陸知喬睜開眼,見眸裏狡黠的笑意,沒惱,極為配合地放嗓音:“以後,你想怎樣就怎樣。”完主勾住頸|子,把臉埋進頭發裏。
祁言懵了。
這是老婆?
是那個總被“欺負”得臉紅害隻能掐、揪頭發的喬喬?
祁言本來掐了念頭,曉得在這裏確實不合適,可是喬喬這麽一|撥,那念頭又冒了出來。眨眨眼,挑眉:“真的嗎,陸總?”
“”
一喊這個稱呼,陸知喬就渾不自在,仿佛自己私底下這副模樣立刻被同事下屬看了去,要的命。
“不許這麽喊。”
“就喊。陸總陸總陸總——”
陸知喬瞪。
祁言愈發來勁,著人下,笑道:“下班了,誰能想到陸總居然沒有回家,坐在公司門口的車裏被人摁著哎喲”
頭發被用力揪了一下。
連忙求饒:“老婆我錯了,別揪,我要禿頭了。”
“禿了算了你。”陸知喬又瞪,上著,手卻立刻鬆開,替了頭皮。
祁言慣會討乖,趁機在臉上啄一下,“那可不行,我答應你要把頭發養起來的。”
提到頭發,陸知喬眼神倏爾黯淡,手中力道愈輕,抿住,沒話,視線不經意落在祁言胳膊上,那裏有一道暗紅的抓痕,是昨晚留下的。
接著又想起許多。
言言寵,遷就,幾個月的時間就將從深淵裏拉出大半截,擁有世界上這麽好的言言,怎麽能不珍惜。
Advertisement
陸知喬笑了笑,抬手捧住祁言的臉,“以後不揪你頭發。”
話間,又被了個吻。
兩人回到家,兒坐在客廳看電視,邊看邊吃零食,悠然自在。
陸知喬心裏念著要自然,催眠似的,當真起了作用,放包,換鞋,倒水喝,自然而然,仿佛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
“妞崽,吃些零食,一會兒要吃飯了。”
“唔。”
姑娘立刻放下手裏的棉花糖。
陸知喬轉進了臥室,祁言一屁坐到兒邊,隨手抓了顆棉花糖剝開吃,“嗯,葡萄味的不錯。”
陸葳怔怔地看著,言又止。
“這主很漂亮啊,麵,誰演的來著?”祁言自然是到旁的目,沒搭理,自顧自看電視。
廚房裏的菜都切好洗好,飯也在電飯鍋裏煮著,等會兒炒個菜就行,趁現在幫著陸知喬穩一下“局勢”,盡快讓昨晚的事過去。
妮子肯定是想跟。
陸葳看也沒看電視機,就:“王。”
“哦,想起來了,演過那個《》吧?”
“嗯嗯。”
祁言又剝一顆棉花糖吃。
“媽”猶豫半晌,陸葳終是開口了,“我有件事跟你。”
“什麽?”
忐忑道:“我想養貓。”
祁言怔了怔,不知是意外還是鬆快,半晌才反應過來,笑:“為什麽突然想養貓了?”
“一直想養,但是媽媽不讓,因為沒時間照顧。”陸葳兩手著角,征詢的眼神著,滿含期待。
“我今去學姐家玩,看到養了一隻,很可!”
祁言手去掏棉花糖,發現沒了,又回手,看了眼臥室,思慮片刻道:“妞妞,你是喜歡貓才想養,還是看到學姐養了,你也想養啊?”
“喜歡。”
“真的?”
姑娘篤定地點點頭。
祁言又問:“那你能照顧好貓嗎?每給它喂食喂水鏟屎,還要提防注意別讓它生病,如果做不到怎麽辦?”
Advertisement
“沒有如果。”陸葳毫不猶豫地答,“我能做到。”
孩子心簡單,喜歡便是喜歡,沒那麽多彎彎繞繞,祁言心想兒不敢跟陸知喬,大概是沒信心能媽媽,於是從這裏下手。腦袋瓜子聰明得很,知道寵,好話。
祁言習慣抬手想臉,想起昨晚的話,頓了頓,轉而攬住肩膀,摟進懷裏,“那行,改我跟媽媽商量一下,功的概率大概是百分之七十。”
隻要陸知喬不是怕貓,或對過敏,這事兒就很好商量。
“嘿嘿~”陸葳雙眸發亮,笑著挽住胳膊,“媽最好了,我最你~”
航班落地東京,舒敏希從機場出來,上了一輛黑轎車,徑直往郊區去。
鄉間寧靜,路幹淨平穩,白牆黑瓦的斜頂屋分布得錯落有致,山川丘陵起伏,田野綠植茂盛,幽然僻靜。
景大致沒有變化,卻是人非。
多年前,舒敏希是個剛進公司的新人,沒什麽遠大誌向,隻想踏踏實實上班拿工資。那會兒公司初規模,最大的合作夥伴是青木家,在一次考察中,青木老頭帶上了自己的寶貝兒沙紀。
當時舒敏希剛過試用期不久,一連接了三筆大單,各方麵能力也不錯,老板顧殊寧頗為看重,於是手把手培養,帶在邊。
接待青木一家,全程陪同沙紀。
那會兒沙紀眼裏心裏都是顧殊寧,而什麽都不懂,最初隻以朋友的方式與沙紀相。後來顧殊寧明確拒絕了沙紀,久而久之,沙紀心裏也沒了念想。
沙紀在中國長居,修習,舒敏希與年齡相仿,常有來往,一來二去漸生愫。
舒敏希不認為自己是生彎,是被沙紀掰彎的,而這麽一彎,就再也回不去了。覺得和孩子談很好,像走一場夢,不願意醒來。
Advertisement
但終究是生活在現實中的人,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後來青木家鬥嚴重,老頭要沙紀嫁給門當戶對的另一世族,各類因素盤錯節,極其複雜。們分手了,沙紀回日本後很快結婚,生下一個兒。
沙紀是不甘心的,婚後日子過不安生,也發覺自己犧牲幸福並不能換來家庭的安寧,最後輾轉離婚,不再管家族的事,獨自帶著兒生活。
這些年,斷斷續續,兩人總有聯係。
誰也放不下。
舒敏希真正恨的不是沙紀,而是老頭,但考慮到公司的利益,明麵上不好撕破臉,是忍了許多年。心中戾氣不,見著沙紀,總忍不住冷言冷語。
昨,夢見了。
在明還要出差,未來半個月忙碌的況下,今放任自己飛了過來。
車子停在那棟屋前,院門口圍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的,舒敏希讓司機別靠太近,自己下了車,步行過去。
那群人是來討債的,各方都有,不知是什麽原因使得他們趕在今日聚集到一起,一個個兇神惡煞要吃人似的。
屋門前又生出不青苔,牆角顯出黴斑來,刷的白牆皮大塊大塊落。
沙紀被圍在人群中,懷裏護著年的兒,不斷向大家鞠躬道歉,皺著臉,角出苦笑,眼神迷茫又無助,像被狂風抖落的枯葉。
“這是在鬧事嗎?”舒敏希旁觀片刻,走上前。
人群安靜下來。
人的目掃過來,落在臉上,剎那間凝固了。
驚喜,諷刺,悲憫
抬眸,迎上那道目,心頭一刺,繼而淡然避開。
許是見著打扮不凡,鬧騰的人話聲音了些,但畢竟欠債還錢經地義,他們腰桿子直,理不虛。舒敏希一問數額,原以為會是一筆驚巨款,卻沒想到不過區區幾百萬日元。
昔日千金姐,淪落到這點錢都拿不出來。
舒敏希想幸災樂禍,但是笑不出來,看著沙紀無助窘迫的臉,隻覺出滿腔心酸。今來是想做個了斷,簡直連老爺都在給機會。
替沙紀把錢還了。
走進院子,矮樹上不知何時多了個鳥窩,枝丫間傳來嘰嘰喳喳聲,屋依然陳舊,幹淨,樸素卻溫馨,茶水還是像上次一樣,滾熱的,青黃相融。
舒敏希沒像上回那樣一口幹,而是口慢慢品,也不話。目落在門口,看著堆玩的孩,平的眉心攏起一褶皺。
“錢我會盡快還給你。”沙紀盯著的臉,生怕不高興遷怒兒,忙出醞釀許久的話。
而後又補了一句:“謝謝。”
以為上次不歡而散,就是永別,沒想到出人意料地來了,出現在自己麵前,毫無防備。
沙紀死灰般的心又燃起一點星火。
“靠贍養費還?”舒敏希挑眉。
沙紀低頭不語,臉頰因窘迫而泛紅。
“以前你幫過我,今我幫你,一筆勾銷,扯平了。”端起杯子抿了口茶。
有點,不如上回的香。
茶葉沒換,水也沒不同,大抵是人的心變了。
舒敏希放下杯子,看著,一字一句道:“如果你願意,就跟我回中國,如果你不願意,我們就再也不聯係。”
聽到前半句,沙紀心生歡喜,卻有顧慮,下意識了眼兒,可聽到後半句,心上燃起的火星子熄滅了——這是在拿的肋,做選擇。
“可以帶上你兒。”舒敏希補充道。
沙紀一怔,抬起頭,還未來得及綻開的笑容僵住了,看到舒敏希眼中的同,憐憫,甚至是施舍,心裏像是有什麽東西崩塌掉,落了一地。
“那就不再聯係吧。”思忖半晌。
從沒妄想過敏希能接兒,自己的孩子自己養,過去犯的錯自己承擔代價,雖然家族衰敗,輝煌不再,但放不下滿傲骨,絕不願去過寄人籬下靠人施舍的生活。
中國有句話:下無不散之筵席。
孤獨才是人生的常態。
舒敏希靜然著,臉平靜,輕輕吐出一個字:“好。”
立秋過後,連續落了幾場雷陣雨,氣溫依然居高不下。
祁言把在非洲拍攝的照片全部洗出來,做影集,家裏收藏一份,給了池念一份,讓先過過眼癮,緩解孕晚期之苦。而後又挑細選了十幾張,拿去參加比賽和展覽。
近幾在給公司拍雜誌,空餘時間很閑,看到家中鞋櫃裏各式各樣的高跟鞋,想起要督促陸知喬鍛煉的事,遂做了一個健計劃。
猜你喜歡
-
完結36 章

愛你不為人知
他曾說會照顧她一生一世,不離不棄,卻又在婚後翻臉,冷漠以待。 她懷孕,他要打掉。 他說,娶你隻是因為你的家產,不離婚,也是因為你的家產,其實我早就受夠你了。 她被困大火,命懸一線,他卻轉身摟著情婦腰肢,眼睜睜看著她葬身火腹……
4.4萬字8.09 20751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2946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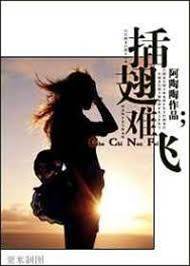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68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