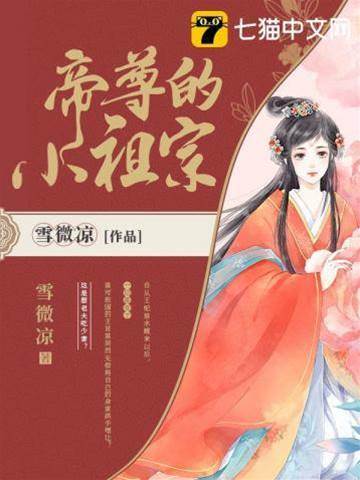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一脈香》 第一百章
近來,整個燕城風頭最盛的莫過於是巫崔錦。
不過短短一月,如今燕城無人不知崔錦的名字,而最為百姓津津樂道的卻不是有窺測天意之能,畢竟能窺測天意的在這燕城中已有了一個巫子,再添一個巫也不出奇了。而出奇的是這一位巫除了上朝旁聽政事之外,其餘時間便像是一個男子一般行走在燕城。
並非說穿著像是男子,而是的作為。
明明是個子,可是私下裏卻與多位朝中大臣好,騎馬箭,飲酒作樂,甚至偶爾尋來歌姬玩樂,也能面不改地周旋。
與巫子穿白不一樣的是,這個外來的巫日穿著紅的袍,上飾極,甚至有時候連一件飾也尋不到,的髮髻也是一不變的,一直都是將烏髮束以玉冠,出飽滿的額頭,整個人顯得英姿颯爽。
漸漸的,漸漸的,燕城的百姓們已經習慣了那一道紅影。
今日乃休沐日。
崔錦正好得閑,也不打算出門際,索留在了屋宅里。夏日已到,正好,崔錦喚了幾個下人將書房裏的書籍古卷都搬了出來,正好曬一曬,免得生蟲。
月蘭在灶房裏想著法子做好吃的。
只覺大姑娘每一日都在奔波,如今難得有一日空閑,怎麼著也該好好地犒勞下自己,遂準備拿出看家本事,烹一桌香味俱全的佳肴。
崔錦坐在藤椅上,悠哉游哉地曬著太,聞著棗花的清香,心裏頭是說不出的愜意。
阿宇過來的時候,正好就見到了這樣的場景。
人紅,綠樹蔭,坐臥在躺椅上,就像是一幅仕圖。
阿宇拍了拍自己的腦袋,回過神,走了前去。
「大姑娘萬福。」
崔錦懶懶地瞥他一眼,問道:「那邊有靜了?」
Advertisement
「回大姑娘的話,汾崔氏的四房這幾日都沒有過來。據小人所查,大房那邊開始有靜了。」
崔錦低笑道:「他們倒也耐得住。」
阿宇問:「大姑娘當真要回本家?」
崔錦說道:「先談一談再說吧。」
那一日被謝五郎擄走後,想通了一件事。與其另起勢力,不如借勢養勢,始終是姓崔的,何況曉得阿爹一直想著回歸本家。曾聽阿娘說過,阿爹有一回酒醉吐真言,說百年歸壽后定要將牌位放在離汾崔氏祖祠最近的地方。雖然阿爹醒后什麼都不記得了,但至此阿娘便知即使阿爹一提汾崔氏便翻臉,但他心底始終是念著本家的。
阿宇應了聲。
次日,果真有汾崔氏的拜帖上門。
而這一回不是四房的,而是大房的,也非長輩份相邀,而是以朝中同僚的份。崔錦沒有矜持,很快便讓人回了送帖子的人,說是會按時赴約。
.
崔府的總管郭宗文侯在府外。
馬車漸漸停下。
月蘭掀起了車簾,馬車裏頭的崔錦了郭宗文一眼,僅是淡淡的一眼,郭宗文便察覺出了這一位與尋常子的不一樣。
他不知該如何形容。
他見過許多人,府里的每一位姑娘他都知道,包括汾崔氏的嫡,曾被皇后讚譽蘭心蕙質的崔家大姑娘崔悅也不曾有這樣的氣度。
不是高高在上的眼神,而是經歷過戰場洗的眼神,不僅僅有堅毅沉穩,而且還有不他無法形容的神態。只是一眼,他便覺到了力。
他的腰微微彎了些。
「在下郭宗文,拜見巫大人。」
「不必多禮了。」
郭宗文應聲而起,吩咐隨從開門。崔錦了眼,開的是府中的正門,迎接貴客方會開的正門。崔錦看出了大房的誠意,給了月蘭一個眼。
Advertisement
月蘭立即鬆開了手。
車簾垂下,郭宗文側退步。
馬車緩緩地駛進了崔府。
崔錦下了馬車,郭宗文在前方帶路。路上有侍婢小廝經過,但皆目不斜視,頗有大家氣度。崔錦收回打量的目,此時郭宗文道:「巫大人,前方便是。」
淡淡地「嗯」了聲。
正廳里崔池已經在等候,與崔池同在的還有崔深。汾崔氏如今管家的乃大房,崔池便是汾崔氏的嫡長子,崔錦的父親若在此還得喚他一聲長兄,而崔深正是汾崔氏的嫡長孫。
崔錦落座。
經過一個月在場上的打滾爬,與一眾大臣的周旋,此刻的崔錦老練得多。微微一笑,與崔池聊起家常。
崔池在朝堂上是見識過這位侄的能耐的,是以也不敢掉以輕心。
崔池笑道:「先前你大兄到燕時,我也曾派人去接過你大兄,只可惜差錯之下錯過了,後來你大兄得聖上榮寵,忙得腳不沾地,你祖父又病逝了,因此也沒來得及與湛侄兒說話。喪期一過,湛侄兒也下放秦州了。我心中一直有憾,你祖父在時便想著接你一家回燕。年時容易衝,你祖父也很是掛念你們一家,多次想要接你們回來的,可惜……」
他嘆了聲。
崔深附和道:「祖父在世時,經常將妹妹一家掛念在邊的。」
崔錦說:「當真是造化弄人,我父親也是時常將祖父掛在邊的。」心中卻是不以為然,汾崔氏若真有那份心思,什麼時候能不找人來接他們回去。不過既然是要為一家人,這一點崔錦也不打算計較。在心目中,世家裏親淡薄,只重利益,談字又有幾分是真?在上有利可圖,便真上幾分。而也想要汾崔氏的支持,雙方是各取所需罷了。
Advertisement
崔池道:「我也很久沒見過九弟了,如今阿錦來了燕,我再修書一封送到秦州,改日等你大兄上燕述職時,正好可以一家團聚。」
崔錦道:「侄聽阿叔的。」
崔池須笑道:「好。」
.
半個時辰后,崔錦離開了崔府。
阿宇一直在外頭候著,見著馬車出來了,連忙迎上。他隔著車簾,低聲道:「大姑娘,可需收拾東西了?」
崔錦說道:「都先擱著,搬去崔府的事,不急。」
在崔錦的預料之中,此回應當如同在那回,與崔全談了易后,短短數日崔全便應承了的要求。只是換了崔池,卻出乎意料了。
真不愧是本家的老狐貍,面做足了,話裏頭滴水不的,只應承了他們一家回歸本家,剩餘的,每每想要開始談條件,老狐貍便不聲地錯開,偏偏還尋不著理由繞回來。
老狐貍的態度很是明顯,回了本家便是崔家的人,崔家的子弟為自家人奉獻是理所應當的。
崔錦又道:「罷了,先回去再說。」
阿宇應了聲。
月蘭是跟著崔錦一塊到崔府的,最懂得察言觀。如今見到崔錦這般模樣,便知心底不痛快,仔細揣了下,小聲地問:「西街新開了一家食肆,大姑娘可要去嘗嘗?」
崔錦忽然想起前幾年在秦州的時候,自己也是開過食肆的。
那會得閑得很,手頭閑錢也多,謝五郎寵著,三百六十五行說也試了數十行。崔錦心想,興許可以將秦州的產業搬到燕來。
思及此,崔錦也不再想崔府的事,高興地道:「去瞧瞧。」
只不過崔錦也就高興了一小會,不到片刻,的馬車被人攔截了下來。馭夫驀然停車,崔錦險些磕到了腦袋。扶了扶額頭,皺眉喝道:「發生什麼事了?」
Advertisement
回答的是阿宇。
只聽阿宇隔著簾子輕聲說道:「大姑娘,是……是謝家五郎的馬車。」
崔錦微微一怔。
此時,外頭忽有驚呼聲響起,隨即是一片嘩然聲。
「啊,是巫子。」
「巫子大人!」
「此生竟能親眼見得巫子大人一面,此生無憾了!」
……
外頭是源源不斷的讚之聲。
阿宇說道:「大姑娘,謝家五郎過來了。」
崔錦又是一怔,不知謝五郎到底在玩什麼把戲。索掀開了車簾,這一掀登時驚了驚。謝五郎逐步向走來,他走得極慢,而周圍不知何時圍滿了人群,將西街得水泄不通。
崔錦與謝五郎相過幾年,是極其明白謝五郎的喜好。
他喜潔,從不在大街上行走。
那幾年與謝五郎在一起,就從未見過他踩在街道上,往往都是坐在馬車裏的。如今見他一步一步地向走來,驚訝的同時,還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緒。
他準確地在的馬車前停下。
周圍喧嘩的人群也在此刻停止了聲音,整個西街登時安靜得連跟針掉下來的聲音都能聽見。
「我在煙華樓為你設了一桌宴席,不知巫可願賞臉?」
在場所有人的目齊刷刷地落在崔錦的上。
巫子專程設宴,只為巫一人。
以往能得巫子親自招待的,五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何況還由巫子親自前來宴請!
不人的目里添了幾分羨慕。
崔錦心裏頭想的可其他人不一樣,此時此刻心底正咬牙切齒得很。謝五郎虛晃一招,周圍的人又記得水泄不通,倘若他擄,還有反抗的餘地。如今堂而皇之地站在的面前,若不答應,未免顯得小氣了。何況謝五郎用的還是巫二字,與朝中同僚可以把酒言歡,巫子亦是同僚。
此刻的本沒有不去的這個選項。
謝五郎出了淡淡的笑意。
「阿錦,宴席上都是你所喜歡的吃食。」
稱呼一換,登時有不人又驚呼了一聲。原以為巫與巫子之間的事不過是傳聞,或是由他人添油加醋所,可如今巫子那麼親地喚巫,還說出如此引人遐想的話語……
兩人之間究竟是何等關係,便十分值得推敲了。
崔錦沒想到謝五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再看周圍百姓好奇的目,曉得是必去不可了。佯作落落大方的模樣,說道:「還請巫子大人帶路。」。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