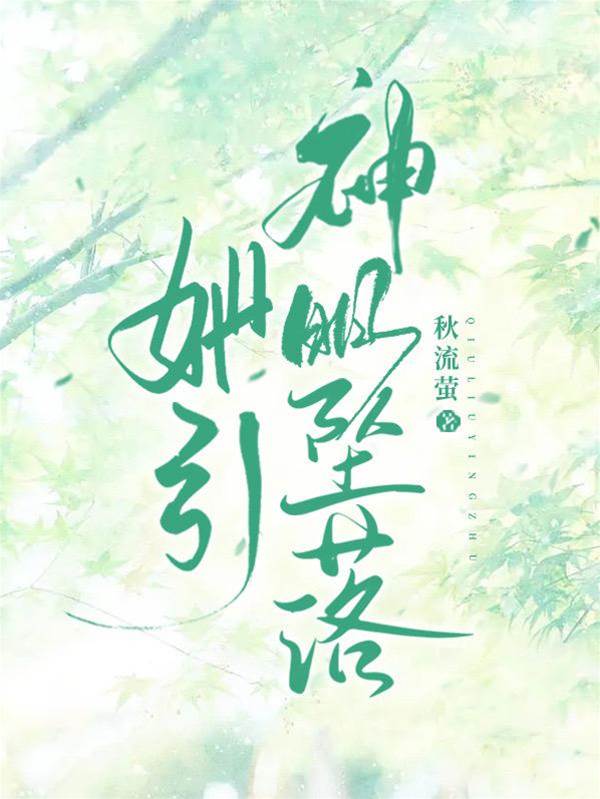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傅夫人是娛樂圈頂流》 第644章 阮阮,怎麼可以逃呢?
深夜,迷霧埋埋。
江阮阮逃了。
半山腰,卻誤野陷阱,大雪覆蓋的泥坑,突然跌落下去,雪化水,很快就滲大,上的溫度驟降。
沒過頭頂的高度,約還有月斜照的微弱亮。
上作疼,是跌落下來,不甚劃到樹枝造的。
想要尋找出口,可哪里有出口啊!
耳邊滿是狼嚎聲,越來越近……
上面是簌簌的風聲,還有……似乎是狼群靠近的聲音。
綠油油的眼睛突然從上面冒出,江阮阮睜大了雙眼……
可是危險沒有靠近,隨之后面聽到的是一陣槍聲。
捂了耳朵,比起狼群,更可怕的是……江安!
他找到自己了。
他說,阮阮,怎麼可以逃呢?
他說,阮阮,別想離開哥哥。
他說,阮阮,該怎麼懲罰你好呢?
他還說,阮阮,乖乖的,你依然我寵著的小公主的。
Advertisement
后來,暈倒了。
不知道是上的傷痛暈的還是見到他嚇到的……
……
熠熠生輝的別墅,隔間卻是設施完備的私家醫室。
是被痛醒的,猛然睜開眼,只看到幾個穿著白大褂神繃的醫生。
而被綁了起來,雙手、雙腳、腰部、頭部都被固定在床上,就連都被膠帶封住,好像案板上的魚,任由生死。
覺到手腕的筋被挑起,似乎又有異.塞了進去,疼痛異常,幾麻木。
陸一帆見醒來,眉頭一皺卻是一語不發,手下的作更是快了起來。
“啊……唔……”江阮阮雙目猩紅,發出的聲音也被膠帶封住。
死死的盯著陸一帆,在心中,如果說江安是十惡不赦的殺人魔,那陸一帆就是罔顧人命的劊子手。
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但反正對來說不會是好事就是了。
Advertisement
手腕已經完全失去知覺,才聽到陸一帆的話,“大家辛苦了,手功。”
再一次睜開眼,江安站在那擋住了頭頂的手燈,整張臉都陷了黑暗中,他給的覺,漆黑一片。
那冰涼的手朝來,搖著頭,淚水早已模糊掉視線,江安揭掉了口中的膠帶。
手解開了那固定住全的束縛,從手到腳。
手腕被綁著一層白的紗布,上被玫瑰刺傷的也都被上了創可,有更嚴重的也綁上了紗布,可唯獨手腕最為明顯。
手腕裝了東西,裝了什麼,不知道。
“阮阮,怎麼可以這麼不乖?”
他們明明隔得很近,可看不清他眼底的神,就像是即將墮地獄的人,只覺得很黑很暗,沒有明。
江阮阮從不明白,什麼時候起,江安變了……
也許,就連江安自己都不明白!
這份,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變的……
在看到有男孩子靠近的那一刻,潛藏在心底的所有抑緒,就再也忍不住,全都迸發出來了……
他不希看到任何一個男孩靠近!
他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
猜你喜歡
-
完結3328 章

先婚後愛:BOSS輕點寵
她以為離婚成功,收拾包袱瀟灑拜拜,誰知轉眼他就來敲門。第一次,他一臉淡定:“老婆,寶寶餓了!”第二次,他死皮賴臉:“老婆,我也餓了!”第三次,他直接撲倒:“老婆,好冷,來動一動!”前夫的奪情索愛,她無力反抗,步步驚情。“我們已經離婚了!”她終於忍無可忍。他決然的把小包子塞過來:“喏,一個不夠,再添兩個拖油瓶!”
591.3萬字8.46 320187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2997 -
連載1815 章

枕上歡:老公請輕點
唐慕橙在結婚前夜迎來了破產、劈腿的大“驚喜”。正走投無路時,男人從天而降,她成了他的契約妻。唐慕橙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無聊遊戲,卻冇想到,婚後男人每天變著花樣的攻占著她的心,讓她沉淪在他的溫柔中無法自拔……
318.3萬字8 35119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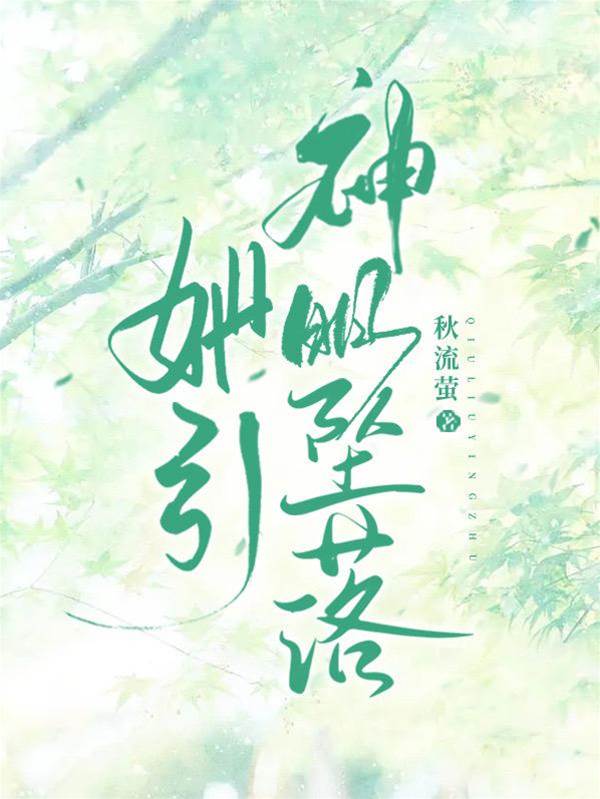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177 -
完結191 章

你有男閨蜜,就不要纏著我了
結婚前夕。女友:“我閨蜜結婚時住的酒店多高檔,吃的婚宴多貴,你再看看你,因為七八萬跟我討價還價,你還是個男人嗎?!”“雖然是你出的錢,但婚房是我們倆的,我爸媽可
33.3萬字8.18 26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