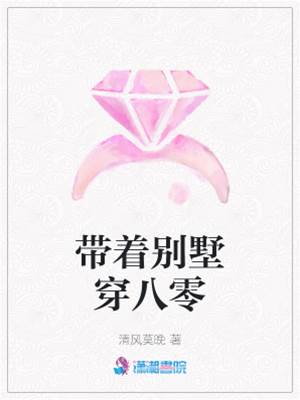《八零暴富小辣椒》 第39章 保證書的作用
吳秀蓉一聽保證書,就說:「啥保證書?咋寫?」
「就讓他寫,今天幹了什麼壞事,保證以後不敢再犯!大姐,你也得讓他給你寫一份!」許然之後看向孫志學說:「要不我就報警!」
孫志學一聽報警,趕說:「別報警!要是報了警我可就完了!」他現在好歹還是個生產隊長,要是惹上司了,這職位就得給他擼了。
吳秀蓉仔細的考慮了一下,這孫志學早晚都得出事,而且今天的事還被人抓包,也不想把事鬧大跟著一塊丟人,就說:「寫,我也得要一份!」
孫志學納悶,就問:「你要啥保證書!」還嫌不夠嗎?
「保證你以後要是再犯,就離婚,到時候孩子家產都歸我,你凈出戶!」吳秀蓉說道,許然還真是給了靈,趁著現在就趕讓孫志學保證!
孫志學當然不同意,這不是挖坑讓他跳呢嗎!
Advertisement
看孫志學不點頭,吳秀蓉就說:「你怕啥?你要不敢寫,你就是還敢犯,也不用人家報警,我自己去報警,反正早晚也是丟臉,今天大家就一塊丟!大不了現在就離婚,我不和你過了!」要不是為了孩子,真想踹死孫志學,如今也算是看了孫志學,這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也不能再一味的忍讓了!
許然看吳秀蓉這麼來勁,就讓昊去拿紙筆,今天一定要著孫志學的把柄,不然今天昊把人打了,以孫志學的尿絕對是要記仇的,有這麼一張保證書在手,孫志學想要使壞的時候也得掂量掂量了!
孫志學也是沒想到自己能在這裏翻了船,屢試不爽的事怎麼這次就能失手了呢?
昊把筆紙放在孫志學眼前,孫志學要是不寫,今天別想走出這個門去!
吳秀蓉讓孫志學趕寫,孫志學沒辦法,只能寫兩份保證書算是代。
Advertisement
許然看了看保證書,基本就是說一句孫志學寫一句,孫志學的簽名就在上頭,以後也抵賴不了。
吳秀蓉拉著許然先出去說話,許然捂著臉疼了。
「妹子,今天是你了委屈了,他那人這輩子怕是也改不了,可是這臉面上的事……」吳秀蓉也是覺得沒臉說,可是許然說道:「放心吧吳大姐,今天的事我們都不會往外說的。」村裏人最嚼舌子,還有一個和作對的周金花在,也不想惹麻煩。
吳秀蓉握著許然的手,拍了兩下,一言難盡的說:「姐謝謝你了!」然後就拉起孫志學,先回家去。
正月十五,鬧出這樣的事來也實在讓人高興不起來。
許然整了整頭髮,就讓外面的月秋進來。
「煮湯圓,今天甩開腮幫子可勁吃!」許然說道,不能拿別人的無恥來懲罰自己。
Advertisement
昊讓月先去看著灶,他則去外面抓了一把雪進來給許然冷敷一下,這臉已經腫起來了,得養兩天了。
「我該早點回來的。」他總是不能保護好許然,今天也是忙才能先回來,他真的無法想像要是自己真的回來晚了,許然會到怎樣的傷害。。
猜你喜歡
-
連載3059 章

億萬軍婚:首長,寵上癮
一場精心陰謀,18歲的安寧失去清白,聲名狼藉。四年後,竟被某小萌寶狠狠糾纏,讓她嫁給他首長老爸。傳聞京城權貴鬱景宸潔身自好、不近女色,偏偏四歲的兒子吵著要媽咪。某日,領著安寧走到老爸跟前。“老爸,這個..
264.7萬字8 18623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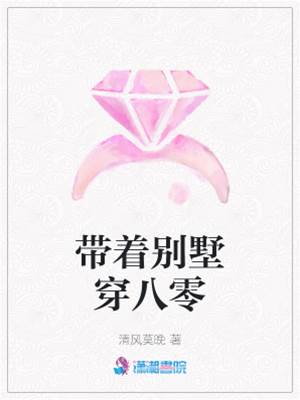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93 章

遲秘書偷偷懷崽,盛總攬腰寵上天
【元氣可愛女秘書x戀愛腦霸道總裁x萌寶】盛焰清,盛世集團新任總裁,28年不近女色,卻因一聲“哥哥”,不明不白的丟了身子。自此食髓知味,每晚都要回憶著小女人的聲音……自我滿足直到某日醉酒後,遲秘書化身撩人精,纏著他叫“哥哥”,盛焰清才如夢初醒,徹底變身戀愛腦。反撩的遲軟梨情不能自已,待她反應過來時,孕肚早已顯懷,逃無可逃……ps:雙潔,互撩,帶崽日常向甜寵文
14.9萬字8.18 172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