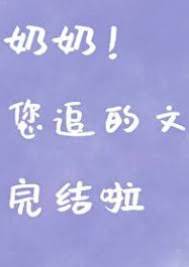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蝴蝶軼事》 第 90 章 Butterfly
Butterfly:90.
仙棒的花火,像是燃燒在指尖的星屑。
岑芙喜歡這種短暫而麗的東西,像個小孩似的盯著手里的仙棒目不轉睛。
夜里有風會冷,把整個人連帶脖子和臉蛋都到羽絨服和圍巾里,鼻尖紅紅的。
就出一只手著仙棒傻傻的盯著看。
看了一會兒,仙棒燃盡,抬臉,瞧著邊的許硯談,憨一笑:“再來一個。”
“傻勁兒的。”許硯談勾,兜里掏出打火機給又點了倆,一手一個。
“去年過年的時候在哪兒呢。”許硯談拉過一把木椅子,在邊坐下陪著,大爺似的懶洋洋。
岑芙揮揮仙棒,仰頭回憶:“嗯…”
“好像在組里,應該是。”
“拍完當天的容大家一塊點了餃子外賣,人多的,還蠻熱鬧。”岑芙想起那天的景。
也不算寂寞。
許硯談長一,用鞋頭踢了踢的鞋,“更喜歡那樣過?”
“怎麼會。”岑芙轉,順勢側著,坐在他一條上,讓他手摟住自己后背,站累了。
“再熱鬧也是湊在一起工作,哪有跟你在家里這麼高興呀。”
許硯談挑眉,品味了幾秒,自我攻略:“主要是有我陪著。”
岑芙撲哧笑了好幾聲,把燃盡的仙棒扔在地上,雙手摟他脖子,冷天兒里把從圍巾里挪出來親了親他的臉。
“對——沒你哪兒行。”
岑芙上的香味隨湊近在許硯談面前短暫的縈繞了一陣,明顯敷衍的哄人技巧,在他這也算勉強過關。
許硯談拍拍后背,“起來了,回去吃餃子。”
兩人牽著手回去,岑芙問他:“我們今天回家嗎?”
Advertisement
“不回去了,陪他住一晚。”許硯談說著:“我那屋收拾一下能睡。”
岑芙聽他的,點頭。
*
吃過晚飯以后就臨近十二點了,姑姑一家決定率先離開,明天上午再來。
許硯談和岑芙留下,不嘆他的預判力,如果他們也走的話,大年夜又剩叔叔一個人在這房子里過夜了。
也不能這麼說,畢竟谷小姐也還在。
岑芙還在回坐在一樓客廳的那兩人時,自己已經被許硯談拉著上了樓梯。
“我那臥室上了大學以后就沒怎麼回來住過,也不臟,偶爾有人打掃,我先收拾,你在屋里玩會兒。”
許硯談囑咐著。
許硯談的房間在二樓最里面,六年前去過一次,被姑姑著給許向臻拿詞典。
就是在那里,岑芙第一次窺見了許硯談不為人知的一面。
在他散漫不羈的表面,藏著曾經撕扯瘋狂的病態。
正如長輩們所說,爺爺和叔叔只是把他從生父那邊帶了出來。
真正拯救他的“惡”的,是許硯談自己。
他一邊縱容著自己在無人知曉時發瘋,又同時與瀕臨變態的自己對抗。
那兩排整齊的書架就是最佳的證據。
岑芙走進這間并不算寬敞的臥室,和上次進來一樣,陳設和家都非常簡約,歐式風格的木質充斥著這間屋子。
許硯談過去扯下落了灰的床單和被罩,任隨便轉著看。
見他出了臥室,岑芙探頭瞄了一眼,然后轉走向那兩排書架,把自己藏在書架中間。
出手指在書架上了一把,指腹上全是灰塵。
這些書真的很久沒有被人過了。
岑芙一直以為他會找個時間把這些“證據”扔掉,換嶄新完整的書籍。
Advertisement
但并沒有。
從其中隨便挑出一本,有關心理健康自我疏導的,翻開,果然,每一頁還是被小刀劃得破破爛爛。
書頁劃得快爛花了,岑芙深深記得,第一次看見他這兩排爛書整整齊齊被擺在這里,聳高的迫弱小靈魂的。
當時是多麼震撼,多麼恐懼。
當見到許硯談的時候,反倒不會那麼害怕。
唯獨見不到他人,卻看見他的這些杰作時,那扎進骨子里的恐怖才真切。
岑芙平靜著目,白皙的指腹細細著書頁里被劃爛的地方。
而再次面對這些,已經不會再害怕。
如果非要說什麼緒,那就是心疼,和敬畏。
許硯談不理這些,說明他就是打算讓這些書永遠擺在這里。
他永遠是面對面審視自己的所有不堪和脆弱。
“干什麼呢。”他的聲音忽然出現在側。
岑芙抬頭,看見靠在書架旁邊的許硯談,他的視線定在自己手里的書上。
聳肩,掂了掂手里的書,跟他控訴:“無聊,想找本書看,你瞧瞧這,我怎麼看。”
許硯談扯了扯線,似乎是沒想到會這麼聊。
他站直子,往前走兩步,接過手里的書,掃了一眼書上這些都看不清字的劃痕。
沒等他說話,面前人靠了過來。
許硯談單手拿著書,敞開懷抱,看著岑芙出手圈住他脖頸,讓他俯下來。
他低頭,與額頭相抵,兩人的眼睛近在咫尺,呼吸熱。
岑芙就這樣認真地注視著他深邃的棕丹眼眸,扇的眼睫像蝴蝶緩慢的展翅。
許硯談垂眸,慢慢看向的,又抬起視線,問:“怎麼了。”
“我在看。”岑芙稍稍偏頭,視線不曾從他的瞳孔挪開,小聲呢喃:“試試看能不能從你的眼睛里,看到許硯談小時候的樣子。”
Advertisement
“突然想知道你小時候是什麼樣的。”
許硯談另一手繞后扶在的腰上,大手一握就幾乎圈住多半的腰。
他短暫壞笑,氣音曖昧:“還是別見了,我小時候可不招人待見,欠揍。”
“你要是見過那時候的我,估計也對我沒意思了。”
岑芙挑起眼尾,往前一寸,用自己的鼻頭頂了頂他的鼻尖,垂下了眼:“怎麼會…”
你明知道,不管你是什麼樣子,我都會喜歡。
“我只知道,是你這個壞家伙,給了我這麼多朋友,這麼多家人。”
說到一半,有些遲疑,半帶赧意,聲音都小了:“以后,還會跟我一起…有個新家。”
許硯談把書隨意地塞在書架上,在腰后的手用力,把人擁進懷里。
兩人擁抱在一起,互相傳遞著溫。
的額頭在他脖頸,著他跳的脈搏。
許硯談彎腰,低頭找過來。
知道,他早就想親了。
岑芙的后背上略有灰塵的書架,仰起頭來承接他的吻。
許硯談的強勢依舊,習慣的攥著的手腕放在頭頂,不給人掙的機會。
今天的吻尤為的熱,可能是因為他臥室的地暖給得太足,也可能是因為除夕夜這樣的節日太過溫暖。
岑芙用的存在,讓這間曾經布無盡黑暗,無盡痛苦的臥室此刻被無盡溫填滿。
他的薄落在耳后最細膩的,親吻著的那塊蝴蝶胎記。
兩人都已。
岑芙呼吸不太穩,笑著與他耳輕言:“小許硯談的臥室…也會有那種東西麼。”提醒他。
許硯談從未停下步調,他使勁在耳后落下一記,發出聲音。
然后告訴:“小許硯談的臥室里沒有。“大許硯談從和岑芙的家里帶了。
Advertisement
岑芙抱著他咯咯地笑,說不出是喜悅還是害。
清靈的嗓音笑起來特別好聽,還糅雜著時的綿沙。
捧著他的臉頰,皺了下鼻子,墜許硯談沸騰深海般的眸底,哼一聲:“你早就想跟我在這兒做,壞蛋。
“知道就行。 許硯談攔腰把人抱起來,沒著急走,湊在耳畔說:“老房子隔音不好。
“你小點聲兒。
他故意提醒:“白天的哥哥,我可沒忘呢。
“今晚不許我別的,就這個。
岑芙實在聽不下去了,抬手在他肩膀打了一下,晃想掙扎。
“許硯談,你壞死了,渾蛋一個。
他跪在邊,帶著的手,放在自己服的紐扣上。
許硯談用惡劣包裝深,嗓音如沙。
漫天的大漠孤沙捧著的是那一彎清月。
“芙芙,我對你不向來是。
他哂笑。
“無惡不作麼。
岑芙。
我對你向來無惡不作。!
猜你喜歡
-
完結193 章

我的霸道兵哥
她是他的藥,蘇爽甜寵撩。 大佬一:【八零兵哥】妹妹不想嫁那個當兵的,家裡人讓姐姐替嫁。(已撩完√) 大佬二:【禁欲影帝】驚!禁欲系影帝顛覆人設,豪宅藏嬌十八線……呃十八線都不是的龍套小女星!(正在撩) 大佬三:【霸總他叔】霸道總裁看上灰姑娘,想和門當戶對的未婚妻退婚,未婚妻轉頭勾搭上霸總他叔——大霸總! 大佬四:待續……
47.4萬字8 23907 -
完結308 章

盛宴之后
帥氣的老公跟大方和善的姐姐茍合在了一起。 她被打的遍體鱗傷,不但孩子不保,最后還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她跪在那個她叫著姐姐的女人面前,求她放過她媽媽。 女人卻一陣冷笑,咬牙切齒的看著她:“譚小雅,這輩子,你已經輸了,你沒有資格跟我談條件……你這個賤種,跟著你媽一起下地獄吧。” 譚小雅瘋了一般的想要跟她拼了,最后卻慘死在自己老公的手下。 本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麼敗了,可冥冥之中,竟又重生歸來。 他們給了她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殘,歡享一場饕餮盛宴。 且看盛宴之后,她如何逆天改命,將前世負了她的,一一討回來! 她要讓所有給過她屈辱的人,全部跪倒在她的膝前,卑微乞求她的原諒。
56.9萬字8 24439 -
完結872 章
她比糖更甜
豪門顧家抱錯的女兒找到了,所有人都在等著看這個從窮鄉僻壤來的真千金的笑話。熟料一眾骨灰級大佬紛紛冒頭——頂級財閥繼承人發帖,“求教,如何讓樂不思蜀的老大停止休假?例:顧瓷。言之奏效者獎金一億!”國際黑客組織瘋狂在各地電腦上刷屏,【致顧瓷:萬水千山總是情,回來管事行不行?】著名研究所聯名發表文章——《論顧瓷長時間休假對全人類發展與進步的重大危害》京都權勢滔天的太子爺怒起掀桌,“都給爺爬,顧瓷我的!”
138.8萬字8 155689 -
完結106 章

投其所好
身為翻譯官,周宴京見過無數美景,都不及祖國的大好河山,與丹枝穿旗袍時的婀娜多姿。.首席翻譯官周宴京剛上任,就因眉宇清俊、言辭犀利給眾人留下深刻印象。有網友打開百科資料,發現家庭一欄寫著——“已訂婚。”…
38.6萬字8 9797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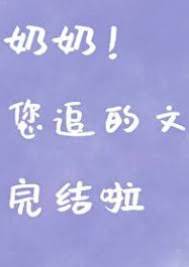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