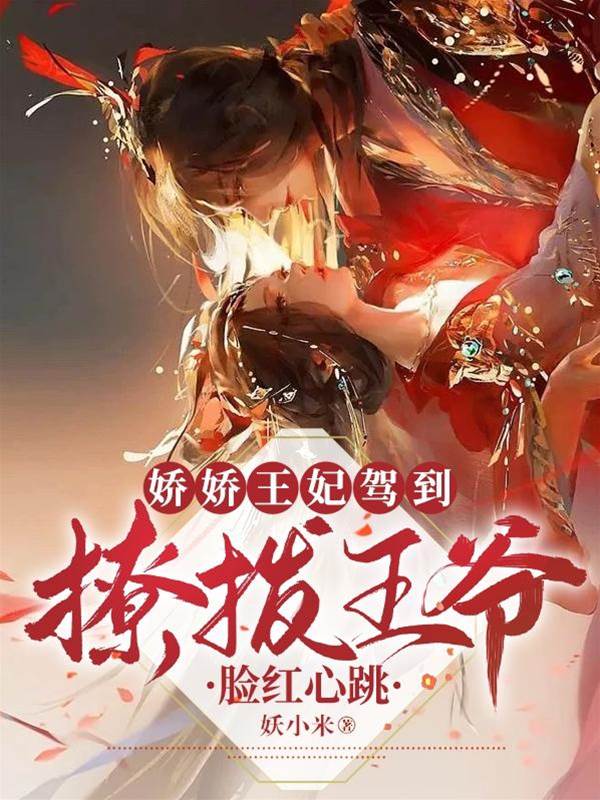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將軍別吃,夫人下毒了》 第六十三章 義莊
林婉城道:“你不要沖,這件事驚了圣上,如果沒有確切的證據,只怕很不好辦。而且,這件事我大概有了一些眉目。”
崔叔明向來知道懷里的這個人兒十分聰慧,不由道:“什麼眉目?”
林婉城從懷里掙出來,看著他,認真道:“你先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種酒是聞不出酒味的?”
崔叔明皺眉一想,慢慢點頭:“有。有一種專門供子喝的酒,淡而無味,名字好像辛水。”
林婉城冷冷一笑:“那就是了。我終于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了!”
林婉城將自己的想法統統告訴了崔叔明,崔叔明朝牢房外了一聲,余慶立時便挎著劍走上來,崔叔明附在他耳邊低低代幾句,余慶一拱手,就快步退了出去。
余慶走了之后,林婉城本來讓崔叔明也一塊回去的。可是崔叔明賴在牢房里不肯走。林婉城不由急道:“這里是監,你一個大男人賴在這算怎麼回事?”
崔叔明抖手將上的鎧甲解下來,舒舒服服在炕上一躺,意有所指道:“這是單間。更何況我只在這里陪著你,又不做什麼,你怕什麼?”
林婉城臉臊得通紅,手就朝崔叔明上錘過去:“你怎麼這麼流氓?”
崔叔明趁勢抓住的手,輕輕往懷里一帶,就讓躺在自己懷里。林婉城皺著眉反抗:“你快放開,你快放開我!”
崔叔明將抱在懷里,用將制住,無賴道:“不放。”
林婉城氣的無語,只得由著他耍一會賴。半晌,林婉城才又開口:“好了,這炕你也躺夠了,趕快回府吧。若是讓史知道你如此荒唐,賴在監牢里不肯走,仔細他們在金鑾殿上告你一狀!”
Advertisement
崔叔明裝睡不理。林婉城用胳膊肘往后輕輕一撞:“你聽到沒有?”
崔叔明就淡淡道:“有那個膽子他們就只管去告吧!”說完就閉上眼不肯再說話。
過了一會,林婉城又疑道:“咦——真是奇怪,上一次采薇和子瀾來探我,我們剛說了一會話,獄卒就來攆人,你進來這麼久了,怎麼不見們趕你出去?”
崔叔明猛地睜開眼,并不回答的話,反而反問道:“夏采薇、衛子瀾?你們平日有嗎?”
林婉城奇怪道:“我人緣好著呢,只是你不知道罷了。”不敢告訴崔叔明夏采薇探監的主要目的是道歉,害怕崔叔明這家伙一怒之下會遷怒采薇。
卻聽崔叔明低低一笑,“嗯嗯”兩聲算是回應人緣好。崔叔明想了一下,又道:“夏采薇是未來的齊王妃,衛子瀾麼……只怕也不簡單……”
林婉城知道他話里話外的意思。崔叔明手握重兵,儲位未定,三位王爺哪一個不想拉攏他?所以,他大概是懷疑夏采薇的機不純。可是林婉城有自己的判斷,是真心覺得夏采薇是個很不錯的孩子,因此便佯怒道:“你這人真是傲,人家與我好,跟你有什麼關系?當你是個香餑餑嗎?什麼人都愿意要?”
崔叔明趴在林婉城脖子上癡癡一笑,熱氣吹得林婉城脖子的:“對對對,我是個臭餑餑。只有我的婉婉想要我,我也只給我的婉婉吃。好不好?”
林婉城不由恨恨道:“誰想要你,去去去,別在我地盤上呆著。”
崔叔明哈哈一笑,輕輕在耳朵上一咬:“我想要你,沒有你,我天天想,吃不下睡不好,還不麼?”
林婉城上不說,心里卻高興起來。卻聽崔叔明接著道:“衛子瀾暫且不提。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夏采薇早晚都要嫁給齊王的。蔣家深恨你,你若跟夏采薇好,將來進了齊王府,豈不是讓難做?”
Advertisement
說實話,林婉城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崔叔明與一提,不由皺著眉頭陷深思。崔叔明卻一把將翻過來,與相對而臥,道:“行了,不許你想這些了,快睡覺。你要是再敢說話,我就親你!”
林婉城恨恨的一拳錘在他口,卻到底不敢開口說話,慢慢伏在崔叔明口,不多時便睡了。
深夜,順天府義莊。
夜深沉,連月亮也被烏云遮住了。幾個背著油桶的黑影悄悄來在在義莊外,他們手矯健,縱一躍,就跳進院墻里。
看守義莊的老張頭已經被迷香迷暈,幾個黑影躡手躡腳來在正廳。正廳里并排擺著十幾口黑黢黢的棺材,為首的那個黑人一抬手,低聲道:“分頭找!”
黑人答應一聲,四散開來。只聽見正廳里“嗡嗡”的聲音響起,黑人們將棺材一個一個打開,拿著昏黃的燭火往棺材里挨個照去。
忽然,一個黑人一舉手:“找到了!”黑人們就趕忙聚過去。為首的往棺材里低頭一看,就見蔣杰雙目閉,臉在這昏黃的燭火下黑黢黢的很是嚇人。
為首的一點頭:“手!”
其余幾人答應一聲,從背上解下油桶,在棺材四周“嘩啦啦”倒出來。
忽然,房梁上人影一晃,又縱跳下兩個黑人來。“刷”一下亮出手中的長劍。
正在倒油的匪徒一頓,都慢慢直起腰來,看著為首的不知如何是好。為首的一皺眉,走出來拱手道:“敢問是哪條道上的兄弟?”
那兩人的其中一個就冷笑道:“總之跟你們不是一道!”一邊說,寒閃,兩人提劍就沖了上去。
一時之間,大廳里刀劍影,打一片。后來的兩個人功夫不弱,但到底對方人多勢眾,剛剛五十多個回合,就略顯敗勢。
Advertisement
“圍起來,快!”忽聽院子里一聲暴喝,不知有多兵丁舉著長矛跑上前,將整個義莊圍的水泄不通。
先來的那個匪首暗道不妙,一腳將對面的一人踢開。手從懷里掏出一個火折,急急吹兩口氣,那火折子上火跳,轉眼就燒了起來。匪首冷冷一笑,一抖手就將火折子扔了出去。
大火將起,勢危急。在千鈞一發之際,門外有一個影沖進來,抬手一劍劈下來,將那火折子劈兩半,剛剛點起的火瞬間就歸于無盡黑暗。
那匪首見勢不妙,就走,來人卻一腳踹在他口,他連還手的余地都沒有,“撲通”一聲狠狠摔在一口黑漆棺材上。來人往后一擺手:“全都拿下!”
后答應一聲,立時便走上來十幾個全副武裝的將士,將打架的人團團圍上,一舉長矛,便將他們押了起來。
后從梁上跳下的其中一人抬眼一看,不由喜道:“余慶大哥!”
余慶皺著眉回頭,那人就把臉上的黑紗往下一拉,余慶不由喜道:“天?你怎麼在這?”
……
第二天一大早,余慶就急急去了順天府大牢,給崔叔明和林婉城送了換洗的和早飯,順帶將昨夜的事說出來。
崔叔明一擰眉:“天也在?”
余慶趕忙道:“是的。天是奉了平王的命令守在那里的。已經守了好些天,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打尸的主意。”
崔叔明慢慢點頭,手又遞上去一包東西:“王爺還說,要將這包東西給林小姐過目!”
林婉城看一眼崔叔明,見他沒有說什麼,就手將那包東西接過來,打開一看,驚道:“這是那天的藥渣?”
余慶趕忙道:“正是。當日蔣府的下人想要把藥渣丟掉,平王就派人暗中取了回來。”
Advertisement
林婉城仔細看了看那包藥渣,依舊沒有發現什麼異常。過了這麼多天,藥渣里的東西早就揮發干凈,到底該怎樣證明這包藥渣被過手腳呢?
林婉城正在深思,不經意間看到了余慶的手上一片鮮紅,不由奇怪道:“余慶,你的手怎麼回事?”
余慶抬起來一看,見怪不怪道:“哦,這沒什麼。大約是這牢房氣太重了吧。不知道怎麼回事,氣很重的地方我的上就會變這樣。”
林婉城腦子里靈一閃,不由笑了起來。崔叔明道:“怎麼?想起什麼了?”
林婉城沖燦爛一笑:“還要麻煩余慶幫我去查一件事……”
余慶領了命,剛剛要退出去,卻又忽然想到一件事。他從懷里掏出一封信,恭恭敬敬遞上去道:“林小姐,這封信是白大夫托人給我的。是從林州鎮國公府寄出來的。”
林婉城一喜:姨母的信!自杜裴氏隨鎮國公去了林州,山高路遠、通不便,林婉城就很與聯系。林婉城中毒之后,害怕杜裴氏擔心,更加沒有告訴,不曾想,這信卻寄到了保安堂,看來,杜裴氏知道了的遭遇。
林婉城展開信來讀,讀了兩行就熱淚盈眶。崔叔明趕忙走過來,溫的給去眼淚,心疼道:“怎麼了?怎麼又哭了?”
林婉城搖搖頭:“沒,沒什麼。”
杜裴氏在心里狠狠將責備了一頓。原來,林婉城離開定遠侯府不久,杜裴氏就派人送來了信。可是卻遲遲也等不來林婉城回信。心里焦灼不安,很快就派人進京打探。來人將林婉城的遭遇打探清楚,仔細跟回稟了,急怒攻心,當時就背過氣去。等悠悠轉醒,立時就派人去尋找們主仆的下落。
猜你喜歡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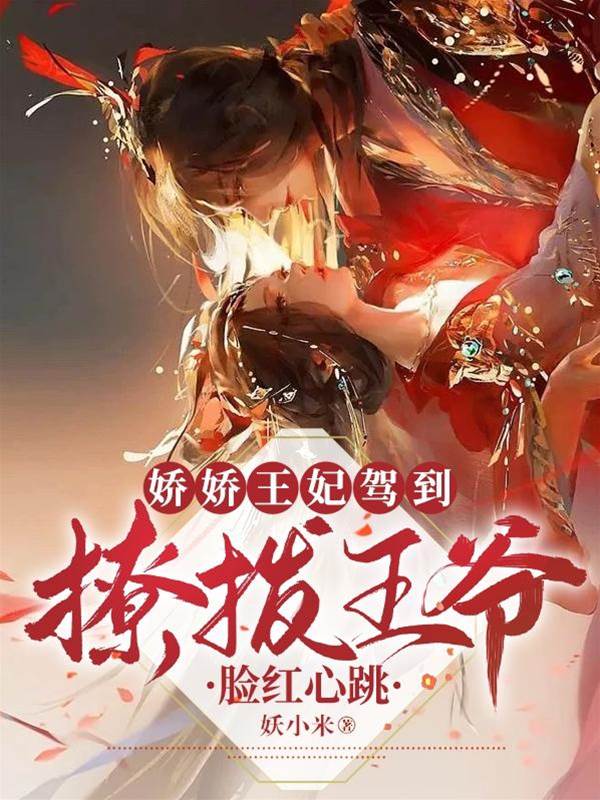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379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347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