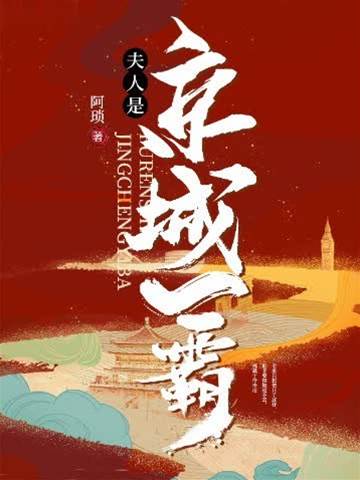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將軍別吃,夫人下毒了》 第二百八十章 大火
林婉城就問道:“汴梁此次的天災嚴重嗎?”
白華笑著搖搖頭:“此次的災害無論是規模還是強度都不如上一次,災后重建工作也做的很到位。而且,咱們有治療瘟疫的靈藥除瘟救苦丹。所以,賑災工作有條不紊,基本沒有太大的困難。”
在場之人聽他如此說,都不由放心地點頭。幾人又聊了京城的況,直到日薄西山,大家才酒足飯飽,歡欣離去。
過了中秋,楚天中被發配去了北疆,楚悠穎親自去十里長亭送別,父兩人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場。楚天中離去后,楚悠穎就在瑟瑟秋風中倒下。
楚悠穎被侍送回王府之后,好幾天都沒有下床。后來,惠妃娘娘特命太醫前去看診,楚悠穎的病才慢慢好轉。于是,朝野外就都在傳惠妃仁德,沒有因為楚家失勢而冷落了楚悠穎。
楚悠穎雖然得到了來自惠妃的溫暖,但是鄭王在朝堂上的形勢卻著實不太好。
自從楚天中倒臺,鄭王在朝堂上的風頭就被平王了下去。鄭王眼見自己即將失勢,他沒有閉門自省,反而搞起一連串的小作。
鄭王派手下在吏部搗,并企圖重新掌控新上任的戶部尚書。這一切的一切自然逃不出崔叔明的法眼。大風小說
崔叔明略施小計,鄭王的計劃就落了空。雖然被抓的人沒有將鄭王供出來,但是皇上還是把他進書房。
隆乾帝看著跪在面前的兒子,只覺得滿眼都是失。過了許久,他才深深吸一口氣道:“這些日子以來,你自己在背地里做了多事?”
鄭王心中本就不滿隆乾帝偏袒平王,聽到他質問自己,忍不住就有些氣悶:“兒臣不懂父皇在說什麼!”
Advertisement
隆乾帝本就肝火很盛,此時他聽到鄭王狡辯,不由一掌拍在龍書案上罵道:“你個畜生!你以為你背地里做的那些勾當朕真的不知道嗎?現在不過是給你一個自認的機會,沒想到,你竟然還敢矢口否認?戶部的那些齷齪事難道不是你的手筆?還有你弟弟府里近來出的那些事,你敢說自己毫不知?”
鄭王心里一驚,知道自己做的這些恐怕皇上已經有了警覺,之所以沒有懲自己,不過是因為沒有抓到確切的證據。
鄭王心里清楚,隆乾帝是在試探自己,自己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咬死不認,否則,只怕齊王的下場就是自己的前車之鑒。
鄭王心里想得清楚,伏在地上失聲痛哭:“父皇明鑒!您不知在何聽說了這些讒言,就扣在兒臣的頭上,兒臣覺得冤枉。兒臣自問這些年來,為了朝廷,為了大周鞠躬盡瘁,一一毫也不敢怠慢,但是父皇您不問青紅皂白就這麼……這麼問兒臣,兒臣心里……”
鄭王再也說不下去,趴在地上哭起來。
鄭王的這些事其實也只是隆乾帝的猜測,他素來了解自己這個兒子,狼子野心,一心想要問鼎九五之尊,所以想要跟平王作對的舍他其誰?
然而,隆乾帝看到鄭王這麼痛哭流涕的樣子,心里也有些打鼓,暗道:要麼是自己這個兒子演技湛,連自己也能蒙騙,要麼就是自己真的冤枉了他。
隆乾帝一時有些拿不定主意,只好擰著眉繼續道:“你非是要朕把證據拍在你面前是不是?你就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嗎?”
鄭王心里咯噔一下,暗道:難不自己猜錯了?父皇真的找到了證據?那自己該怎麼辦?如果自己繼續抵抗,只怕只會讓父皇更加生氣,到時候雷霆一怒,只怕自己承不起……
Advertisement
可是……如果父皇并沒有什麼證據呢?他會不會只是在欺詐我?我如果上當,那豈不是不打自招?
該怎麼辦?鄭王現在猶如站在一個岔路口,前進不行,后不是。他低著頭將自己最近的行為捋了一遍,并沒有發現自己有過什麼差錯。鄭王一咬牙,梗著脖子道:“父皇若是有證據,兒臣定當萬死贖罪,一定三跪九叩給六弟賠禮道歉!”
隆乾帝看著一臉倔強的鄭王,銳利的雙眸微微瞇著,他定定看了半晌,并不能發現什麼破綻,只好哼哼冷笑道:“你是料定了我沒有證據是不是?”
鄭王吃了秤砣鐵了心要跟隆乾帝杠到底:“父皇只將證據拿出來吧!兒臣縱使死在大周律法之下,絕無半點怨言!”
隆乾帝慢慢將桌上的茶盞端起來,舉在前稍微押了一口,稍微平靜了心虛,才冷聲道:“退下吧!”
鄭王聽到這句話,心里的大石頭終于放下來,他知道自己這道坎算是過去了。鄭王立刻變了一副乖順臉,端端正正行了禮,退了出去。
隆乾帝看著他遠去的背影,眉頭不由就擰在一起:自己這個兒子演技果然是進益了。
剛剛自己的那句“退下”其實也是暗藏玄機。前一刻還是疾言厲,后一刻就讓他退下,為的就是看他的反應。
如果是了委屈的人,怎麼可能如此平靜乖順地退下?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會如釋重負,不追究污蔑的事。
鄭王回到家將隆乾帝今日的態度仔仔細細想了一遍,馬上就察覺出不對勁。他偏袒平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只是沒想到他竟然完全不念父子之,對自己的勢力進行如此大規模高強度的打擊。
鄭王心里很疑,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如果任憑這種況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自己就會像那個倒霉的齊王一樣被完全架空,然后自己就只能將萬里江山拱手讓人。
Advertisement
可是如果要起反抗,自己又該怎麼做?
鄭王忽然就想起自己的母妃。惠妃是宮出,一路爬到妃位很是艱辛。平日里,待人溫可親,對待鄭王卻十分嚴格。
開始,鄭王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惠妃那里得不到一母,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才慢慢明白。惠妃是在幫他長,同時也是為了在父皇面前樹立起一個好形象。
在朝堂上,只有惡劣的環境才能使人很快長。在后宮,只有形象溫良才不會被皇上、太后猜忌,才能活得長久。
他們母子二人沒有齊王那樣的外家,也不像平王母子那樣有隆乾帝的寵,所以只有活得小心翼翼,只有靠著這些別人不齒的小心思,他們母子才有可能笑到最后。
然而,正往明白惠妃的苦心時,他已經長大人,那時候,他與惠妃之間早就有了隔閡。雖然,他能夠諒,也非常謝,但是這種東西,并不是說修復就能夠修復的。
因此,鄭王自開府建牙,除了初一十五之外,很進宮給惠妃請安。遇到問題,他也總是自己想辦法解決,只有遇到實在不能決斷的問題,他才會去向惠妃討一個主意。
鄭王派心腹進宮向惠妃討教,宮里很快就傳出了消息。惠妃對于鄭王的境只有一句話:做你自己想做的!
這就是要自己反抗?可是自己現在完全被隆乾帝束縛了手腳,又如何能夠反抗的起來呢?
惠妃似乎早就知道鄭王是窮途末路,所以,除了給鄭王帶來一句話之外,還賞賜了一樣東西下來。
惠妃賞賜的東西不是其他,而是釧皇子進京時,代表然進貢的一塊玉。
鄭王當時將這塊玉親自到鄭王手上:“王爺,金珠就像是這塊玉一樣,都是我們然的寶貝,現在,我將他們一并托給你,希你好生照顧!”
Advertisement
鄭王得了玉不敢獨,趕忙就謹獻給了隆乾帝。隆乾帝得知這塊玉的來歷之后,又賞賜給了惠妃。
鄭王手將裝著玉的盒子接過來,打開一看,頓時擰起了眉:盒中的玉早就殘缺不全、七零八碎。
鄭王不由怒道:“好大膽的奴才,竟然敢摔壞母妃賜下的玉!”
惠妃邊的大宮嫣然一笑:“王爺莫急!且聽奴婢道來。這塊玉自從來到奴婢手里就是這個樣子的,奴婢從來沒有打開過!”
鄭王不由驚奇:“怎麼會這樣?這……難道是……是母妃摔碎的?”
那大宮溫和一笑:“惠妃娘娘希王爺仔細參詳!”說完,也不再停留,給鄭王行了一個禮就退了出來。
鄭王捧著那塊摔碎了的玉,眼睛里一片迷茫:母妃想要做什麼?這摔碎的玉究竟代表什麼意思?
當晚,鄭王趁著夜就去了一趟鄉院。
金珠公主自從被幽之后,就再沒有見過鄭王的面。此時,鄭王夤夜而來,滿臉寒霜,一看就知道來者不善。
鄭王不知和金珠公主說了些什麼,就疾步離開了鄉院,至于他們談話的容,包括鄭王府的家奴在,沒有一個人知道。
過了兩日,鄉院忽然燃起熊熊烈火。鄭王衫不整地從書房里跑出來,慌慌張張就命府上的奴才救火。
鄉院火勢兇猛,火幾乎將半邊天空的照的通紅,住在鄭王府附近的人家全被驚了。似乎整個府上的奴才都在喊:“金王妃還在大火中沒有出來,快救火!快救王妃!”
鄭王府的家奴吵吵嚷嚷,忙活了一夜,才把大火撲滅,只是鄉院只剩下一堆黑炭。
面對著那一大片斷瓦殘垣,鄭王驚怒道:“快去找王妃!”家奴不敢怠慢,在灰燼里拉了半日,才終于才在一個矮墻下找到一燒焦的尸。
尸燒毀的十分嚴重,上的皮、飾早已燒化,只能從邊散落的一顆鴿子蛋大小的寶石勉強分辨出這是金珠公主的尸。
鄭王派家奴清點在大火中喪生的人,數來數去,竟然了一尸。金珠公主從然帶來十二個婢,四個的已經被鄭王理掉,剩下八個隨著金珠公主圈在院子里。
只是,這一場大火之后,侍的尸竟然了一。鄭王不敢怠慢,親自將府上的奴清點一遍,卻并沒有發現那個侍的影。
鄭王不由驚疑:昨夜大火漫天,這個侍是怎麼從大火中的?又是如何從戒備森嚴的王府逃出去的呢?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588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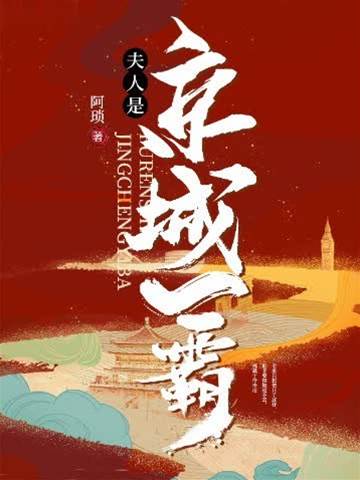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1726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2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821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