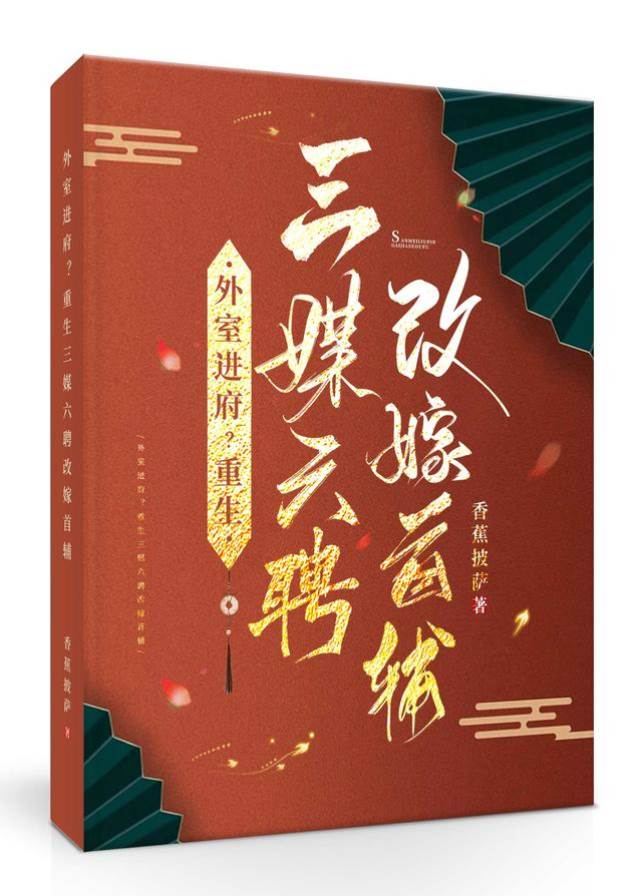《穿書之殘王會讀心》 第13章 我是不會讓你醫治祖母的。
“本當然要詳查。”
林德往包間高位一坐,大手一揮,“帶時天上來。”
今早,時天到衙門擊鼓,狀告怡紅樓制作假賣契,要強行霸占其兒時晴。
這是天理不容的事。
不管狀告是否屬實,他都隨時天來了這好運來酒樓。
沒曾想,天子腳下,竟還真有這種罔顧王法的事。
一怒之下,他破門沖進了屋,本大力懲戒一番怡紅樓的人,可現在……這賣契也不像是假的呀!
那麼,時天與怡紅樓,誰在說謊呢?
他有必要了解真相,再公平裁決。
“時天?”
時富不可思議地重復了聲,沒等他從震驚中回神,時天已在人攙扶下,到了包間。
“草民時天,拜見大人。”
時天一上來,就跪到地上行禮。
“時天,你狀告怡紅樓制造假的賣契,要霸占你兒時晴一事,可有證據?”
林德直奔主題。
“大人,草民從不曾寫過賣契約,他們手中的賣契約定是假的。”
時天肯定地說。
“那你看看這賣契約是否出自你的手筆?”
隨著林德的話,一旁的衙役將賣契遞到了時天手中。
看過那賣契后,時天子了。
雖然他記得清楚自己沒有寫過賣契約,但是,那契約上的一字一筆,確實是他的字跡,就連下方的印章也是他的。m.166xs.cc
“大人,這…這…這……”
時天一時語塞,竟是說不出話來。
Advertisement
“契約是否出自于你的手?”
林德目微沉,穿著服的他,本就一威嚴,如此一來,那通的威更甚了幾分,“如實招來。”
“大人,契約上面的字跡與印章,的確出自于草民的手。”
時天匐磕下一頭說,“可是,草民絕不曾寫過賣契約,更沒有要賣兒的念頭。請大人明察秋毫,還草民一個清白。”
眼看事一下子陷了死胡同,林德本想將人帶回衙門,調查后重審。
這時,一個清脆的音響在了人群中。
“大人,那賣契約是假的。”
林德去,就見一湖藍紗的,婷立于人群之中。
“你是何人?為何如此肯定那賣契約是假的?”
“小時錦,見過大人。”
時錦走出人群,站到時天旁,對林德盈盈一拜道,“小之所以說那張賣契是假的,是因為小手中有著一張類似的假信件。”
說著,時錦從袖中取出一封信抖開,走讓周圍人看清上面的字跡,再遞給衙役呈到林德手中道,“那信上是小的字跡。但小能肯定從不曾寫有那封信。”
看到信,時天詫異地看向了時錦。
他不明白那封信怎麼就到了時錦手中?
更不明白時錦這會兒把信拿出來做什麼?
可疑歸疑,他沒出聲。
時錦的變化,不用時晴告訴他,他亦到了。
是以,他相信時錦那樣做是有目的的。
Advertisement
就像今早時錦讓他去衙門擊鼓告狀一樣。
“你想說什麼?”
林德看了信問。
“時晴。”
時錦對人群后方的時晴招了招手。
時晴為時錦端來了一盆水,放到了屋中的餐桌上。
“大人請看。”
時錦在林德的注視下,拿過信,將信平展開放了水中。
隨著的作,房中眾人的目,不由得都放到了盆中,信上。
在眾人注目下,盆中的信紙以著眼可見的速度,發生了變化。
只見一張張剪裁方正的字紙從信紙上剝離,漂浮在了水中。
直到信紙了一張白紙。
看到這里,所有人哪還有不明白的地方。
很顯然,信紙上的字,都是有心人分開找來,再一字字到信紙上的。
真相也就公布在了眾人眼前。
別說林德看到這一幕驚呆了,就連一旁以張三為主的怡紅樓眾人,也都看呆了去,驚嘆起了那造信之人的心機與能力。
唯有時富……
時富在看到這一幕,臉驀地一白。
他知道那封信與賣契都是假的。
這也是他暗中對時天下殺手的原因。
只要時天死了,那信就是死無對證,就是時天寫的。
一旁的汪雯見時富模樣,也明白了賣契是假的。
趁眾人目都被時錦盆中的信紙吸引時,掙開衙役的手,沖到時天面前,一把奪過時天手中的賣契,塞進了中。
那賣契本就還是一張紙,這一作下,竟被汪雯功吞下了肚。
Advertisement
眾人反應過來時,只看到吞了賣契的汪雯,整個往后倒去。
“祖母!”
時富眼疾手快,上前扶住了汪雯,才讓汪雯避免了與大地親接,“大夫,快讓人請大夫,我祖母暈倒了。”
林德對一旁的衙役示了個眼,那衙役立馬出了包間。
眼見汪雯氣越來越差,時錦上前,“讓我看看吧!”
“不行。”
時富一眼瞪向時錦,厲聲拒絕。
“氣急攻心,引起了腦梗塞。若不及時醫治,之后就算能醒來,余生也只能在床上渡過。”
時錦向時富分析著汪雯的況。
“滾開!”
時富失去耐心地大吼,“別在我耳邊危言聳聽。我告訴你,不管你說什麼,我都不會讓你接近祖母的。更別提醫治什麼的了。”
昨天,在時府,時錦借救治祖母之名,用銀簪扎祖母的事,他聽祖母說了。
是以,此時此刻,他絕不會讓時錦祖母。
“……”
時錦撇了撇。
不醫就不醫。
當想醫嗎?
也不過是走走過場,免得日后被說閑話。
況且,就算出手,也沒打算讓老太太痊愈的。
這老太太那麼偏心,最好是一輩子蹦跶不起來。
“時富,讓我……”
“滾!”
時天也看出了汪雯的不對勁,只是,他剛開口就被時富拒絕了,“一個鄉下的赤腳醫生,也配給我祖母看病,真是癡心妄想。”
一襲話,說得時天臉一陣紅一陣白。
Advertisement
好在衙役這時也把大夫找來了。
大夫替汪雯把了一陣脈后,搖著頭說,“老夫人這是怒火攻心,造了暈厥,我給老夫人開點疏心解氣的藥,老夫人很快就會醒來了。”
看到這一幕,時錦蹙了眉心。
這個時代的醫這麼落后的嗎?
一個腦梗被生生診治氣暈了。
這實在是庸醫誤診啊!
“錦姐姐!”
時晴拉了拉時錦的袖,趁眾人不注意,小小聲地問,“什麼是腦梗塞呀?”
見識過時錦給時天做開顱手后,時晴就對時錦的醫崇拜到了極致。
時富不相信時錦給汪雯下的診斷,相信。
“腦梗塞也稱腦梗死。”
時錦以一種能理解的方式向時晴解道,“是腦部缺、缺氧導致的部分腦組織壞死或化。”
“那祖母……”
“我之前說的是真的。”
時錦知曉時晴想說什麼,知道姑娘善良,也就拍著時晴的手安道,“放心,死不了的。”
這可不是見死不救,這是人家不讓救。
也沒法的。
忽地,門口一陣,時錦回眸間,一張悉的臉闖進了眼中。
猜你喜歡
-
完結353 章

良陳美錦
未到四十她便百病纏身, 死的時候兒子正在娶親. 錦朝覺得這一生再無眷戀, 誰知醒來正當年少, 風華正茂. 當年我癡心不改; 如今我冷硬如刀.
95.5萬字8.43 174645 -
完結2905 章

鳳帝九傾
因一場夢境而來,因一張皇榜結緣。 九皇子要娶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大夫,皇城嘩然。 公主,郡主和帝都所有官家小姐,齊齊反對。 皇上,太后,皇后……警告威脅,明槍暗箭齊上陣,只為阻止這樁婚事。 風華絕代九殿下冷笑,“娶她,我活;不娶她,我死。” 九個字,所有反對的聲音一夜消失。 藥房中侍弄金蛇的女子云淡風輕般輕笑,帶著一種俯瞰世間螻蟻的漠然無情,“娶我?問過我的意見了?” “如果我現在問你呢?”深情的雙眼鎖在她面上,一把匕首抵在自己心口,“是你從地獄裡救我出來,我以身相許。你若不願,我將性命還你,再入阿鼻地獄。 ""這天下,還無一人有資格娶我,更從未有人敢威脅我。 ""那我嫁你,行嗎"
256.6萬字8 114779 -
完結1310 章

帝女難馴
一夕之間,宮傾玉碎,德妃和沐王叛亂奪宮。她親見父皇慘死,母后被玷污,弟弟被殺,她也被素來以純真善良示人的妹妹做成了人彘,死無全尸。 一朝移魂,帝女歸來,涅槃重生! 離那場慘事發生不過還有兩年,兩年,她該如何才能阻止一切,報仇雪恨! 惶惶之際,卻遇見了他,他驚艷才絕,謀略無雙,卻甘愿為她傾力相助,為她成就一切。既然上天如此厚待,她自會攜他之手,共同進退。 惡奴?殺之,讓她們也嘗嘗什麼叫我為刀俎,人為魚肉的滋味。 德妃?斗之,讓她也嘗嘗什麼叫寒夜凄苦,冷宮寂寥的滋味。 皇妹?辱之,讓她也嘗嘗什麼叫錐心刺骨,萬人欺的滋味,帝女重生,與烈火中扶搖而上,傾一世心謀,成就風華無雙。
236.8萬字8 30570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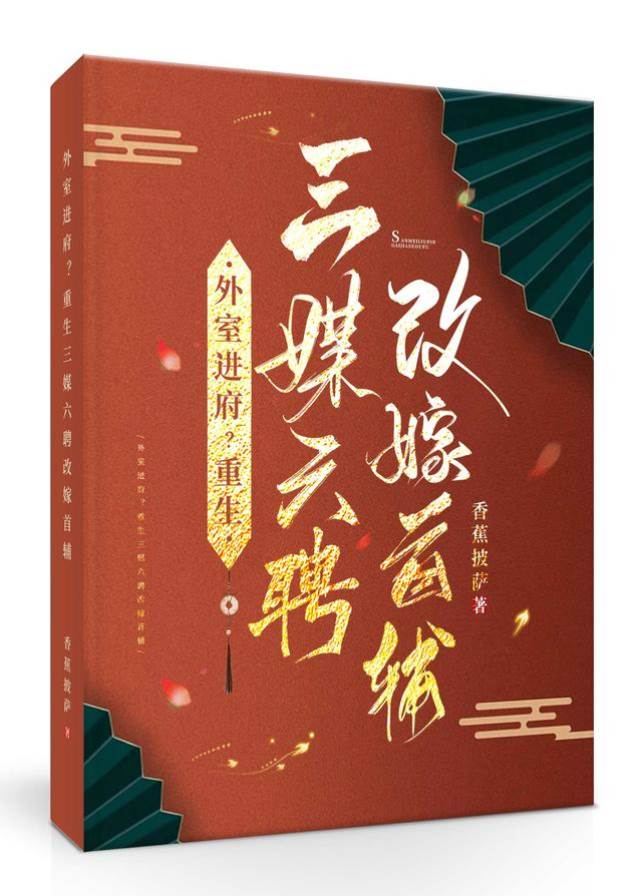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33 53539 -
完結494 章

寵妻無度:腹黑攝政王重生太粘人
【男主重生+追妻+虐渣+1v1+雙潔+甜寵+男主有嘴+傳統古言+18+】大婚當日,沈雁歸在雪地等了足足半個時辰,等來攝政王牽著別人的手入府拜堂,而她,堂堂王妃從
99.6萬字8.18 161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