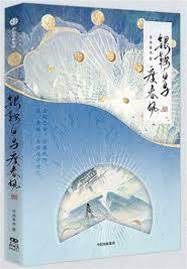《重生成了反派的掌中嬌》 第44章 有漏網之魚
“八大世家,歷來都是陛下的心頭大患,
這次雖然是武安侯狼子野心,栽贓陷害,
但陛下好不容易拿了我和你二叔的職,自是不甘心如此迅速讓我們復原職的。”
溫國公意外的對皇帝的心思極其清楚,
“阿婉,接下來,我們的強敵不僅來自朝中,還有上面的那位。
告訴祖父,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麼。”
溫婉挑挑揀揀的將能說的事都與溫國公說了。
盡管刻意藏了一部分,溫國公還是嘆不已。
“阿婉,你是真的長大了!”
曾經只會躲在閨閣里看書度日的小孩兒,能以一己之扛起整個溫國公府,已經足夠讓他驚訝。
沒想到,自己能活著走出詔獄,竟然也有孫的功勞。
這溫國公如何能不驚訝?
溫婉卻淡笑著道:“孫只是在合適的時機里抱了一條大罷了,
這其中欠下的人,卻是要祖父去還的,祖父又何須如此驚訝?”
沒錯,溫婉將自己做的所有不方便說出口的事都推到了謝淵渟上,
心中暗暗苦惱,祖父如今出了獄,看來,謝淵渟那邊得早早對下口供了,
不然說,穿幫就完蛋了。
適逢和靖北候府約好的時間也到了,溫婉便以回田莊收拾東西為由,去了南郊別院。
上次來時,還是整整齊齊的一家四口,如今卻只剩下靖北候和謝淵渟父子。
溫婉這才想起來,長公主和謝中渟奉命回靖北主持大局去了。
“侯爺恢復的如何,可有些知覺了?”
溫婉按著靖北候上的幾個位問話。
靖北候點點頭,“此前雙毫無知覺,最近偶爾會覺到疼,還有些麻麻的。”
“有知覺就好。”
Advertisement
溫婉拿了筆墨重新開方子,一邊道:“還是十天的劑量,我每隔三天便會來施一次針。
只是現在回了府,我再來別莊不是很方便,侯爺能不能換個地方?”
“可以。”
不等靖北候說話,謝淵渟就做了主,“上次你我見面的酒樓雅間,屆時我和父親在那里等你。”
他敢安排,溫婉就沒什麼不敢應的,應了聲,為靖北候施針。
心里惦記著事,治療很快就結束。
出了別莊,謝淵渟卻道:“是你威脅那些大臣為溫國公府求的?”
“二公子在說什麼,我聽不太明白。”
溫婉揣著明白裝糊涂,“有人為我祖父求,我怎麼不知道?”
固然不會認,謝淵渟卻已經認定是所為。
“我不管你那些東西是哪兒來的,但你一次威脅了那麼多大臣,
目的還如此明顯,你以為那些人會放過溫國公府嗎?”
謝淵渟簡直搞不清楚溫婉究竟是聰明還是愚蠢,
“一個武安侯就能害的你們闔府上下幾乎送命。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被你威脅的大臣若是聯合起來,溫國公府會是何等下場?”
“想過又如何?”
深知謝淵渟能來問,心中定是有了定論,溫婉干脆也不裝了。
“你想讓我怎麼做,手握證據而無于衷,眼睜睜看著我祖父他們白白送命嗎?”
溫婉冷靜道:“你靖北候府有二十萬大軍讓他們投鼠忌,可我有什麼?
二公子想讓我怎麼辦,啊?”
“你,你別生氣啊!”
明明溫婉的語氣并無起伏,但謝淵渟卻敏的察覺到緒中難掩的怒意,
“我沒不讓你救人,可救人也得講究方法啊!
你這樣一來,不是明晃晃的把溫國公府擺在那麼多大臣的對立面了嗎?”
Advertisement
謝淵渟有些無奈,他不怕人跟他生氣,大吼怒罵都無妨。
就怕這種不聲的將所有緒藏起來的人。
忙語無倫次的安。
溫婉卻并不領,“我做都做了,還怕他們報復不?
大不了我讓祖父辭,我們回幽州老家去。
無一輕,祖父勞一生,也該清福了。”
謝淵渟失笑,“以溫國公如今的地位,你真覺得他能說走就走?”
溫婉哼了一聲,頗不耐煩的瞪他,“你到底想說什麼?”
追上來啰嗦了這一通,謝淵渟分明是有想法的,愣是憋著不說,溫婉想打人。
“溫國公府最近正于敏的地位,無論是陛下還是朝中大臣,暫時都不會對你們出手,
安分一些,別再有什麼小作。”
知道溫婉只是一世氣惱,并不會沖行事,謝淵渟才娓娓道來。
“回頭勸勸你祖父,一味地妥協不是辦法。
既然退到如此地步,陛下都不放心他,不若重握兵權,做個真正功高震主的權臣。
當然,這只是我的建議,要不要采納,全在于你祖父自己。”
溫婉記得,曾祖父杯酒釋兵權后,其實也是留了一手的。
只是前世事發突然,祖父又愚忠,沒機會走那條退路而已。
如今祖父既然出獄,那是不是說明,未來的一切都將與前世不同了?
如此思索著,溫婉的心思未免就復雜了些,“你,為何要與我說這些?”
靖北候府已然困,無論是皇帝還是朝中大臣,暫時無能力與靖北候府為敵。
如今正是靖北候府休養生息的好機會,謝淵渟主提醒,讓溫國公府早做打算,
分明是想要打破目前八大世家與皇室的維持已久的平衡。
Advertisement
在溫婉看來,這并非明智之舉。
“既然這京都容不下靖北候府,那我不妨再把這池水攪渾一些,
讓那些藏在底下的臭魚爛蝦全都浮出水面,不好嗎?”
“你要把所有的矛盾擺到明面上?”
溫婉微驚,“長公主能同意嗎?”
包括皇室在,八大世家在桌子底下踹腳不是一天兩天了,但表面上還在飾太平。
謝淵渟卻如此不加遮掩的表達出對皇室的厭惡,同為皇室眾人的長公主能樂意?
謝淵渟豈能不明白溫婉心中顧慮,了然道:“我母親心中清楚的很,親疏遠近,分得清。”
早在太后和皇帝明明不放心謝宗麟,卻還是要將長公主嫁給他的時候,
長公主就不把自己當皇室之人了。
為謝宗麟的妻子,謝淵渟兄弟倆的母親,知道誰才是自己最重要的親人。
溫婉由衷的慨,作為天玄歷史上第一個穿著鎧甲上陣殺敵的人,長公主真的非同一般。
……
隨著案真相大白,武安侯府一家也被押解回京。
事牽扯諸多,證據確鑿,為了殺儆猴,也是避免夜長夢多,皇帝直接下令滿門抄斬。
行刑當天,溫婉特地去觀刑。
武安侯府上百口人跪在菜市口,頗為壯觀。
溫婉一一看過去,沒看到那個悉的面孔,下意識的眉頭微蹙。
坐在對面的謝淵渟注意到的神變化,也跟著向外看去,“怎麼,可是有何不對?”
“武安侯府的人都在這里了?”
溫婉趁著說話的功夫又找了一遍,確定自己要找的人不在。
“不是說滿門抄斬,我若沒記錯,連襁褓中的嬰兒都死了吧?
為何武安侯府的二小姐卻不在?”?
Advertisement
忙活了這麼久,真正要對付的本不是什麼武安侯府,而是秦挽裳。
可是,秦挽裳并不在下方等候斬的人群中。
“你確定沒有看錯?”
謝淵渟微愕,“你說的那武安侯府的二小姐今年多歲?”
天玄太祖于世中立國,建國之初,律法條例多顧及民意,
即便是滿門抄斬或者株連九族的大罪,也會適當赦免或者減輕十歲以下的懲罰。
即便朝廷不放心,也只是私底下死,不會帶到法場上。
溫婉明白謝淵渟這話的意思,連連搖頭道:“已經十四歲了,比我還要年長一歲。”
話說完,溫婉的臉跟著難看起來。
想起了秦挽裳那通天的手腕,
難道說,秦挽裳的心計之深沉,在這種時候已經發揮作用了?
前世從旁人口中聽到秦挽裳的種種傳聞時已經是很多年以后了。
那時候秦挽裳已經憑借雷霆手段幫助太子傅恒與二皇子傅軒博弈多年,
朝堂上下皆是關于秦挽裳這位奇子的傳聞。
若非溫國公府遇害的種種線索都指向前晚上,溫婉都會被秦挽裳這個奇子給折服了。
以為秦挽裳是了太子妃后才大展拳腳,卻原來,這麼早就出鋒芒了嗎?
“你確定秦挽裳不在其中?”
謝淵渟再度向求證。
溫婉沉沉點頭,“我認錯誰,也不會認錯。”
那是恨到骨子里的敵人,如何能忘記?
下意識的回答后,溫婉就驚愕的看到謝淵渟匆匆跑了出去。
午時三刻將至,監斬臺上的忠義侯熱的汗流浹背,只恨不得早早完任務向陛下差。
正扔下紅頭簽,下令行刑,卻聽一道帶著戾氣的聲音道:“尚書大人且慢!”
“謝二公子、不,謝指揮使,你這是作何?”
白牧皺眉看著謝淵渟,他倒是不懷疑謝淵渟是來劫法場的。
只是擔心這個紈绔是要變著法兒的折磨武安侯府的人以泄心頭之憤。
眾目睽睽之下,他若是應了謝淵渟,無異于徇私枉法,
若是不應,又要得罪這個紈绔。
猜你喜歡
-
完結277 章

醫妃有毒
前身被下藥,爲保清白撞柱而亡,卻把她給撞來了!雖然僥倖還活著,卻不得不爲了解藥找個男人劫色!!貪歡過後,她毫不猶豫拿石頭把男人砸暈了!天妒英才,想我堂堂的皇子,居然被一個女人趁機劫了色,完事了就把我砸暈了不說,還把我僅剩的財物都給摸走了!女人,你怎麼可以這麼沒下限?
78.6萬字8 47890 -
連載791 章
攝政王妃狂虐渣
她明明是侯府真千金,卻被假千金所矇騙挑撥,鬨得眾叛親離最後慘死。一朝重生,她重返侯府鬥惡姐虐渣男,順便抱上未來攝政王的金大腿。抱著抱著……等等,這位王爺,你為何離的這麼近?攝政王強勢將她抱入懷,冷笑道撩完再跑?晚了!
126.1萬字8 89085 -
完結81 章

暴君的籠中雀
葉蓁蓁六歲那年不慎落水,一場大病之後,她腦子裏多了一段記憶。 她知道大伯收養的那個陰鷙少年葉淩淵會在幾年後被皇帝認回皇子身份。 她還知道葉淩淵登基後,因為對大伯一家曾經的虐待懷恨在心,狠狠報複葉家,她和爹娘也沒能幸免。 她還知道他會成為一個暴君,手段殘忍,暴戾嗜殺。 重來一世,她發現少年和她記憶中的人天差地別,忍不住靠近
47萬字8 20812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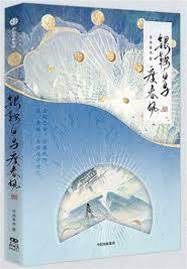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9 -
完結437 章
媚色難囚
一心復仇釣系心機美人vs禁欲清冷白切黑偏執大佬被心愛的夫君冷落兩年,最終趕出門去,沉尸河底。借尸還魂,重回夫家,她成了身懷秘密的遠房表小姐。媚眼如絲,顛倒眾生,她是令男人愛慕、女人嫉妒的存在。只有那清冷高貴的前夫,始終對她不屑一顧,眼神冰冷,一如既往。只是這次,她卻不再逆來順受,而是用媚色織就一張網,徐徐誘之,等著他心甘情愿的撲進來然后殺之而后快!裴璟珩紅了眼角嬈嬈,你依然是愛我的,對嗎?阮嬈嫵媚一笑你猜。(以下是不正經簡介)她逃,他追,她插翅……飛了!他摩挲著手中龍紋扳指,冷笑下令,“抓回來,囚了!”他囚了她的身,她卻囚了他的心。情欲與愛恨,走腎又走心。
86.5萬字8 29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