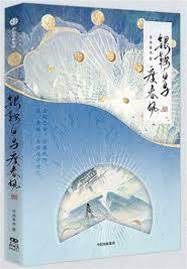《權寵天下:盛寵毒醫小嬌妃》 第81章 扣押
聽到這個聲音,方才始終沒有多大反應的阮桃卻是皺了皺眉。
只覺這聲音為何會如此耳,似乎在哪聽過似得。
“聽到沒有,耽擱了我們司侍大人的要事,你們可擔待得起?”
聽到這聲為他們說話,對方便更為囂張了。
阮桃聽得直皺眉,一時有些琢磨不這人的來意。
按理來說,司侍乃是宮廷,不該如此大張旗鼓地前往宮外才是。
“司侍大人不應該是在宮里頭伺候皇上與娘娘們嗎?不知為何要去王府,有何貴干?”
想到這阮桃便不再沉默,開口試探道。
“本奉陛下的命令前來,你們只管讓路便是了。 ”
外面那子的聲音也有了幾不耐煩,帶的侍衛們更是端著一副狗仗人勢的模樣喋喋不休。
雙方爭執不下,一時僵持,只是未過多時那一直在開口與車夫對質的男人便好像失去了耐心一般,開始大聲嚷起來。
“我倒要看看這馬車里是哪個頭烏,好狗不擋道,有本事就出來!”
這話甚是鄙難聽,一下便像捅了馬蜂窩一般,惹得王府眾人怒目而視。
“大膽,你怎敢如此詆毀我們王妃殿下!”
“豎子竟如此囂張,我看你們不是宮的私事大人,而是故意挑事,想要離間陛下與王爺的反賊!”
隨著幾段又急又重的爭吵聲,外面僵持的兩隊車馬終于是按捺不住,廝打了起來。
一時鬧得人仰馬翻,遍地都是哀嚎之聲。
阮桃不如山的坐在轎,并沒有率先出去。
因為再次聽到那子的聲音,已然分辨出了來者何人。
這聲音可不正就是那日在皇帝的壽宴上假冒于的所謂“桃夭”嗎?
發現了這一點之后,便再也未曾著急。
Advertisement
畢竟王府之中能帶出來的侍衛都是銳,不至于被一群烏合之眾所打倒。
再加上有意挫挫那子的氣焰,便默認了王府的侍衛教訓他們。
畢竟是對方先出言不遜,即便是陛下那邊追查下來,也是他們占理。
既然對方給自己遞了刀子,那己方又豈有不收的道理?
阮桃已然在心底算計好,到時論起來便一口咬定是對面下流鄙,出言不遜,自己以為是旁人冒充要代為教訓一番便是了。
外面打得熱火朝天,阮桃卻不不慢地閉目養神。
“住手,你們不要再打了!”
那子的聲音再次響起,卻是有了幾分慌。
阮桃聞言睜開了眼,悄悄地掀起簾子瞄了一眼。
只見一個王府的侍衛已然拎著一把劍挑開了轎門,要看看對方是何種模樣。
而轎的子終于是慌了,即便強作鎮定的仍舊就待在轎,那卻是不住地往后。
“好了,都住手吧。”
阮桃刻意等那侍衛的劍快要架到那子的脖子上之時,方才不不慢的喊了聲停。
王府的侍衛聞言都聽話地停止了與對方的糾纏。
由于有不侍衛都是前次與阮桃一起去過苗疆的,所以對的話也極其信服。
阮桃說一,他們絕不會說二。
當然,王府的侍衛雖然停止了與對方兵刃相,卻并沒有放松警惕,而是一個個手握著劍監視著對方的行。
“怎麼會是你,王妃殿下?”
當阮桃緩緩掀開了簾子之后,對面的子臉上毫無意外之,卻發出了一聲夸張的驚嘆。
“臣見這奴才如此出言不遜,只當是哪位不長眼睛的在冒充王府之人,方才讓下人們出言教訓呢。”
這話說的半真半假,這若是不知道的人,倒還真以為他們這是路見不平呢。
Advertisement
阮桃卻對的話置若罔聞,對其反問道:“你是何人?本王妃未曾見過你。”
今日那冒充名號的子換了一裳,連帶著蒙面的面紗也大相庭徑。
阮桃雖然聽出了的聲音,卻是不愿指認。
“既然是陛下親自冊封的司侍,并且要來王府為王爺診治,是否有陛下所綬旨意?”
“陛下并未擬旨,只是傳了一道口諭,怕是此時還未曾到王府之中,請……”
“大膽!”
阮桃還未等將話說完,便一聲怒喝打斷了的話。
“好一個假傳圣旨的人,王爺從未有什麼病癥在。依本王妃看,你們怕是要打著陛下的幌子前去刺殺王爺!”
無論被封為司侍是真是假,只要不出皇帝的旨意來,并且阮桃一口咬定不認識,便不用對客氣。
阮桃說著將方掀起一角的珠串簾子猛然擲下,白玉珠子撞的聲音清脆作響。
“來呀,將這些叛徒逆黨統統給我拿下,送至王府由王爺發落。”
說完,便繼續安然自得的坐在馬車,聽著馬車外再次響起的喧嘩之聲。
只是這一次為過多時,外面便安靜下來。
“并報王妃殿下,人已被我等盡數拿下。”
外面傳來了侍衛首領的通報聲。
“做的不錯,待回王府之后,本王妃定會嘉獎于爾等。”
阮桃面無波瀾地應了一聲。
一是對面的車隊便被阮桃帶來的侍衛所接管。
兩隊車駕并作一隊,浩浩地趕往了王府。
待阮桃悠閑地踩著腳踏下了馬車之后,便見那個子被劍挾持著,看向自己的眼神帶著恨意。
而那子所帶的隨從們也都一副憤憤不平的模樣,甚至有人還嚷著:“你這樣做就不怕陛下降罪嗎?”
Advertisement
只是很快那個囂的人便被侍衛用劍柄捅在了肚子上,疼得彎下了腰。
“都老實的點,今天查不出你們的幕后主使,你們都休想有好果子吃。”
阮桃心底暗笑,卻是裝作一副毫無察覺的模樣,指揮著那些侍衛將他們押王府之中審問。
“這個領頭的不要用刑,免得畏罪自殺了。”
而阮桃自己則是悠哉悠哉地踱步從那子旁路過,并貌似漫不經心的說了句話。
“就關在王府的廂房之中,送些水與吃食,別死了。”
那子似是知道掙扎無用,也沒有多說什麼。
顯然雙方都知道對方的意圖,但是阮桃就是不吃那一套。
既然說自己是陛下封的,那便拿出證據來。
但顯然沒有隨攜帶信之類的東西,那邊只能由得阮桃扁圓,吃了這一記下馬威。
那些個侍衛常在王府之中伺候,自然是看得懂主子的意圖。
見阮桃下令,侍衛們倒也沒有,只是松開了架在子脖子上的劍,指著前方為引路。
“這位刺客姑娘,請吧。”
待那子心不甘不愿地跟著去了,阮桃看著旁邊一眾剛才還在狗仗人勢的侍從們,此刻都像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
的角勾起一抹笑容,明可人,一時那些人都看呆了。
但阮桃說出來的話可沒有的容這麼令人欣賞了。
“至于其他人都帶下去,好好伺候著,別死了就行。”
這宛如地獄惡鬼的話從一位漂亮的人兒口中說出,更添了幾分冷艷之。
無視那些或求饒、或慘嚎的聲音,阮桃頭也不回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之中。
在外待了這幾天,到底還是沒有住慣了的地方舒服。
Advertisement
阮桃高高興興地將那些個“刺客”拋至了腦后,早早地洗漱歇息下來。
現在這時,王府中侍衛首領早已將阮桃的所作所為全數告訴了玦。
“啟稟王爺,雖然是王妃下令,但此事茲事大,屬下不敢瞞王爺。”
玦聽完了屬下的匯報,臉上雖然沒有什麼表,但也沒有表現出反對,只是點了點頭命他退下。
只是當那侍衛首領將要退出書房之時,卻是聽到了玦的聲音從后傳來。
“今后王妃如何吩咐,你們便按的吩咐照做便是,不必再來匯報本王。”
已然過門檻的侍衛首領卻是一個踉蹌,險些撲倒在地上。
“是。”
他又轉過,畢恭畢敬地應了一句,回時卻忍不住了額角的冷汗。
他雖是個侍衛首領,卻跟隨玦多年。
玦向來只將權勢掌控在自己手上,即便是玦最親近的下屬也不能擅自決定某件事。
故而當玦如此說的時候,侍衛首領只覺得今兒個是不是風聲有些過于喧囂,以至于他都開始幻聽了。
當然,很快他便被玦的一句話打消了念頭。
“王妃是這個王府的主人,你領命照做便是,不用遲疑。”
“屬下明白。”
這侍衛首領又是苦兮兮地轉過再次行禮,只是這回他離開的腳步卻是輕快了不。
作為下屬,他們又何嘗不知道王爺這些年過的并不痛快。
皇家爭斗,向來是你死我活、爾虞我詐,定然沒有置事外的道理。
而王爺從小便是活在這等環境中掙扎求生。
作為他多年的老下屬,侍衛首領幾乎見證了他一路上所經歷的種種,對這位王爺的心態也并不是像對主子那般簡單。
除了為主盡忠,侍衛首領也將自家王爺視為親人一般的存在。
現在王爺有了一個可以全然信任的人,這位侍衛首領只覺得欣非常。
猜你喜歡
-
完結277 章

醫妃有毒
前身被下藥,爲保清白撞柱而亡,卻把她給撞來了!雖然僥倖還活著,卻不得不爲了解藥找個男人劫色!!貪歡過後,她毫不猶豫拿石頭把男人砸暈了!天妒英才,想我堂堂的皇子,居然被一個女人趁機劫了色,完事了就把我砸暈了不說,還把我僅剩的財物都給摸走了!女人,你怎麼可以這麼沒下限?
78.6萬字8 47890 -
連載791 章
攝政王妃狂虐渣
她明明是侯府真千金,卻被假千金所矇騙挑撥,鬨得眾叛親離最後慘死。一朝重生,她重返侯府鬥惡姐虐渣男,順便抱上未來攝政王的金大腿。抱著抱著……等等,這位王爺,你為何離的這麼近?攝政王強勢將她抱入懷,冷笑道撩完再跑?晚了!
126.1萬字8 89041 -
完結81 章

暴君的籠中雀
葉蓁蓁六歲那年不慎落水,一場大病之後,她腦子裏多了一段記憶。 她知道大伯收養的那個陰鷙少年葉淩淵會在幾年後被皇帝認回皇子身份。 她還知道葉淩淵登基後,因為對大伯一家曾經的虐待懷恨在心,狠狠報複葉家,她和爹娘也沒能幸免。 她還知道他會成為一個暴君,手段殘忍,暴戾嗜殺。 重來一世,她發現少年和她記憶中的人天差地別,忍不住靠近
47萬字8 20744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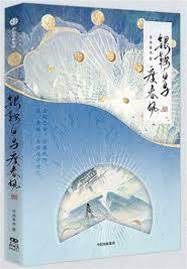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2 -
連載437 章
媚色難囚
一心復仇釣系心機美人vs禁欲清冷白切黑偏執大佬被心愛的夫君冷落兩年,最終趕出門去,沉尸河底。借尸還魂,重回夫家,她成了身懷秘密的遠房表小姐。媚眼如絲,顛倒眾生,她是令男人愛慕、女人嫉妒的存在。只有那清冷高貴的前夫,始終對她不屑一顧,眼神冰冷,一如既往。只是這次,她卻不再逆來順受,而是用媚色織就一張網,徐徐誘之,等著他心甘情愿的撲進來然后殺之而后快!裴璟珩紅了眼角嬈嬈,你依然是愛我的,對嗎?阮嬈嫵媚一笑你猜。(以下是不正經簡介)她逃,他追,她插翅……飛了!他摩挲著手中龍紋扳指,冷笑下令,“抓回來,囚了!”他囚了她的身,她卻囚了他的心。情欲與愛恨,走腎又走心。
86.5萬字8 29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