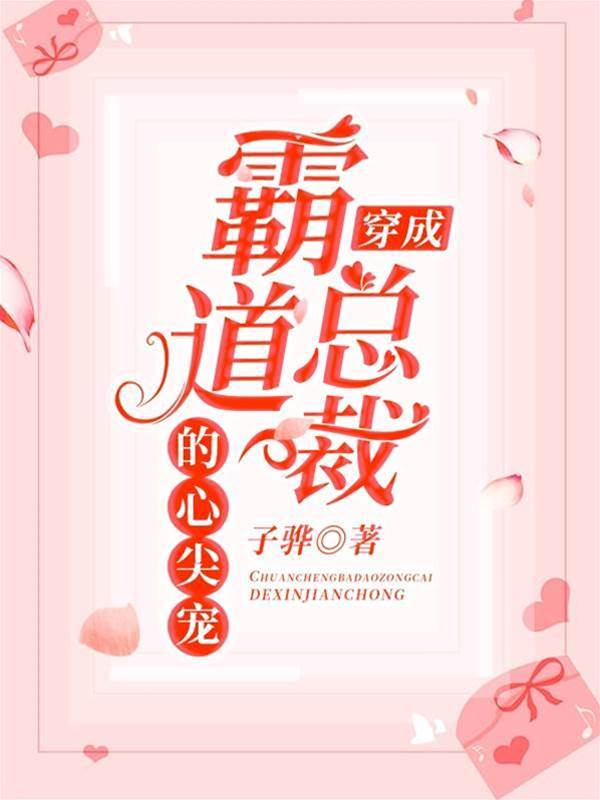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阿瑯》 206,道歉
領頭的衙差聞聲抬起頭,和一雙幽深的眼睛撞在一。衙差頭領不自然地蹙了蹙眉,接著去打量這個問話的男人。
看對方的穿著打扮,并不是多麼貴重的人,只是說他是行走江湖的商人,在對方上又毫不見商人的市儈之氣,灑超然好似魏晉子弟。
頭領一時不準阿瑯的份,再加之阿瑯的語調很自然,又帶著些許的好奇,讓他無從可以拒絕。
只停頓了一會兒,衙差頭領道,
“這位犯乃是因為在朝堂上彈劾清河王在邊境的一些不法作為,怒圣上,被判了流放之刑……”
這個回答,就有些奇妙了。
人人都知清河王到邊境去是為了打敗叩關的敵寇,只是不法作為,是什麼作為?怎麼個不法?
人的腦子是活的,只要去想,就能想出千百種各種不同的東西。
這位衙差頭領,看似回答了,卻含含糊糊的,讓人不有自主地去猜想。
阿瑯看著那衙差,道,“哦?不知清河王做了哪些不法之事,惹得這位大人愿丟。”
阿瑯對于這位老人是有些悉的。他是史臺的史,一向以耿直出名。
當時和寶珠郡主他們一起玩耍的王姣正是他的孫。
因為王姣,對于王史也略知一二,見過幾面。
為首的衙差聽出阿瑯的口中帶著一些質問,又再次打量了一番。差從上京而來,也不是沒見過世面的小吏,既不準阿瑯的態度,他決定主試探。
“貴人既開了尊口,這鐐銬也能暫時除去。”
阿瑯輕輕一笑,背著手,搖頭道,“不用了,小人不過是好奇而已,這樣好,萬一除去鐐銬,讓犯逃走的罪責小人可擔待不起。”
Advertisement
“既然是犯,差大哥怎麼看管嚴厲就怎麼來。”
為首的衙差楞了楞,沒想到試探出的竟是這樣的一個回答。
心頭的那點子疑也就被按了下去,如此也不再管阿瑯,正巧掌柜的將后頭的院子整理好,恭敬的請差等人進去歇腳。
阿瑯怎麼也沒想到,竟然是王姣的祖父帶頭彈劾蕭珩。
還在上京時,和王姣的祖父見過幾次,從他的言行,以及在朝臣中的風評,并不像會做這件事的人。
差押著王老史往后院而去,經過阿瑯一行人時,阿瑯側了側子,為首的差朝微微點頭。
王老史在經過阿瑯后沒幾步遠,又轉看了眼阿瑯,最后回頭前走去。
阿瑯對王老史投過來的目沒有任何的躲避,而是微笑著直視回去。
幾日沒有下樓,阿瑯帶著仆從幾個也沒有撿雅間去坐,而是就在大堂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點了幾樣酒菜,坐著聽邊上人的閑談。
邊上有幾個走鏢的鏢師回頭沖著他們張,見著阿瑯獨自一人坐著,碧枝等幾個則是站在后,頭接耳地說笑。
覺得阿瑯這看起來不怎麼地,派頭倒是大的。
阿瑯只當著沒聽見,坐在位子上收集著四面八方的消息。
不聲地點了點桌面,“你去問問,嫂子和侄兒,可還需要什麼東西,補齊后,我們就要開始行路了。”
十三連忙上樓去詢問,下頭幾個鏢師見著十三上樓,頓時笑了笑,招呼伙計過去,“小二,再給我們添些酒水鹵饅頭。”
旁邊有人阻止,“老七,老大可說過,不讓喝酒的。”
那個老七的‘嗨’了一聲,“無妨,老大這會正睡得香,不睡到天黑都不會起,你們不說,他怎麼會知道?”
Advertisement
“再說了,這趟貨不過就是笨重些,又不值錢,怕什麼。”
同桌的鏢師攔不住老七,只好由他去了。
小二走到柜臺邊,跟掌柜的低聲說話。
掌柜的笑道,“這你也要來問我,客人說要什麼,咱們有得就要給客人。”
阿瑯清楚地看到,掌柜的一邊說,一邊在柜臺臺面上畫了點什麼。
小二見狀,當即轉去了后廚。
阿瑯微微地看了眼碧枝,就見碧枝頷首,轉朝門外走去。
那邊,小二的轉去后廚,沒多久就端了酒菜冷盤上來。
他手中托盤還留著一樣菜,聽他的場,這菜大抵是要送到押送犯的那些差手中。
阿瑯他們坐得位置,邊上的道通往后院,差他們歇腳的院子。
小二端著菜,往阿瑯坐得這邊走來,經過阿瑯的位子時,也不知是手還是腳,竟是一個趔趄。
那托盤里的菜,竟是作流暢地從托盤上跳到了地上,飯菜倒在地上,滿屋子都是飯菜的香味。
很不錯的飯菜,只是阿瑯卻是從袖兜里出一塊帕子,捂住口鼻,并且往后退了一步,
“掌柜的,你這伙計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飯菜都灑在本客人的上了……”
阿瑯一臉的不舒暢,守在后的一個侍衛毫不猶豫地上前,將那掉落在阿瑯不遠的餐盤給踢得老遠。
小二被眼前的形給嚇了一大跳,好不容易回過神來,想要默默地把灑在地上的飯菜掃走。
那餐盤也不知去了哪里。
他不斷躬給阿瑯作揖,賠罪。一副諾諾地樣子。
正巧,在里頭歇腳的差從里頭出來,邊跟著的是王老史。
一看到地上的飯菜,王老史就知道,這本該是送到他手上的,如今卻是被打翻了。
Advertisement
當即氣得是渾發抖。
“你……真是欺人太甚,世態炎涼,窮鄉僻壤出刁民,今日老夫落難,總算看盡了人冷暖……”
阿瑯挑眉,這老史手指被氣得直打哆嗦,竟是指著阿瑯不放。
“這位犯原來竟是到了這里才看到人冷暖嗎?小人還以為,你早該看盡了呢。如此,也該習慣了也。”
“畢竟,像你這樣在背后刀的人,是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這位小二很不錯,你不配吃這麼好的飯菜……”
阿瑯面帶微笑,語氣冷淡。
蕭珩為何出京,又為何沒和一同前往邊境,不就是邊境的形式有變嗎?
可這些人,在上京高床枕,卻如此對待一片赤子之心的人,別說,任何人都會寒心。
王老史被阿瑯的這番話給氣得臉都青了。
“你……你……你……你懂得什麼?如今大周朝好不容易安定下來,不圖謀國富民強,竟是四打戰,這不是讓我們本不富裕的國家,雪上加霜嗎?”
阿瑯‘哈’的一聲笑了起來,
“是嗎?難道是我們想要打戰嗎?這次為何會打戰,你難道不知道嗎?是周邊小國,聯合起來叩關。”
“按照你的意思,為了國富民強,竟是讓他們隨意的擾邊境百姓嗎?”
“難道邊境百姓就不是大周朝的百姓嗎?”
“你住在上京,你知道邊疆百姓的痛苦嗎?上說著為民請命,要國富民強,卻不把邊境的百姓當人看,這什麼?”
那邊上的鏢師在這邊有了靜后,立刻就回過來看熱鬧,聽到阿瑯問話。
那喝了點酒的老七大著舌頭接過話頭,
“這滿口仁義道德,忠君國,世界上滿肚子男盜娼,貪圖樂。”
Advertisement
他朝地上啐了口,“呸,偽君子……”
邊上的鏢師連忙捂住他的,不讓他再繼續說話。
王老史本就被阿瑯氣得臉發青,這會更是搖搖墜,恨不能找個地鉆了進去。
“你們……你們……”
阿瑯笑容滿面地,朝地上還沒來得及掃掉的飯菜點點下,
“這麼好的飯菜,真不該給你這個偽君子吃。忠君國,國富民強都還沒達到,怎麼能吃?”
“如此為民請命的好,就應該和邊疆的百姓一樣,三個月吃不上兩回。”
王老史面發青,搖搖墜,終于,嚶嚀一聲,被氣得昏厥過去了。
押送的差是真的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
他剛才帶著王老史出來,是要將人送走,沒想到還沒出門,竟就被氣得昏厥過去。
剛剛就不應該在這個客棧歇腳,就應該直接到雍州府的驛站里去歇腳。
那是府的驛站,落腳的人不會有閑雜人等,更不會出現眼前的這個況。
沒等押送的差把腸子悔青,就聽到大堂里發生更大的,一聲能刺破耳的尖聲傳來,讓人忍不住捂住耳朵,想要大罵。
“死狗了,死狗了……天吶,這飯菜有毒……”
也不知從哪里竄來一只臟兮兮的野狗。地上香噴噴的飯菜被了個干凈,肚腹那里鼓鼓的,吃了個飽。
不過,這樣味的一餐,卻了它的最后一餐。
狗兒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剛剛從小二托盤里完地摔到地上的飯菜里有毒。
“不是小人做的,不關小人的事。”才剛回神的小二立刻又被下懵了。
下意識地朝差等人搖頭擺手,
“小的萬萬不敢做出這樣的事來……”
若不是小二,那就是客棧的大廚了。
只是不管是誰,這個客棧要倒大霉了。
掌柜得從人群里鉆了進來,看到這一幕,差點癱在地,幸好被打翻了,若是真的有人死在客棧,那這客棧也崩想要開下去了。
碧枝還有十三,不知什麼時候,和別的侍衛一起,將阿瑯悄悄地圍了起來,保證不管發生什麼意外,都不會讓傷。
阿瑯拍了拍口,一臉的害怕,“這……這……簡直太可怕了。”
抖了抖被飯菜弄臟的袍,嚇得都要哭了,
“快,快,帶我去換裳,我可不想死……”
王老史的心很復雜,他沒想到,在這流放的路上,竟然有人想要毒殺他。
當初,他會彈劾蕭珩,是因為有人投了書信到史臺暗設的弊竹里。
所謂的弊竹,就是一個長約一尺的竹筒,一般設立在偏僻的巷子里。
若是有人想要檢舉某些員的惡行,就可以悄悄的把信投進去,自有史臺專門收弊竹的人來取。
原本,以他的資歷,是不會去收弊竹的,可那天史臺里的人都有活兒,正巧,那條暗巷又在他家府邸的附近。
于是,他去將之取了出來。
誰去弊竹那里取了信,那麼,就由誰在朝堂上彈劾。
那天,他拿到的,正是彈劾清河王蕭珩的信簽。
拿到展開的那一刻,他就知道,這是一個局。
只是,他就算知道這是個局,他也不得不往里跳。
否則,他就失去了當初要做史的初心。
王老史閉了閉眼,他若是一死,朝堂上,文和武將勢必要廝殺起來。
到時候就會變文臣和武將之間海深仇。
朝廷也會大,最后大周朝會走向一條路,誰也不知道。
這簡直就是個一石好幾鳥得計策,一定是那些聯合在一起的附屬國想出來的惡毒謀。
王老史想到的,阿瑯同樣想到了。
剛剛讓碧枝和十三離開,就是去查為何差會停留在客棧里。
雍州府衙離這邊并不遠,驛站過去二十里就到了。
如今還是日頭高掛,不存在什麼天黑前趕不到驛站的事發生。
這樣的停留,本就是疑竇重重。
這飯菜,是暗中打翻的,不過是不想王老史吃這麼好的飯菜。
最起碼,在查清楚王老史為何彈劾蕭珩之前,決定讓王老史吃不上。
饞死他!
可真是錯有錯著,竟化解了一場謀。
阿瑯心十分復雜。
在不遠的一間雅座里,里頭的人也險些被氣暈過去。
“怎麼回事?一個菜盤子,都端不穩當!”
他們千方百計,花了那麼多時間,安排了各個看似十分巧合的路障,在收到消息,清河王妃有可能路過雍州時,才把這藥下在飯菜里。
為得就是嫁禍給清河王妃。
如今,面前的一切都白費了?
碧枝收到阿瑯的指令去詢問楚郡王妃母意見時,楚郡王妃正巧也要下樓,聽聞,示意碧枝先下去,隨后就到。
只,楚郡王妃才剛下了樓梯,看到那圍在一起的客人頭接耳,耳邊時不時地飄了幾句話。
拼湊完聽到的消息后,楚郡王妃的臉刷地白了下來。
抓著樓梯欄桿的手,指節發白。
猜你喜歡
-
完結1340 章

梧凰在上
斬靈臺前,眾叛親離,被誣陷的鳳傾羽仙骨被剔,仙根被毀,一身涅盤之力盡數被姐姐所奪。寂滅山巔,她的未婚夫君當著她好姐姐的面,將變成廢人的她打進葬魂淵中。挺過神魂獻祭之苦,挨過毒火淬體之痛,人人厭棄的她卻成了淵底眾老怪們最寵愛的掌上珠,而她卻放棄了安逸生活,選擇了最艱難的復仇之路......
192.8萬字8 14980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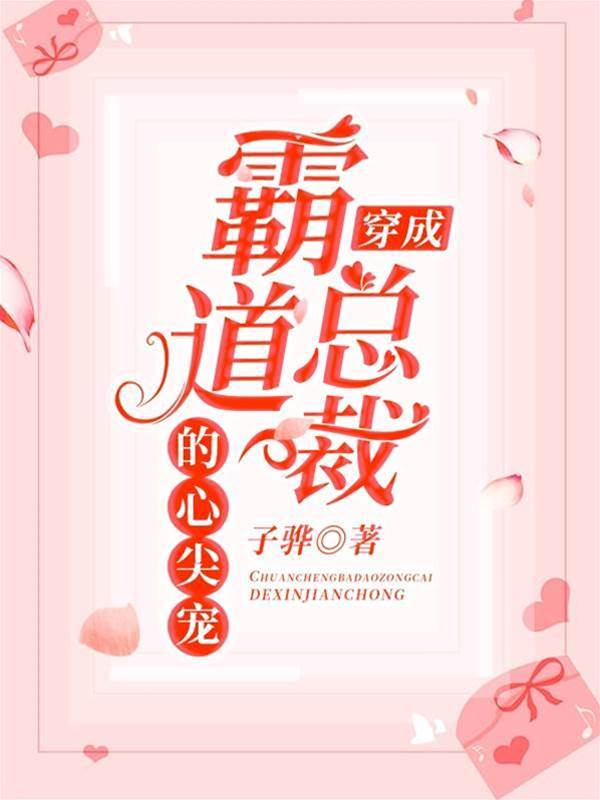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8 -
完結165 章

名門醫妃
韓雪晴穿越到古代,成為寧瑾華的王妃,安然病了,韓雪晴是唯一一個能救她的人,生的希望握在她的手里。不過慶幸的是她曾是一名現代的優秀外科醫生,是一個拿著手術刀混飯吃的她在這里一般的傷病都難不到她,只是這個世界不是那般平靜如水,有人在嫉妒她,有人想讓她死……
44.6萬字8 8301 -
完結179 章

病美人嬌養手冊
南楚攝政王顧宴容操持權柄,殘暴不仁,其兇名市井盛傳。 皇帝爲攝政王選妃之宴上,世家貴女皆人人自危,低眉斂目不願中選。 獨獨鎮國公府裏那位嬌養深閨的病弱幺女,意味不明地抬了抬眼。 謝青綰天生孱弱,卻偏生一副清幽流麗的美貌,怎麼瞧都是懨懨可憐的模樣。 顧宴容奉旨將人迎入了攝政王府,好生供養,卻待這病美人全然沒甚麼心思。 只是他日漸發覺,少女籠煙斂霧的眉眼漂亮,含櫻的脣瓣漂亮,連粉白瑩潤的十指都漂亮得不像話。 某日謝青綰正噙着櫻桃院裏納涼,一貫淡漠的攝政王卻神色晦暗地湊過來。 他連日來看她的目光越發奇怪了。 少女斜倚玉榻,閒閒搖着團扇,不明所以地咬破了那枚櫻桃。 男人意味不明的目光細密地爬過她溼紅的脣瓣,聲色暗啞:“甜麼?”
27.7萬字8.18 58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