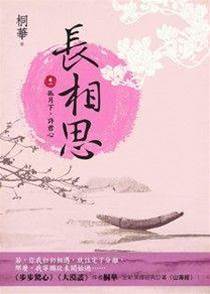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王爺,王妃貌美還克夫》 第579章 那會是什麼?
「那……好啊。」雋喆笑笑,不著痕跡地在他的腰上了一下。
閻子權見他笑,自以為得意,親手給他倒滿了酒,笑著說:「來來,我們喝一碗。」
「干。」雋喆端起酒碗,和他相。
「晚點,我們去……」閻子權又湊過來,約他去青館玩。
那是京中有名的男倌聚集地,原本只是一家酒樓而已,只因酒樓主人有斷袖之好,所以後來變了京中同
最聚會的地方。京中人對此見怪不怪,因為裏面有幾個非常出的男子,所以偶爾也有人去看個熱鬧。
雋喆笑笑,眸子裏殺機閃,「好啊。」
閻子權大喜,一把抓住他的手,神兮兮地說:「雋喆還未識得此道之樂,到時候嘗過了,以後就離不開了。」
雋喆回手,回手,笑道:「你先去,在後巷裏等我,我隨後到。靜小一點,別讓他們知道了,傳我叔叔耳中,大家臉上都難看。」
閻子權抬頭看了看眾人,低聲音說:「好,我在後巷等你。」
雋喆點頭,端起酒碗繼續和人寒喧。
閻子權樂不可吱地出了門,直奔後巷。幾隻烏在牆頭蹲著,惻惻地盯著他看,冰涼的眼神看得他渾不舒服。一陣涼風吹來,他不自地打了個冷戰。
「這小子,怎麼還不來,莫不是耍我?」他不耐煩地跺了跺腳,揮手驅趕那幾隻烏。
一隻白雀飛過來,一張,一顆金珠子落到了他的腳邊。
「嘿,還有金珠子撿……」他大喜,握著金珠子往前看,那白雀往前飛了一段路,又吐了顆金珠子。閻子權趕追上去,自言自語道:「這鳥賊是哪裏的金珠子?」
白雀在巷子裏停停走走,讓他撿了四粒金珠,突然就消失到了大樹茂的樹葉中。
Advertisement
他轉手裏的金珠,樂呵呵地轉,一抬眸,只見雋喆就站在面前,搖著扇子,笑地看著他。
「原來你來了。」他大喜,大步走近他,想拉住他的手。
雋喆眼中狠的一閃,抬扇就敲向他的頭頂,冷冷地說:「去……」
閻子權眼珠子一直,直接倒在地上。
「死狗。」雋喆冷冷地罵了句,一腳踩在他的臉上,狠狠一碾。
「主子。」黑侍從們從暗出來,垂著雙手問安。
「他們還想引我去破解機關,卻不知道我已經留在他們邊了。我已經知道了雙雪樽的樣子,他們找不到漠教,就會用雙雪樽來給小十解毒,到時候我就拿到雙雪樽了。」雋喆慢吞吞地說。
「那為何現在不加重藥量,儘快得手?」隨從好奇地問。
「急什麼,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我要好好玩玩這些人。」雋喆冷笑,低聲說:「他們以為真能一手掌握乾坤,我就讓他們知道,這世間就有人能隨時把他們玩弄於掌之間……」
「對,還要給我們的王報仇恨。」隨從咬牙切齒地說。
「報什麼仇。」雋喆轉過頭,無地說道:「他們死於誰的手,本與我無關,那是他們無能窩囊。我才不會蠢到把什麼國家大義背在上,虛偽!我要的只是我喜歡的東西,不管是寶貝,還是人。」
「主子說得對。」隨從趕說道。
「那丫頭今晚會來看玉匠,我要去陪玩玩。得到的心和人,再把丟掉,一定比殺了的人更有趣。」雋喆笑了起來。
「可是不是和南彥深厚?」隨從猶豫著問。
「那又如何,人的心能有多堅定?」雋喆冷酷地說。
幾人面面相覷,完全不他的心思。
「主子,那我們……」
Advertisement
「把這死狗拖下去。」雋喆低眸看了眼閻子權,狂傲地說:「就掛在皇宮城門之上,我就要看看他們的本事,到底有多大。」
「這……閻晟正在宮中,若是……」有人遲疑地說道。
「廢,你們害怕了?」雋喆眼神一寒,冷冷地質問。
幾人打了個冷戰,趕把閻子權拖起來,飛快地竄進了夜幕深。
雋喆轉過,背著雙手,慢慢走向玉匠住的小院。幾隻烏從牆頭飛起來,不時落到百姓院中,啄食狗盆或者貓碗裏的飯菜,貓貓狗狗卻在一邊,不敢靠近。偶爾有月過了茂的枝葉,落在雋喆的前面,他一腳踩過去,把月碾碎,彷彿碾掉的是他心裏埋藏多年的怒火。
嘎吱……
有扇小門響了幾聲,他飛快扭頭,只見小門裏竄了一條黑狗,看了他一眼,夾著尾逃得飛快。
他冷笑,這些畜牲倒有眼,知道怕死。
在他眼裏,除了金銀珍寶之外,世間萬事萬都是無用的廢。
「主子……」又有一道黑影從高牆飄下,抱牆說道:「有人闖進詭劫宮了。」
「什麼?」他心神一凜,冷冷地問:「何人?」
「應當是傅石沐,不過他未能闖過機關,第三重時就被困住了,現在還在試圖闖關。」
「該死。」雋喆臉龐扭曲,往前走了幾步,扭頭看向東面,小聲說:「重布前三重機關,關閉珍寶宮,等我回去之後再理。」
「不撤嗎?」
「為何要撤,我要帶著雙雪樽回去。」雋喆冷笑,大步往前走。
隨從擰眉,雋喆太過張狂了,這些年雖說未到過敵手,但閻晟和阿九並不是好惹的人。再者傅石沐一人就能闖過三重機關,若再多幾人……後果不堪設想!
Advertisement
雋喆的張狂不僅在於他的為人事上,還在他放置珍寶的事上。他甚至沒有建地下寶庫,就把所有的珍寶放進大宮殿中,隨時可以進去把玩欣賞。
若外人闖進去,很容易就能把他多年搜集來的珍寶搬空!
「不如暫時把珍寶撤進山裏?」隨從跟上前,小聲勸道。
「他們若真有本事,怎麼會這麼久都沒有察覺到我們的存在?若他們真有本事,就不會任由我留在他們的邊了。」雋喆傲氣十足地搖了搖扇子,小聲說:「等著吧,只有一個人會贏,那就是我。」
輕盈的腳步聲落到了城牆上,烏驚飛,一道白影兇猛地撲起來,利爪抓住了兩隻,狠狠摜到了地上。
雋喆飛快閃,躲進暗。白豹豎著長尾,碧幽的眼睛盯著他們藏的方向。
「這是……」
「閻晟的豹子。」雋喆眼神一涼。
「它怎麼找到這裏的,一點靜也沒有。」隨從有些心悸,額頭微微冒汗。
「別出聲。」雋喆悄然扣住暗,渾繃,隨時準備迎擊撲來的豹子。
但此時突然傳來了尖聲,豹子叼起了烏,慢慢退進了影中,然後一躍而起,沿高牆退開。
「怎麼回事?」隨從趕攀上大樹頂端,往尖聲傳來的地方看。
「是前面的勾欄院裏打架。」隨從低頭說道。
「行了,你回去吧。」雋喆快步走出影,大步趕往玉匠家。
小轎停於大院門口,於靡上前去,抓住門上的銅環叩門三聲。
「誰?」裏面傳出懶洋洋的問話。
「求玉的。」於靡大聲說。
「這麼晚了。」大門打開,一個瘦的漢子打著哈欠掃了一眼幾人,側過了聲,嘟囔道:「先進來吧,師傅已經睡下了,我去一聲,若他他不起來,你們就只能明天再來了。」
Advertisement
「多謝。」於靡抱抱拳,三步並兩步跳下臺階,掀開了轎簾,向小十出了手。
小十扶著他的手腕,鑽出轎子,好奇地打量了一眼四周,慢步走進了小院。
「你們要買什麼玉。」漢子打著哈欠問。
「家母大壽,聽聞這裏有玉雀極為靈驗,所以想要送一件玉雀,祈禱家母安寧長壽。因為時間太,所以明兒就得趕回去。」小十聲說道。
「哦,但師傅已有七年不做玉雀了,一來是因為好玉難尋,二來是因為當初玉雀是為了激太後娘娘才做的,後來世人弄得變了味道,師傅怒了,也就不做了。」漢
子一面解釋,一面把幾人引到廳中坐下。
側面布簾打開,又走出一名婦人,端著沏好的茶,放到幾人面前。
「師傅前幾日做了一件玉壽桃,若獻給令堂大人,令堂一定高興。我去師傅一聲,看他有沒有神鵰上令堂的名字。」婦人笑地說道。
「玉不是尋常玉嗎?」小十好奇地問。
「一般的玉確實尋常,但師傅頭一批用來做玉雀的那幾塊料卻不一般。」漢子坐下,神兮兮地說道。
「哦?」小十很驚訝,卷宗上沒有一寫明過玉雀的不同之。
「那幾塊料是大元皇宮裏流落出來的。」漢子脖子往前,小聲說:「是當年用來滋養雙雪樽的寶貝。你們可曾聽說過雙雪樽?太上皇和太后都是而立之年,卻依然是青春容貌,就是因為這雙雪樽的緣故。不過,師傅不許聲張,知道的人很。現在反正都沒了,我才敢和你們說說。」
「原來這樣。」小十秀眉擰,輕輕點頭,難怪被走了。想必那人也知道這玉的來歷!
「那師傅在做玉的時候,還有誰知道這玉的來歷?」於靡追問。
「我還有一個師弟,早些年死了。」漢子輕嘆,惋惜地說:「是去采玉的時候失、、、足摔死的。」
「是啊……漢子一臉哀,輕聲說:「不然,依他的靈氣,今日就應當超過師傅。」
「是有經驗的玉匠,應當常在山中行走,尋找玉……」小十若有所思地起,來回踱步,小聲說:「只怕不是失足……」
「那會是什麼?」漢子驚訝地問。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侯府真千金她重生了
重回十年前的江善(周溪亭),站在前往京城的船只上,目光冷淡而平靜。她是被人惡意調換的文陽侯府的真千金,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里的容妃娘娘是她姨母,溫潤如玉的二皇子表哥是太子之位的熱門人選,出生既頂端的她本該萬千寵愛、榮華富貴且波瀾不驚地過完一生。但十六年前的一場人為意外,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等她得知身世,回到文陽侯府,取代她身份地位的江瓊,已經成為父母的掌心寶。前世她豬油蒙了心,一心爭奪那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論是父母的寵愛,還是江瓊身份高貴的未婚夫,這一世,她只想快快活活地活一...
107.9萬字8 330763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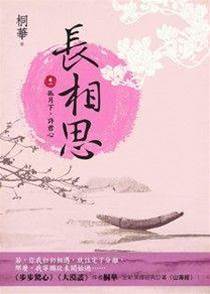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