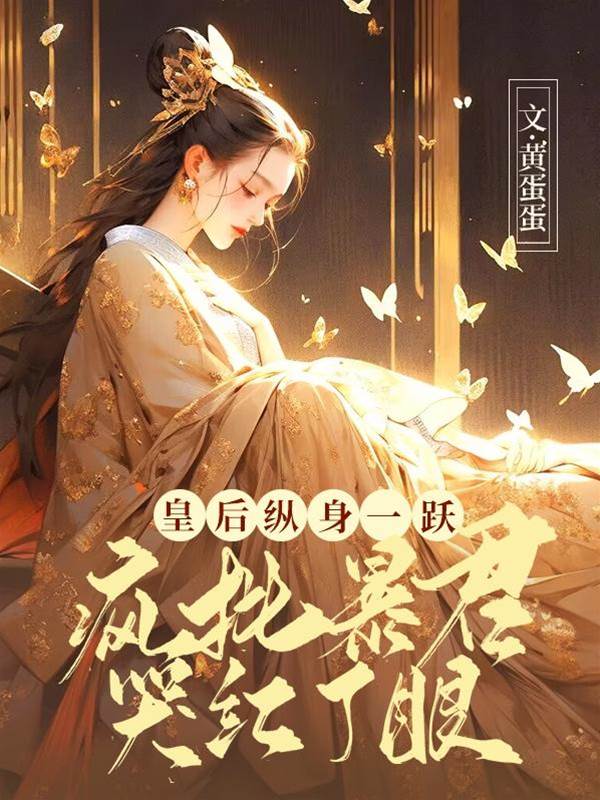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通房寵》 第 35 章
阿梨答應婚事后,秦二郎再未心什麼,只安心養胎,其余的事,自有他去置。
沒幾日,秦三娘便曉得了,氣急敗壞地來,同阿梨抱怨,“二哥說你們的婚事一切從簡,家中難得熱鬧一回,二哥這人真是的。”
阿梨只輕輕地笑,并不說話,低頭著手里的百戶,這裳都快好了。
忽的,秦三娘抱住了,極輕極輕說了句,“阿梨,謝謝你。”
阿梨愣了片刻,很快明白過來,以為秦二哥用什麼法子騙過了三娘,三娘以為他們的婚事是真的。但實際上,三娘只是裝傻,什麼都知道。
也是,經營鋪子的秦掌柜,在外明無比,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就被人哄騙過去。
阿梨也沒開口,只淺淺笑了一下。
天漸漸暖和起來了,一日,秦懷來了這里,帶回了一個消息。
大抵是天暖和起來的緣故,秦懷的氣好了不,從前毫無的,也有了氣。
阿梨見了他,便照舊如從前那樣喚他“秦二哥”。
秦懷頷首,坐下后,便道,“先前林家來鬧事的人,我已經查出來,是縣中主簿。大抵是見你孤一人,又有個鋪子,便了心思。此人惡事做盡,侵占良田,搶占民,卻因做得蔽,無人知曉。過些日子,京城會派新知州來,到時候我會想法子將曹主簿的惡行,遞到新知州面前。你大概不知道,去年蘇州知州犯了事,新知州是陛下派來整頓蘇州場的……”
阿梨原還認認真真聽著,后來便有些走神。
直到秦懷察覺,停了下來,阿梨才回過神,抬眼著秦懷。
秦懷以為對場之事不興趣,便不再說那些,只道,“日后你不用怕,林家人不會再來鬧事了。”
Advertisement
阿梨抿出個溫的笑,點頭道,“謝謝你,秦二哥。”
秦懷卻只淡道,“無妨。原就是我該做的。”
阿梨卻搖頭,“不是你該做的。這世上沒有誰應該幫誰,你和三娘幫我許多,若沒有你們,我不可能在蘇州安頓下來。”
秦懷聞言,怔了一下,腦海中閃過另一張臉,那個小姑娘也和他說過類似的話,但同阿梨不一樣,是驕縱跋扈、生機的。
小姑娘落了水,他救了,小姑娘凍得哆哆嗦嗦的,還倔強道,“你什麼名字,你救了我,我讓我爹爹給你銀子。我爹爹可是長史,最疼我了!”
秦懷記得,自己當時只說,“不用了”,便那小姑娘回去了。
小姑娘活蹦跳,第二日還來尋他,他卻夜里就病倒了,那時候三娘已經出嫁,他不想打攪三娘的生活,便只一個人熬著。
小姑娘賴著不肯走,日日給他熬藥,也不知如何從家中溜出來的,想必,還是吃了不苦頭的。
只是,一向倔強,便是苦,也絕不肯低頭。連嫁人也是,明明是個生慣養的小娘子,卻敢忤逆長輩,絕食、投井、上吊……無所及其不用。
其實,他秦懷哪里配得上那樣的深,那個驕縱的小娘子,合該有個能陪一輩子的夫君,而不是和他這麼個短命鬼糾纏。
他能給什麼呢?
連最起碼的陪伴都不能。
現在,應該有孩子了吧?不知道是兒子還是兒,若是兒,會不會和生得很像?
秦懷不知道,是不是時日無多的緣故,他最近總會回憶起從前的事,尤其是那個小姑娘。
秦懷微微搖了搖頭,拋開那些念頭,同阿梨說了句,便打算回去了。
Advertisement
在親之前,他想將曹主簿的事解決了。
.
關于婚事,秦懷說要一切從簡,阿梨自是沒什麼意見,連日子都未算,只在秦府外放了鞭炮,秦懷去了一趟府,簽了字,婚事便算塵埃落定了。
兩人雖了名義上的夫妻,但實際上,依舊同原來一樣,阿梨也從未喊過秦懷相公,從來都是一句“二哥”。
秦懷倒是改了口,但也只是客客氣氣一句“阿梨”。
兩人似乎心有靈犀般,從不主親近對方。
漸漸地,了夏,書肆的生意也愈發好了,但阿梨卻不大去書肆了。
倒不是旁的,蓋因現在不方便出門了,先前孕態不顯,自是不必躲躲藏藏,如今肚子高高隆起,自然不方便出門了。
阿梨日日待在家里,白日里便折騰吃的,如今口味變重了,吃酸的辣的,就是不吃清淡的。
這可苦了秦懷,秦懷從小便吃得清淡,但他也能忍,但凡阿梨問他,他便說很合口味,阿梨才不會算命,自然猜不出他在裝。
日子安安穩穩地了秋,阿梨生產的日子,近在眼前了。
自己倒不是很在意,仍舊在家里溜達,但秦家兄妹卻一個比一個張,秦三娘恨不得把胭脂鋪的事都丟了,搬回家里住。
秦懷也一改先前日日待在書房的習慣,白日里會下意識看一看阿梨的況,若半個時辰沒見到,就會起來尋。
直到秋的第二月,孩子終于在大家的期待中,到來了。
是個模樣很好的小姑娘,阿梨生時十分順利,沒怎的折騰,估計孩子是個知道疼人的,下午的時候發的,天還沒黑,便落地了。
小姑娘白白凈凈的,小臉圓圓的,眼睛眉和阿梨生得很像。
Advertisement
秦三娘抱著侄不撒手,心肝寶貝的一直喊。還是秦懷嫌吵鬧,趕出去,秦三娘才不舍將孩子還給阿梨。
兄妹倆似乎是出去了,阿梨輕輕側過頭,溫的目落在自家兒臉上。
從前便不大明白,薛母怎麼會恨不得將一切都捧給薛蛟,如今自己做了娘,才明白了那種覺。
那麼小小的團子,是你費勁千辛萬苦生出來的,上流著和你一樣的,從牙牙學語,到蹣跚學步,再到長大人。
溶于水,真的不是上的一句話。
阿梨輕輕將臉在兒的小臉邊,輕輕蹭了蹭,小聲道,“娘不會讓你吃苦的。”
這時,秦懷進來了。
半年相下來,阿梨早將他視作兄長,便喚他過來,道,“二哥,你抱抱吧。”
秦懷應了聲,小心翼翼將襁褓抱進懷里,小孩子骨頭很,秦懷連力氣都不敢用,但又怕抱得松了,將孩子摔了,一小會兒,便額上出了層薄薄的汗。
阿梨看得好笑,不忍心再為難他。
秦懷很快將孩子還給阿梨,問,“給孩子取名了嗎?”
阿梨搖搖頭,“還沒有,二哥給取吧。我怕取不好。”
秦懷應下,回去翻了一晚上的書,第二日便過來,道,“瑜吧。上善若水,取河之意。玉無瑕,是為瑜。這名字可好?”
阿梨念了幾遍,點頭,“自然很好,多謝二哥。小名我想好了,便歲歲。”
秦懷便笑了,“歲歲平安,你倒是會取。”
阿梨輕輕笑著道,“我就盼歲歲平安,這便夠了。”
秦懷沒有自己的孩子,便把歲歲當自己的孩子,他原也不大出門,便日日親自照顧歲歲。
倒是阿梨,了冬,便一頭扎進書肆的生意了,斗志昂揚。
Advertisement
如今是有兒的人了,自然不能像從前那樣倦懶,得給閨攢下一份家業來。
有的時候,秦二哥會帶著歲歲過來找,歲歲黏著阿梨,一天不見,便會哭。
阿梨在這方面倒是個嚴母,反倒秦二哥是個慈父,歲歲一哭,便立即抱起來哄,哄不好,便抱過來尋阿梨,阿梨抱抱。
以至于明明沒有緣關系,歲歲卻很喜歡秦爹爹,父倆親如一人。
這一日,阿梨出門辦事。
最近有一套書,是蘇閣老的大作,在京中賣得極好,只是蘇州還沒有。有不人來書肆問過,阿梨如今對生意十分上心,便記在心里了。
聽說城西有個印書坊,很有些本事,從京中弄來了雕版,阿梨便尋了個日子,帶著劉嫂去和書坊坊主談生意。
如今謹慎許多,每次出門都會記得戴上帷帽,連頭發都不一點,生怕再招惹了什麼人。
同書坊坊主談妥了生意,同劉嫂便回書肆,還未進門,就見外面站著幾個侍衛模樣的人。
阿梨一愣,走上前去,輕輕朝那侍衛道,“我是這家書肆的掌柜。”
侍衛沒攔,客客氣氣道,“是我家大人在里面,掌柜的直接進便是。”
阿梨略略松了口氣,心道是哪位大人,這樣大的陣仗。
心這般想著,阿梨朝劉嫂一點頭,兩人一前一后踏進屋子。
阿梨走進去后,便見到兩人站在柜臺前,似乎在挑選硯臺。
負責看鋪子的小伙計一見到阿梨,便喜出外道,“掌柜,您總算是回來啦。”
他這一聲“掌柜”,令正微微低頭看硯臺的兩人同時抬了頭,其中一個側過頭來看阿梨,然后笑著道,“原來是掌柜的回來了,你家這小伙計未免膽子太小了些,我不過問他這硯臺是如何做的,他便支支吾吾不敢說話了。”
那人說罷,便等著阿梨回話。
阿梨卻結結實實愣在了那里,顧不上回答那人的話,震驚的目穿過帷帽垂下的白紗,落在站在側的李玄上。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未見,李玄似乎高了些,人清瘦了些,長而立,姿拔,穿一青云錦的錦袍,他微微垂著眉眼,面清冷,像是對邊發生的事毫不在意,有一種濃郁的疏離。
深吸一口氣,下意識屏住了呼吸,不敢開口說話。
李玄怎麼會來蘇州?
來辦案?
還是……來找?
猜你喜歡
-
完結752 章
太後孃娘今天洗白了嗎
(雙潔、甜寵、1v1)沈紅纓玩遊戲氪金成癮,卻不曾想穿到了自己玩的古風養崽小遊戲裡……成了小皇帝崽兒的惡毒繼母當朝太後,十八歲的太後實屬有點牛批,上有忠國公當我爹,下邊宰輔丞相都是自家叔伯,後頭還站了個定北大將軍是我外公!氪金大佬穿成手掌天下權的惡毒太後,人人都以為太後要謀朝篡位,但是沈紅纓隻想給自己洗白設定好好養崽,誰曾想竟引得宗室藩王癡情追隨,忠臣良將甘拜裙下;莫慌,我還能洗!容恒:“太後孃娘要洗何物?”沈紅纓:“……洗鴛鴦浴?”【小劇場片段】人人都說國師大人聖潔禁慾不可侵犯。卻見太後孃娘勾著國師大人的下巴滿目皆是笑意道:“真漂亮,想要。”容恒:……世人咒罵太後惡毒,仰仗權勢為所欲為。後來,燭火床榻間那人前聖潔禁慾的國師大人,如困獸般將她壓入牆角啞聲哀求:“既是想要,為何要逃。”【禁慾聖潔高嶺之花的國師x勢要把國師撩到腿軟的太後】
66.3萬字8 61973 -
完結555 章

新婚日,醫妃她炸翻王府!
【醫妃+雙強+替嫁+美食】一朝穿越成替嫁王妃,公雞拜堂?夫君嫌棄?小妾上門找茬?不怕,她用精湛的醫術虐渣,順道用廚藝俘獲夫君芳心。“娘子,今晚我想進屋睡。”“不要臉!”
102.3萬字8 9290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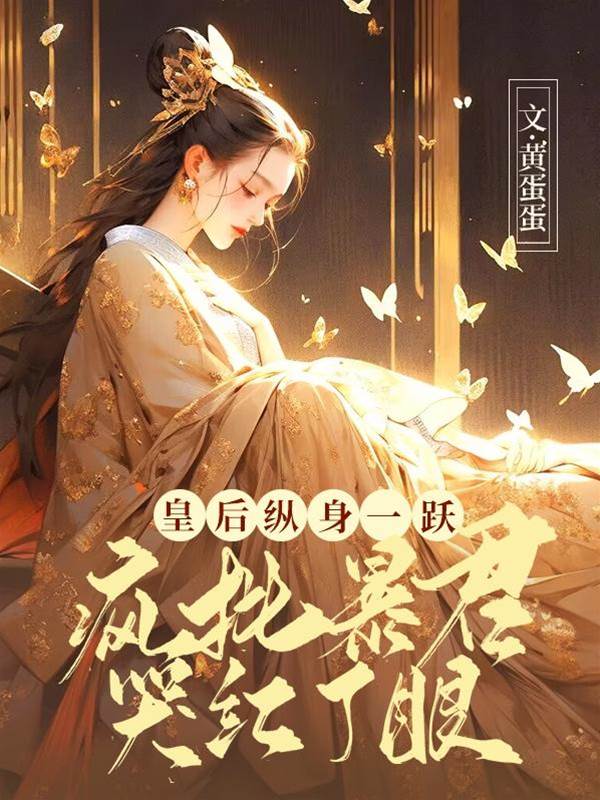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296 章

寵婢無雙/儲媚色
無雙十五歲便跟了龔拓,伺候着他從青蔥少年到如今的翩翩郎君。 外人都道她得了伯府世子寵愛,日子舒坦,不必起早貪黑的勞作。 只有無雙知曉那份小心翼翼,生怕踏錯一步。那份所謂的寵愛也是淺淺淡淡,龔拓的眼裏,她始終是個伺候人的奴婢。 韶華易逝,她不想這樣熬到白頭,琢磨着攢些錢出府,過平常日子,找個能接受自己的老實男人。 將這想法委婉提與龔拓,他淡淡一笑,並不迴應。 他的無雙自來溫順乖巧,如今這樣小心,不過是因爲家中爲他議親,她生出了些不安的小心思,太在意他罷了。好吃好住的,他不信她會走。 出使番邦前,他差人往她房裏送了不少東西,也算安撫。 半載之後,龔拓回來卻發現房中已空,家人告知,無雙已被人贖身帶走。 成親日,無雙一身火紅嫁衣站在空蕩蕩的喜堂,沒有賓客,更沒有她未來夫婿。 主座男人手捧一盞茶,丰神如玉一如往昔,淡淡望着她。 她雙腳忍不住後退,因爲氣恨而雙眼泛紅:世子,奴已經是自由身。 龔拓盯着那張嬌豔臉蛋兒,還記着手上捏住那截細腰的觸感,聞言氣笑:是嗎? 他養她這麼些年,出落成如今的模樣,可不是爲了便宜別人。
45.5萬字8.18 558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