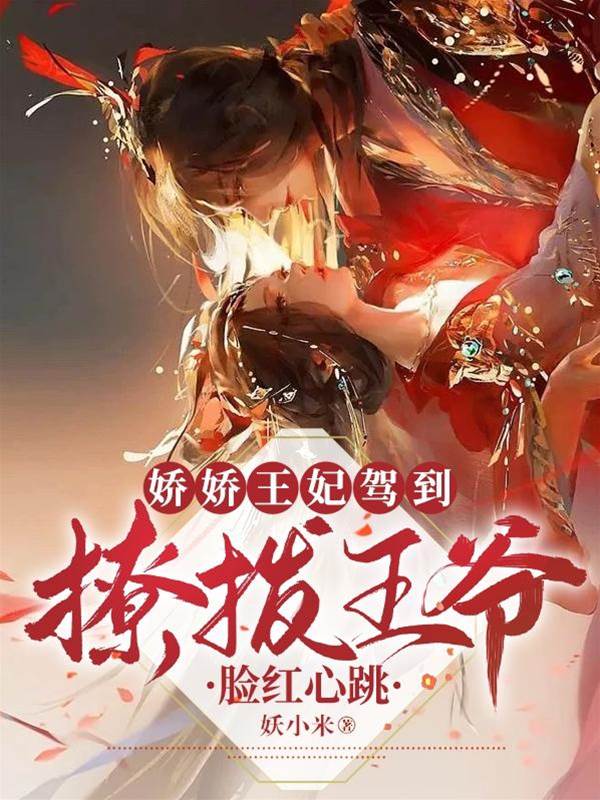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權傾裙下》 129. 尾聲五
趙嫣在華過了半個月清凈日子。
又至雨水明亮的盛夏,歸京時正值七月初,趙嫣順帶與聞人藺去了一趟西山,將墳冢上荒蕪的雜草一一踏平清理,焚香祭奠。
“趙衍,兩歲生辰吉樂。”
趙嫣輕輕拂去青碑上的楓葉,換上一小束新摘的野花。
……
趙嫣回宮的第一件事,便是召集吏、禮二部完善秋闈鄉試的審查及擢選之制,由表及里,為來年春闈和殿試擢選寒門,平衡朝堂做準備。
秋闈后,王裕等革新派在趙嫣的授意下,開始著手推行子學堂。
學自去年開始便有了,只不過那時收留的皆是戰歿將士的孤或妹,朝臣士子并無意見,但若要在京畿乃至整個大玄推廣子讀書之策,使男平等、尊卑無界,那些自恃清高的保守派自然坐不住了。
含明殿,朝中兩派人馬又開始了長達月余的舌辯。
“若子都去拋頭面、讀書游玩去了,何人執掌中饋?何人相夫教子?若人人都不想安居后宅生兒育,人丁單薄,長此以往,我大玄恐將陷無兵應戰的窘境哪!”
說話的是國子監祭酒江卿甫,六十歲的老者以額頓地,痛心疾首地勸諫,“請長公主殿下思!”
“這不是請您老來商議麼,江祭酒起來說話。”
趙嫣不聲笑笑,示意李浮向前攙扶。
江祭酒作勢抹了抹濁淚,巍巍站起。
一旁的柳白微適時開口道:“教養孩子,不一定非得是子;上陣殺敵,亦不一定非得是男-丁,祭酒大人的格局還是小了些。”
“潁川郡王未有實權,站在朝廷議事之未免太過僭越。”
“國之大事,人皆有責,我食君之祿,更當為君分憂,如何說不得?”
與江祭酒一列的年輕男子甩了甩袖子,哼道:“我看是黑白顛倒,混,國將不國!”
Advertisement
柳白微揪住其破綻,挑眉道:“羅侍郎,你這話罵天罵地大不敬,史臺趕記上,參他一參!”
姓羅的年輕男子自知緒激下失言,面霎時醬紫,匆忙跪拜以表忠心:“臣只是就事論事,絕無半點對長公主不敬之意,還請長公主明鑒!”
“羅侍郎此言,按例是要褫杖責二十,以正朝綱。”
趙嫣虛闔雙目,見羅侍郎額角滲出了冷汗,這才慢悠悠笑道,“念在羅侍郎也是衷心為國,杖責便免了,罰奉一月,回家面壁自省吧。”
羅侍郎松了口氣,只得俯首稱“是”。
出了含明殿,膠著的氣氛瞬間松懈。
柳白微與王裕向前,笑嘻嘻道:“羅侍郎,永興街開了家回紇羊店,一起去吃點?”
羅侍郎同江祭酒回了一禮,笑嘆道:“郡王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著如何套下的話吧?下次下次,今日容下回去想想,明日如何駁你。”
柳白微笑得張揚,向前道:“別這麼記仇嘛,都是為了大玄!下了朝,該吃吃,該喝喝,走走走!今日我請客!”
說罷一把勾住羅侍郎的肩,回首朝有些斂的青年道:“王裕,一起來!”
趙嫣站在含明殿前,看著朝堂上針鋒對決的這兩撥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地走遠。
聞人藺負手而來,順著的視線去,沉聲笑道:“殿下馭臣,越來越得心應手了。”
“也有太傅的功勞。”
趙嫣私底下仍會戲謔喚他為太傅,悄悄靠近以肩了他的手臂,“你不覺得如今的朝局很有意思嗎?朝堂上兩撥人吵歸吵,但一下了朝,仍是往來談笑、相知相敬的同僚。不會像先帝、魏琰之流那般,因利益不同而大肆排殺異己。”
所謂君子和而不同1,大抵如此。
Advertisement
因有年死于濁世,所以才致力于拂開一片清明。
聞人藺著明亮的雙眸,頷首贊道:“嫣嫣真厲害。”
“敷衍。”
趙嫣瞥了眼四周垂首而立的宮侍,上嫌棄,可眼底的笑意怎麼也掩蓋不住,悄聲道,“不過江祭酒倒是提醒我了,本朝一向是子十五及笄便許配婚嫁,若子也能十年寒窗苦讀,知書明理,則婚育必定推遲。我希無論男,都可有選擇主主外的自由,但大玄朝的兵力不能疲,所以我想,能不能讓適當增加兵,讓有能力的子也能上戰場。此事你在行,還得肅王殿下幫襯些。”
聞人藺拖長音調“哦”了聲,笑著轉進了殿,慢條斯理拉了把椅子坐下:“那要看殿下,如何請求本王了。”
趙嫣一噎,跟著進去,雙手撐在書案上看他。
“聞人妖妃,你別太得寸進尺了!”
“不可以嗎。”
聞人藺屈指抵著額角,人眸噙笑,毫無自省之意,“殿下一回來就忙于政務,都多久沒陪陪未婚夫了。本王夜間多留一刻,還要被司寢催著趕走。”
趙嫣忽而就有些理解,史書中那些專寵一人的昏君行徑了。
但是個有定力的攝政長公主,絕不能屈服于小小男的。
“過幾日吧。”
揚著眼尾傾撐桌,“過幾日我回東宮去住。”
“過幾日?”聞人藺漆眸漸深。
“明日,今天真不行。”
趙嫣不自覺咽了咽嗓子,直堅定道,“我要去閱奏折了,勿擾。”
“好啊。”
聞人藺反傾靠近,低聲道,“殿下閱奏折,臣閱殿下。”
這話!
想起那段荒唐的回憶,趙嫣窘得抓起案幾上的朱筆朝聞人藺擲去。
聞人藺輕飄飄接過,朱筆在指間利落轉了個花,得逞般肆意低笑起來。
Advertisement
翌日,聞人藺騰出了一整天的時間,陪趙嫣理完奏折,就帶乘馬車出了宮。
九月桂子飄香,各應季瓜果載道。
“怎麼突然想著,帶我出宮玩兒?”
街上行人往來,貨郎吆喝不絕,趙嫣戴著帷帽,開一角輕紗,“我還以為……”
聞人藺似是看穿的想法,揚反問:“以為什麼?”
趙嫣輕咳一聲。
還以為,聞人藺要拉著試一試新煉的那什麼藥油。
“雖然殿下有些失,但本王腦子里也并非全然是那事。”
聞人藺面平靜,一正氣的樣子,“怕殿下久居宮中不出,遲早憋蔫了,這才帶殿下出來散散心。”
趙嫣作勢嚶嚀一聲。
聞人藺眼尾一跳,睨目道:“又作甚?”
“本宮好!有夫如此,妻復何求?”
趙嫣單手著帷帽垂紗,笑說。
聞人藺面沒,可線卻明顯上揚了幾個度,抬手了的后頸道:“去看看有無喜歡的地段或宅邸。”
趙嫣意外道:“宅邸?是要選新的學館址嗎?”
聞人藺似是微微一怔,見滿眼放,倒也沒否認。
想到什麼,趙嫣又小聲道:“這錢沒法從國庫中出,加之年初減免了多地賦稅,帑中的銀錢尚未攢夠。我原想……推到明年春再做決定的。”
聞人藺笑了聲,悠緩道:“只管先看,從殿下的聘禮中扣。”
“真的啊?”
趙嫣追了上去,眉眼如月,“學館地址我想購置在大寧坊,地段便宜,也清凈。”
“還有呢?”
“還有?”
“若讓殿下選私宅,喜歡何?”
“那必定是永昌坊,離東宮和太極宮都很近。”
趙嫣負著雙手興沖沖計劃,末了反應過來,“你問這個作甚?”
“無甚。”聞人藺淡然道,眸中淺笑莫測。
Advertisement
“騙人,肯定有什麼!”
趙嫣狐疑,然而不管如何追問,聞人藺都只是悠然信步的樣子,不愿開口。
趙嫣最終還是將學館的地址選在了明德館的隔壁,一則此正巧有幾畝荒廢已久的宅院租售,價錢也不算貴;二則明德館這個地方,對趙嫣和所有求學不易的人來說皆有重要意義。
修繕,改造,聘請學夫子,擢選適齡有才的……前前后后籌備了大半年,京中第一座正式的學館試著推行。
第一批擢選的學生不多,滿打滿算不到六十人。
其中一部分為朝中革新派吏家中未出閣的眷,代表家族的政治立場以作則而來。一部分是憑真才實學錄用的小才,還有數為京畿外小門小戶家慕名而來的子,想借學館這個跳板尋個乘龍快婿……
學初試,刷掉一半渾水魚的,最終留下來的不過十二人。
但趙嫣已然很滿意。
永平二年,八月。
宮中一年一度的經筵日講開設,由新擢的戶部尚書周及主持。與此同時,學館亦是正式啟學。
學生們的儒服是趙嫣親手改良的,淡藍白底的大袖儒服,配禮節飄帶、玉飾和香囊,行翩翩,頗有雅風。
學生們或含蓄,或開朗,但拜孔圣人像時,皆是一樣的知禮認真。
一墻之隔的明德館,幾個年輕氣盛的儒生聽著隔壁清脆的音,既新奇又不太茍同。
其中一個哂笑道:“子能學個什麼名堂出來?只怕是來此攀龍附,尋覓佳婿來了。”
另一人也隨之附和:“就是就是!張兄,我看你還是離遠些,免得被哪個小娘子看中,平白玷污了這功名。”
隔壁的誦書聲有一瞬的停滯。
繼而踢踏輕快的腳步聲靠近。
墻下,有個脆生生的嗓音應道:“隔壁的人也太不要臉了些,說得我們看得上爾等似的。”
“就是呀!”
另一個音道,“來這里的子都不容易,自當勤苦勉勵。即便與你們同一館,也只會想著如何在讀書治世上將你們打敗,書文瀚海,古今圣賢,當窮一生求之,哪一樣不比你們強?”
“可不是這樣嗎!凡是見著子,就以為是奔著他而來,未免太自以為是了些。”
“某些男子哪,就知道靠束縛子來獲取自信,真是可憐。諸位同儕別和這種人浪費口舌,咱們繼續溫書。”
方才嚼舌頭的那幾個年輕人頓時得面紅耳赤,也不敢反駁,道了聲“好男不跟斗”,便兩兩回書舍苦讀去了,勁頭比平日更足,像是要找回面子似的。
琴樓之上,趙嫣坐觀高,將一切收歸眼底。
“聞人淵,我忽而有個主意。”
眼眸一瞇,扯了扯旁聞人藺玄的袖道,“你說若是定期讓明德館和學館聯合考校詩文經論,比評出一二甲張榜表彰,會如何?”
那只怕是雙方鉚足了勁地比拼,有得好戲看了。
聞人藺手搭著雕欄,頷首點評:“并駕齊驅,必能日行千里。殿下這招角逐之計用得不錯。”
“我覺得可行。”
趙嫣眼眸越發清亮,笑道,“說不定不久的將來,這里真能走出不夫子、宰相呢。到那時,必是八方來賀,萬象包容。”
聞人藺想了想那畫面,倒也不錯。
“殿下又有得忙了。”
聞人藺順著牽拉袖的手往下,與五指扣。
“這不,有太傅在嘛。”
趙嫣毫無后顧之憂,笑跟著聞人藺下了樓。
聞人藺睨目,輕輕勾了勾的掌心。
趙嫣五指一蜷,不甘心地勾了回去。
兩人竟像個孩一樣,借著袖袍的遮掩,悄悄用手指打架。
吉日吉時,街上正有送親的隊伍經過。
漂亮的嫣紅花轎,垂幔輕飄,手持卻扇的妙齡新婦朦朧可見,圍觀的群眾笑著掌相迎。
幾個散課出來氣的學生手拉著手,墊著腳尖在人群中觀看,贊嘆道:“快看!好漂亮!”
轎中的新婦亦是從卻扇后悄悄瞥目,向那群自由自在的儒服投去艷羨的目。
在這個人迭涌的岔口,們皆是選擇了各自的道路,一往無前。
“嫣嫣。”
上車前,聞人藺喚道。
“嗯?”趙嫣提踏在腳凳上,回首看他。
今日正好,氣氛也正好。
聞人藺勾住的手指,濃的眼睫半闔,語氣繾綣低沉得像是經過千萬次深思慮。
“我們親吧。”
他說,“組建一個,我們自己的家。”
秋風卷過,送嫁隊伍灑落的彩紙翩然飛舞。
趙嫣忽而明白,去年聞人藺問有無心儀的私宅地段時,那藏匿眸中的未盡之意是什麼。
行于深淵的人終于得以窺見天,說他,想有個自己的家。
猜你喜歡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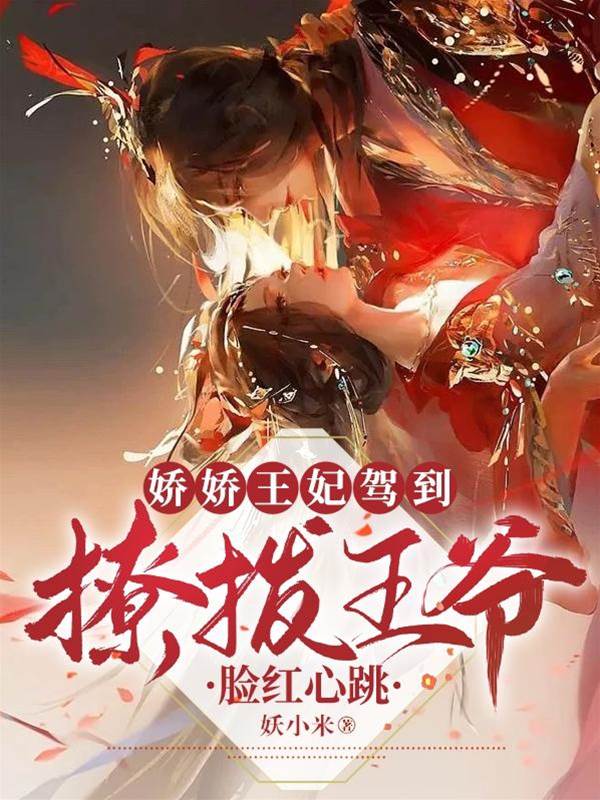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 100528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268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