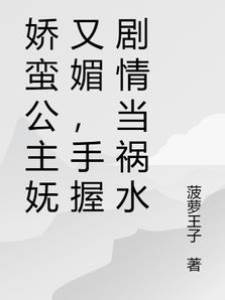《霸王與嬌花》 45
沈令蓁翻了個簡單的“三條”,繃著繩子把手擱到他眼下:“喏,郎君來吧。”
霍留行嗤笑一聲,三兩下翻了個“方叉”給。
“張飛穿針,中有細,看來郎君還是有兩下子的。”沈令蓁一面夸著他,一面湊上前去,手指靈巧翻飛,挑出個“田地”來。
霍留行垂著眼將線絡掃了一遍,抬手便是一個“棋盤”:“嗯嗯嗯嗯嗯嗯嗯?”——來點難的行不行?
“那我真格了哦。”沈令蓁想了想,勾著指頭來回穿梭幾下,輕輕巧巧翻出個“小方凳”。
之前幾個圖案都是一個面,這回卻有了形,霍留行低下頭,從下往上看了看,比比手勢:“嗯嗯嗯嗯。”——手抬高點。
沈令蓁配合著抬高,見他細細看了一會兒,似是瞧出了門道,開始手。
好言相勸:“郎君盲目出手,小心把繩翻散了。”
霍留行停下作,抬起眼瞥。
“郎君看仔細些,到底對不對?”
霍留行眉頭一皺,觀了半天,輕輕敲一個板栗:“嗯嗯?”——詐我?
沈令蓁被他敲得“哎喲”一聲,苦于騰不出手捂腦門,怨懟地看著他,見他有竹地要來翻繩,一氣之下把手藏到了腰后,不給他。
霍留行手去奪,被躲開,“嘖”出一聲來,朝勾勾手指:“嗯嗯嗯嗯嗯。”——別我。
“郎君已經了!”
霍留行心說他也沒用力啊,看腦門當真紅了一片,笑樂了,一手摁住后腦勺,一手給額頭,了幾下:“嗯嗯嗯?”——好了吧?
沈令蓁不不愿地出花繩來。
霍留行手指翻了個“花盆”,挑眉看著,滿臉“小人得志”的喜。
Advertisement
“郎君別高興得太早,厲害的還在后頭呢。”說著,十指全,穿、勾、挑、捻,最后一繃,編出一只“蜻蜓”來。
霍留行看噎,打算捋袖子的時候發現自己上并沒有袖子,只得沉住氣端坐著,待小半柱香時辰過去,在沈令蓁數次“手都酸啦”的催促下,才終于靈一現,不料這下激越太過,一使勁“蹭”一下直接把繩結扯斷了。
沈令蓁瞠目看著他,隨即拍手笑道:“郎君輸了!”
霍留行氣得說不出話來。
當然,不氣也說不出。
“嗯嗯嗯!”——這不算!
“怎麼不算?若人人都像郎君這樣,翻不出便扯斷繩子,豈不永遠分不出輸贏?”
“嗯嗯嗯嗯!”——我翻得出!
沈令蓁搖著頭不同意。
霍留行點點頭:“嗯,嗯嗯嗯,嗯嗯嗯嗯!”——行,算你贏,再來一次!
沈令蓁被他小孩似的模樣逗笑:“剛剛是誰不肯跟我玩的?”
霍留行坦然地指指自己的鼻子:“嗯嗯嗯,嗯嗯嗯?”——就是我,怎麼著?
沈令蓁看著生生被他扯兩截的繩子,皺皺鼻子:“可我就找著這麼一細繩。”
他拿起稍長的一截,打了個結,示意這不就完了。
“繩子短了,對郎君這大手來說就難了。”提醒他。
“嗯嗯嗯嗯,嗯。”——廢什麼話,來。
沈令蓁只好陪他接著玩。
幾下來,霍留行似乎找著了竅門,換卡在了一把“茶壺”上。
沈令蓁一時找不著思路,柳眉擰個結,歪著腦袋打量他手中的線絡,不知不覺間越湊越前。
霍留行默不作聲地把手往后退一寸。
一心一眼都在繩上,毫無所覺地更進一寸。
一退一進幾個來回,無意識地挪離了凳面,重心不穩之下整個人空懸著朝前栽去。
Advertisement
霍留行上藥膏已經收干,手一松接住,玉溫香捧個滿懷,低低笑起來。
沈令蓁的臉頰著他的膛,耳朵被他腔傳出的震磨得又又麻。
推搡著他爬起來:“你耍賴!”
霍留行不贊同地道:“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翻不出就投懷送抱,明明是你耍賴。
沈令蓁皺皺眉:“郎君嗚哩哇哩地,說什麼呢?”
霍留行放慢速度,重新“嗯”了一遍。
搖頭:“我還是沒聽懂。”
他耐著子再“嗯”。
的表更加困:“郎君再說一次?”
霍留行反應過來,一怒之下站起來。
沈令蓁慌忙逃竄,卻被他三兩步追上,抓了過去。
“嗯嗯嗯?”——耍我呢?
“我沒有,我真沒聽明白!”
說著“沒有”,臉上得逞的笑意卻了馬腳,霍留行又要,手一抬起,看這一就紅的,得哪兒都不好下手,頓了頓,改去撓腰肢。
沈令蓁被撓得又是笑,又想哭,一路閃躲著倒進床榻,歪七扭八地討饒道:“郎君饒……饒了我,我不耍你了!”
霍留行這才停下手,氣勢洶洶俯視著,這一眼,卻看見因為掙扎而變得紅的臉頰,還有大敞襟下出的。
沈令蓁見他霎時笑意全收,愣道:“郎君怎麼了?”
霍留行回過神,搖搖頭,指指脯的位置。
低下頭,立刻紅了臉,手忙腳地把散的襟掩好。
屋子里靜默下來,霍留行低咳一聲,也低咳一聲,咳完又聽他再咳一聲。
最后還是沈令蓁先若無其事地道:“啊,剛才那局,應該還是郎君輸了吧?”
霍留行正了正,揚眉:這是什麼道理?
Advertisement
“繩是在郎君手中散開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我不松繩,讓你摔著?
點點頭,理直氣壯:“也不是不可以。”
他能摔了嗎?小無賴。
霍留行也不跟計較,大方地揚揚下,示意就算贏吧。
沈令蓁清清嗓子:“那郎君就得答應我兩個要求。我先說第一個。”
“嗯。”
“我希從今往后,不論什麼事,郎君都再也不欺瞞我,騙我。”
霍留行面無奈。
果真還是知道了送花人是誰。
“郎君要反悔嗎?”
他默了默,搖頭。
沈令蓁豎起小指與拇指:“那拉鉤。”
霍留行不太爽利地出手去,拿拇指摁上的拇指,問:“嗯嗯嗯嗯嗯?”——還有一個呢?
沈令蓁費勁地想了半天,搖搖頭:“我沒想好,郎君就先欠著吧!”
大汗淋漓地鬧了一場,不得黏糊,很快便離開了臥房去沐浴,臨走叮囑霍留行安安分分待著,可一回來,卻看他把自己撓得渾一片紅,尤其脖子上,一長溜的珠子。
實在管不住他的京墨與空青哭嚎著說“夫人可算回來了”,求趕治治霍留行。
沈令蓁與兩人合力把他拖去睡覺,自己坐在床沿死死盯著他,一看他抬手,便將他手一把拍掉。
若是空青和京墨這麼攔他,恐怕早被分筋錯骨。可對著沈令蓁卻還不了手,霍留行只能閉著眼睛暗暗磨牙。
沈令蓁看他睡不著,問道:“我給郎君唱首謠吧?”
他不吭聲,像是默許。
沈令蓁便輕輕唱了起來:“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
霍留行驀地睜開了眼睛。
“……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Advertisement
霍留行抬起一食指,在手背上寫字:誰教你的?
這是《后漢書》里記錄的一首歌唱民生疾苦的謠,講的是漢桓帝時期,頻繁的戰爭與徭役令士兵百姓飽煎熬,苦不堪言的故事。
沈令蓁說:“是阿娘從前唱給我聽的,郎君也聽人唱過嗎?”
霍留行點點頭,繼續寫:我父親。
兩人陡地陷了沉默。
能將這樣一首謠教給孩子的人,會有多窮兇極惡?
霍留行忽然想起那日初到國公府時,趙眉蘭與他開誠布公的一段話。
說,二十八年過去了,不管當初有多苦衷,始終不曾對霍家解釋過一個字,因為他大哥確實死在手里,結果已然如此,過程如何,再談皆是多余。可事到如今,為了沈令蓁,再多余,也還是要說一句,可對天起誓,當年是真心實意前去勸降,對他大哥絕無殺心。
霍留行輕輕嘆出一口氣。
其實不需要起誓,這麼說了,他就已經相信了。
這位鎮國長公主,骨子里是個非常驕傲的人,若非真相如此,不屑于拿這種事說謊。
然而說的沒錯,或許彼時雙方確實產生了什麼誤會,可不論過程如何,都改變不了結果。
霍留行沒有見過他的大哥,也沒有真正經歷過當年的戰,那段仇對他而言是用耳朵聽來的。如今得到趙眉蘭這樣的解釋,他或許稍微多了一些藉。
可他父親失去的是一個鮮活的兒子。要他父親就此釋懷,還是不能。
霍留行看著神黯然下去的沈令蓁,知道與自己想到了一塊去。
所有人都安著,告訴,他們兩家人現在是不得不合作的命運共同,讓把心里那個死結撇到一邊去。
可是那個死結只是去了邊上,并沒有消失。
不去的時候,好像可以暫時置之不理,一旦及,就會發現,它還是打在那里,還是絞得人心發疼。
而此刻,除了盡量避開它,霍留行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他拍拍床榻,示意沈令蓁上來睡覺。
兩人似乎對此心照不宣,沈令蓁也很快笑起來:“那郎君還撓不撓自己啦?”
霍留行咬著牙哼哼:“嗯嗯。”——我忍。
沈令蓁便上了榻,又盯了他一會兒,看他當真一不,才放心地睡了過去,不料翌日一早天亮,卻看枕邊人睜著布滿的眼,一臉幽怨地看著。
被嚇了一跳:“郎君看什麼呢,怪嚇人的!”
霍留行的嗓子消了些腫,稍稍能發聲了,解釋道:“要聽實話?”
沈令蓁點點頭。
這是當然。他昨晚答應了的。
“看你好看。活了二十八年,真沒過這種苦,了一整夜,就指著瞧你續命了。”
“……”
大清早的,這麼可憐的甜言語,誰得住啊。
沈令蓁支吾著說:“……那郎君怎麼不醒我?有個人說話,好歹還能分一分心。”
“還要聽實話?”
沈令蓁搖搖頭:“不聽了,不聽了……”怕被他說得,心里的小鹿都撞死了。
霍留行這下還就偏要說了,啞著嗓子,目炯炯地看著:“看你睡得太香,舍不得吵醒你,連手都沒敢抬起來撓一下。”說著就要去掀被衾,討賞似的說,“不信你來檢查。”
哎呀……這還怪人發臊的。
沈令蓁被他那眼神瞧得,飛快披下了榻,吩咐空青與京墨來替他上藥,自己一溜煙跑了。
霍留行卻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脈,神抖擻地坐了起來:奇哉,妙哉。誰說二十八歲不能撒?早知道說實話有這種用,他端個瓜皮架子?
——
沈令蓁用過早食后,聽空青和京墨說,霍留行白日里意稍減,方才上過藥,終于睡著了。
點點頭,又問:“今日剛好是初一大朝會,替郎君向宮里告假了嗎?”
“一早就已派人去了。”
沈令蓁放下心來,見霍留行睡著,左右也無事可做,便去了東廚照看他今日的湯藥和膳食,這一照看,一直忙活到巳時,聽門房來報,說二皇子再次登門。
因霍留行還未醒,沈令蓁讓人不必打擾他,自己從東廚匆匆到了廳堂接待貴人,過門檻,一眼看見滿面歉意的趙瑞,還有他邊一位太醫模樣的人。
“二殿下。”沈令蓁向他福行禮,心中已然猜到他今日來意。
趙瑞朝頷首回個禮:“今早在朝會上聽說霍將軍因食用鰒魚得了急病,我實在難辭其咎,這便請了宮中太醫,想著來替他診治診治。”
沈令蓁忙道:“此事全因郎君質特殊,著實與二殿下無關,若說誰有錯,倒該怪我沒有照顧好郎君才是。昨夜已有醫士來過,郎君的病現下也有了好轉,正睡得安穩呢,二殿下盡可寬心。”
趙瑞歉然一笑:“話雖如此,還是請太醫看過放心一些。”
沈令蓁面為難:“二殿下,郎君一夜未眠,我怕這會兒醒了他……”
“是我思慮不周,那這樣,我讓太醫留在府上,等霍將軍醒了再診,你看如何?”
沈令蓁福了福:“那令蓁就在此代郎君謝過二殿下意了。”
趙瑞搖頭示意不客氣,聽邀請他留下來喝杯茶,忙說不叨擾了,主告辭。
沈令蓁便親自送走了貴人,又吩咐下人給太醫上了茶,讓他在此稍候,自己則去了霍留行的主院。
進院的一瞬,邊笑意消散無蹤。
的這位二表哥,登門道歉來得如此迅速,來了卻毫不過問霍留行的狀況,反倒三句話不離診脈一事,看來看去,實在不太像個真正飽含歉意的人啊。
沈令蓁剛到廊廡下,正想著這下恐怕不得不醒霍留行了,就聽臥房傳來他怒不可遏的沙啞聲音:“你們讓一個人去應付老二?我是死了嗎?”
“郎君息怒,小人是看您好不容易睡著了,才沒有醒你,又想著這里是霍府,出不了岔子,且夫人為人也機警,理應……”
“我理應你個榔頭!那畜生對做過什麼,你不知道?”
沈令蓁一聽這是要打起來,趕疾步穿過廊廡,剛來到臥房門前,正瞧見穿戴好冠的霍留行風風火火一把掀開了房門。
還沒等開口,他便先張了,像要問什麼,結果張了半天,愣是沒吐出一個字來。
沈令蓁哭笑不得:“郎君別急,慢慢說,我好端端的呢。”
霍留行對著清了半天嗓子,恨恨一拍大。
天殺的,一著急,又失聲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48 章

農家嬌福妻
傅胭穿越後當了十二年丫鬟,總算等到能出府了!可是,想順利出府先得找個相公?要不,這個鐵憨憨先湊活下……農家小子蕭烈心裡有個神仙白月光,不敢肖想,遠遠望見一次便能激動難眠。有一天,白月光主動找上門,說要嫁給他?娶!馬上娶!敢嫁我就拿命寵她一輩子!
43.6萬字8 34286 -
完結1061 章

空間之錦繡農門
剛得了個空間就魂歸異世,再次醒來,穿越成命硬剋夫、沒人敢娶的小農女,為擺脫家中極品,匆匆賤嫁。丈夫是個瘸子獵戶,家裡窮得叮噹響,還帶著一個五歲的拖油瓶。許清表示,不慫!種農田,養牲口,做糕點,釀美酒,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懟親戚,鬥極品,開店鋪,賺大錢,旺夫旺到祖墳冒青煙。「娘子,看!這都是為夫為你打下的江山!」「把剩下的秧插完再說!」
188.5萬字8 100603 -
完結546 章

王爺和離後又來爬牆了
戰地醫生慕容卿意外穿越,一朝分娩,被王爺跟他的白月光當場羞辱,差點斃命。 她理清思緒一手虐白蓮,一手抓經濟。 一個不小心還帶著小寶成了盛京首富,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某王神出鬼沒,好! 既然你不負起當爹的責任,老娘就休夫另娶。 某無賴抱著她的大腿,「王妃,把本王吃乾抹淨了,你還想去哪? “ 慕容卿本不是好色之徒,但是...... 王爺的腰,奪命的刀啊!!!
101萬字8 17896 -
完結625 章

我妻薄情
謝玄英出身富貴,皎若玉樹,文武全才,后人精辟總結:比他能打的沒他博學,比他博學的沒他美貌,比他美貌的沒出生然而,如此開掛的人生,卻有三件挫敗之事第一事,遇見心愛的女子,卻難結連理第二事,歷盡千辛成了親,她不愛我第三事,她終于愛我了,但更愛事業謝玄英:平生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程丹若:我想要牛痘、奎寧和青霉素女主穿越,有金手指,半考據半架空,合理地蘇一下閱讀提示:1、架空世界,風俗背景為設定,以本文為準,請勿代入其他時代2、作說有部分注解和提示,建議閱讀,不要屏蔽3、醫術部分會查閱資料,但不是...
112.6萬字8 1458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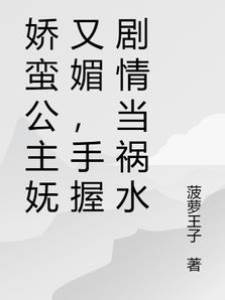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4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