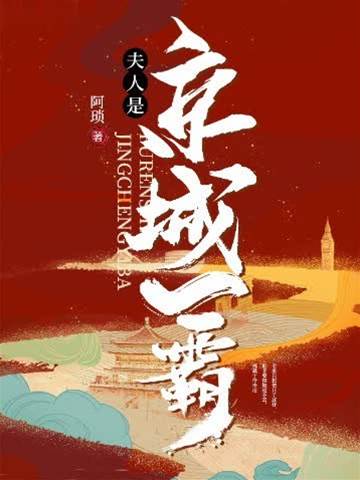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云鬢亂》 第 35 節 入骨歡
我踉踉蹌蹌地爬了起來,搶在蕭寰前頭對著定淵怒罵:「大膽奴才,自去領五十大板謝罪!」「是,是!奴才該死!」定淵連滾帶爬地逃了出去。
蕭寰回頭看我,并未拆穿我拙劣的計謀,許久后,忽而森然一笑:「宜,你想不想要朕的孩子?」
沒有人想要這個孽障,我不知道他在盤算什麼,但我到了害怕。
他沒有我回答,卻突然將那碗湯碗狠狠摔在了地上,「蕭宜,你信不信?朕有辦法保住咱們的脈。」
「不!」我發出了一聲絕的呼。
他要做什麼?他已經瘋了。蕭寰丟下此言,便拂袖離去,此后,他命人對我嚴加看管,徹底斷了我的退路。
可我仍舊低估了他。
元延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歲的臨華公主終是出嫁了,駙馬乃是剛立下赫赫戰功,幾個月前才被陛下提為寧將軍的顧修。
只是大婚那夜,新郎顧修竟被人迷暈在了新房里,一覺睡到了天亮。
翌日,顧修接旨遠赴邊疆抗敵,一場勝仗過后,竟于帳中暴斃。
剛出嫁不到一個月的臨華公主頓時了寡婦,只能搬回華宮,獨留下寧將軍的腹子。
我不知道顧修到底是怎麼死的,他不過二八的年紀,又常年習武,骨朗健,我不信他會這樣輕易就去了。
我只知道,顧修的父親是統掌三千營軍權的侯爵,顧修承襲其父之能,屢立戰功。因而蕭寰早就忌憚顧家權勢滔天。
能使出這樣一舉兩得的手段,只怕世間再無人及他了。
10.
愈是痛苦的日子,愈是過得極慢,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到懷胎近六個月的,只覺自個兒終日渾渾噩噩,卻又時常要在人前強作鎮定。
Advertisement
我是大昭最尊貴的公主,凡塵俗世皆不能沾染我分毫,即便「克」死了新婚的丈夫,世人亦不能妄議我分毫。不是不能,是不敢。午后,蕭寰遣人來華宮賜滋補佳品,來者亦有定淵。
這是蕭寰的試探和肆無忌憚,他料定了定淵的屈從和我的乖順,便故意讓定淵到華宮來折磨我。
簾外傳來定淵的聲音,他只吩咐小太監放下東西,便急急想要退下。我本不敢留他,卻驀地生了逆天的膽子,我只想堂堂正正地看他一眼。
「謝福。」
我挑簾而出,他驚得連連后退,慌忙垂首,只恨不能把頭埋進地里去。
我并未挽發,上只著一件梅花紋紗袍,肚子高高隆起。這是我懷胎后,他頭一次見我。
待我行至他前時,他更是駭極,跪下輕呼一聲:「公主!」
他老了,眼角竟起了細細的紋,我這才驚覺——定淵已至而立。
他此前挨了五十大板,如今行仍舊不利索,可能保住
命已是蕭寰的恩賜。
「傷可好些了?」
「奴才好些了。」「退下吧。」
送走定淵,我漸起了困意。
九年前那個撕心裂肺的夜,了我的心魔,讓我夢魘纏。「定淵,救我!」這場噩夢在日落時作結。
醒來時,我已不在貴妃榻上,而是置寢帳。
蕭寰正斜臥在一旁,垂眼盯著我,邊泛起一抹笑,含著戾氣。
「謝福救不了你。」我心頭一滯,卻又不敢出聲,只強下紛的思緒。
可蕭寰對我了如指掌,見我如此神,便知我心底在想什麼,一時不由更怒,手便掀開薄衾。
我頓覺恥無比,不自覺推拒。
蕭寰眼里戾氣更盛,手上也失了分寸,一把揪住了我披散的發,往后拽去,力道狠極。
Advertisement
我疼得面目扭曲,卻不敢出一聲兒。
蕭寰見我面上憋得通紅,終是心生不忍,猛地松開了手。
涼風吹起曳地的紗簾,我側頭自簾中去——定淵正跪在帳外,背上模糊,必是又了杖責。
我嚇得驚呼一聲,下意識起想要出去,卻被蕭寰一把擒了回來。
他揚手向我揮來,手掌卻又在半空中停下,緩緩垂落。
我再不敢出聲,我越是求他,他便越不會放過定淵。「日落了,睡吧,罰他在帳外跪一夜,明早朕讓他回去。」
話落,他摟著我躺下,閉上眼睛不再作聲。蕭寰生乖戾,誰敢忤逆他半分,他便要加上百倍奉還。
我只得閉目,眼角卻不住淌下一滴淚來,那淚一路滾落,終至蕭寰臂上驚擾了他。
他突然掐住了我的脖子,狠道:「不許哭,你若再敢為他流上一滴淚,朕便即刻殺了他。」
我生生憋回了眼淚。
對,我不能哭!
11.
翌日,陛下再度杖責監謝福的事兒傳遍了整個昭宮。
宮人們都說謝福得勢的日子到頭了,有點兒資歷的太監們更是拳掌,一心盼著取而代之。
誰料待謝福養好了傷,竟又被喚回麟合宮伺候,眾人又皆嘆君心難測。
我已懷胎近八個月,行甚是艱難。只是蕭寰再難近我,我自也落得清靜。
這段時日,蕭寰念及我懷胎辛苦,待我有的溫。
定淵已回到他邊繼續當差,不過蕭寰命他再不準踏華宮半步。
太醫替我估算的生產之日將近,蕭寰竟愈加焦躁起來。
他霸占我多年,早已癮,念膨脹,只恨不能將我嚼骨,吞進肚里,與自己永不分離。
現如今,竟生了癲狂的念頭——
Advertisement
想讓我趁產下胎兒之際假死,好借此胎換骨,名正言順地為他后宮里的新寵,而他又能將這孩子養在邊。
這樣天大的謀,我卻不得不從。
我在蕭寰面前從無半點權利,就連為他人而流淚的權利都沒有。
蕭寰大約是瘋了。
這九年歲月,竟磨不去半點他對我的執念。
我讓妤蓮暗中給定淵帶了話,此后,便常踱到華宮外散步。
三日已過,仍不見謝定淵半點蹤影。
我心中愈加絕,哀嘆之際,手折下了一枝梅花。
忽聽遠傳來腳步聲,一路輕踩著落葉而來。
回首之時,手里的梅枝驚得落在了腳邊。
「定淵……」
「公主……」
定淵見了我,遠遠停住不。
我走上前去幾步,又堪堪止住,眼角一熱竟淌下淚來。
「定淵……」
帶我走吧,離開這無邊煉獄,即便是死,也能一得解。
可我生生吞下了后頭的話,只又喚了一聲——
「定淵!」
許是見我眉目哀切,竟是在求他的模樣,定淵心中苦,終是松了口:「宜……」
話落,他亦隨我落下淚來。
「謝定淵,我不為難你,只想再見你一面,此后前塵往事一筆勾銷,你我再無瓜葛。」
定淵聽罷,愣了許久,竟一步步挪上前來,緩緩展臂,抖著將我攬懷中,這是他頭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這樣我。
十八載了,我于他而言,便是那天上的云,看得見,卻不著。
而今,他已不要命了。
……
「謝定淵!」
伴著一聲怒極的呵斥,我猛地推開定淵,當即被蕭寰親手擒住。
抬眼去時,只見蕭寰眸里似有猩紅的烈火,直灼得人無可藏。
沖著被執金衛制伏在地的定淵,他高聲吼道:
Advertisement
「你該死!」
我見此景已喪盡理智,不經思量便大聲懇求:
「是我有罪!」
可我忘了,
蕭寰最忌諱的便是我為了謝定淵而忤逆他。
「公主無罪!」 定淵掙扎而起,揚聲反駁:「是奴才蠱了公主!」
蕭寰見此形,更是怒火中燒,一把出執金衛腰間的劍大步朝定淵走去。
「你這該死的閹人!」
「不!」我厲聲長呼,飛撲而去,驚得苑中飛鳥四散,卻被牢牢拽住。
蕭寰停在定淵前,回首朝我看來,眉目間盛滿戾氣——「由不得你。」
「不要!」我閉上眼睛,天地間再無聲響,唯有劍刃捅的聲音是那般清晰可聞。
再睜眼,定淵已倒在泊之中,他朝我綻開一笑,頰間微微沁出一個笑渦,一如十八年前,我初見他時的模樣。
殷紅的濺到了邊,炙熱滾燙,灼得人生不如死。
我只覺腹中一陣絞痛,不由哀呼一聲,間緩緩淌下來。
12.
元延十二年,臨華公主難產而終,腹中胎兒產下三日便夭折而亡。
至于那輕薄了公主的謝福,則被人裹上一卷草席抬出宮,拋了葬崗。
陛下為保公主生前清譽,亦將當日親歷此事的宮人紛紛死。
聞名一時的臨華公主竟被一介卑賤的太監輕慢,終落得夫亡子夭人亦終的結局,上到達顯貴,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唏噓。
可眾人嘆了一陣子卻又紛紛忘卻,漸漸再無人提及蕭宜的名字。
第二年春末,蕭寰后宮有了一位新寵,被其視若瑰寶,竟將臨華公主的故居華宮賜予這位新寵居住。
據傳此乃是西域小國進貢而來的絕世人,生來氣若游,通,終日見不得。
一生不可邁出宮門半步,直至老死。
故而在偌大的昭宮里,除卻陛下的心腹和華宮近伺候的宮,再無人能窺探其容貌。
眾人皆嘆,陛下被迷了心竅,喪了理智,日日夜夜浸在那華宮,再也出不來了。
不倫的貪歡,呼嘯的,在月華四濺的華宮綿延不散……
元延二十二年,蕭寰已至不。
三年前秋獵時落了箭傷,此后便埋下病,每年冬至,總要犯上一回。
太醫總道:「陛下生來有瑞氣護,只待稍加調理,不日便可痊愈。」
但我知道,對于蕭寰的生死,太醫們是說不得實話,也不敢說實話的。
蕭寰鬢間已有了幾白發,近來的政事擾得他疾復發,而我這個旁人口中的「妖」更耗盡了他的氣。
這半個月來,他已經清瘦得不樣子了。
我尚且記得,彼時在麟合宮初見他時,他是那樣風姿卓絕,矯若驚龍,可如今,他已盡數失了神采。
蕭寰將去的那天,是一個寒冷的雪天。
我照例陪著他臥在榻上,唱著阿娘在戒宮時教我的歌謠給他聽。
蕭寰閉目靜聽,待一曲唱罷,他忽然費力地睜開眼看我,眼底憔悴卻盡是寵溺。
我及他的目,著自己出了幾滴淚來。
蕭寰出枯瘦的手了我的發道:
「不許哭。」
那聲音已啞得像是撕裂了一般。
未過多時,蕭寰的監王荃推門,徑直遞來一個紅蓋兒的青瓷小瓶。
「娘娘,請吧。」
我微微一滯,隨后釋然一笑。
蕭寰癡癡看向我道:「宜,朕不能比你先去,朕怕你再與旁人……朕怕自己不能瞑目。」
我略略搖頭,一指輕抵住他的,再而拂過他的眉眼,輕道:「我明白。」
話落,我緩緩接過小瓶,仰首一飲而盡,又鉆進蕭寰懷中,眼角溢出的淚打了他前的衫。
「蕭寰……」這是我最后一次喚他的名。
縱然他違背倫理綱常霸占了我十九年;
縱然他殺死謝定淵,讓我哀極攻心痛失骨;
縱然他抹去了蕭宜所存在的一切,將我困在這華宮里整整十年。
可此刻,我竟對這畜生生出了一憐憫。
眼前逐漸模糊起來,待沉黑暗之際,只聽他在我耳畔留下了最后一語:
「宜,等等我……我就來……」
癡人啊……
元延二十二年雪后的寒夜,華宮莫名起了一場火,大火連燒三天三夜。
陛下在烈火中駕崩,上下哀慟三月。
此后,新帝繼位,再無人憶起華宮的一切。
昭宮里的鐘聲照常響起,不曾因為誰的離去而停止,唯有那聲音遠遠拋過夕霞,綿延出一道無盡的弧。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830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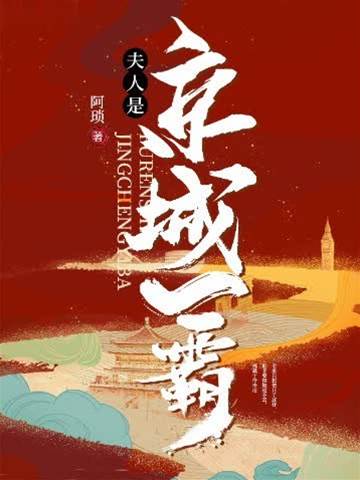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1738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878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