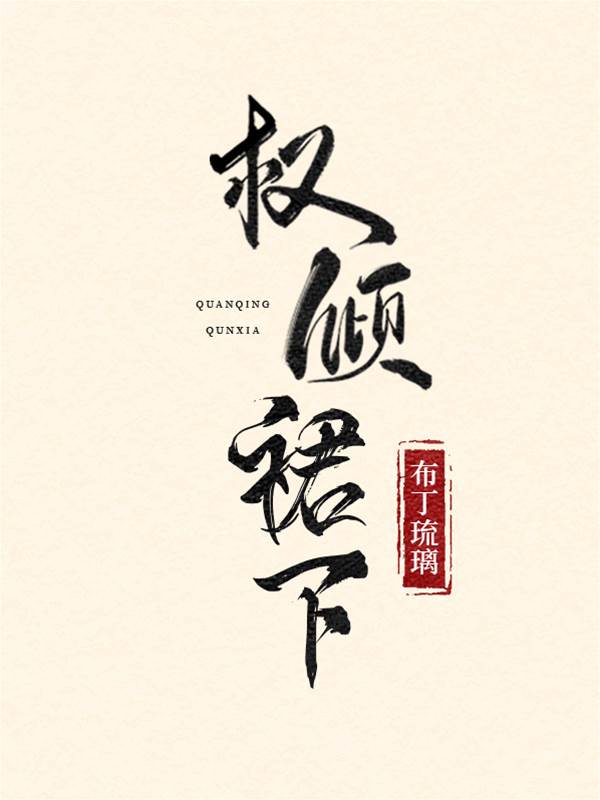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替身竟是本王自己(雙替身)》 第 32 章 三十二
豫章王桓明珪來瓊林閣純屬閑著無聊無可去。
一般人能逛的地方不知凡幾,但像他這樣夜夜笙歌的人,平日該玩的都玩夠了,上元夜也無非是燈多一些,逛的還是平日常去的地方。
瓊林閣的酒菜是全長安酒樓里最致新巧的,他逛累了想坐下吃點宵夜,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里。
桓明珪走進瓊林閣中,目先往高臺上的歌姬舞伎瞥了一眼,只一瞬便知道乏善可陳,大部分都是面孔,新來的兩人也姿平平。
接著他認出了東宮和齊王府的侍衛,納罕地了下頜,這兩人就差拔刀相向,上元夜竟然一起上酒樓,真是匪夷所思。
隨即他便在人叢中發現了著侍衛裳的隨隨,只遠遠見個模糊的廓,雙眼便是一亮。
隨隨男裝雌雄莫辨,可以騙過大多數魯男子,但年男子與子的格形畢竟不同,豫章王何許人也,稍稍一打量便看出是子。
電石火之間,他已想通其中關竅,“嘖”了一聲,朝樓上瞟了一眼。
這桓子衡也真是,上元佳節帶了人出來,自己坐在樓上樂,卻人在樓下坐冷板凳。
豫章王最是憐香惜玉,一見人冷落,就忍不住想去溫暖一下。
他二話不說就向侍衛們走去。
桓煊在樓上看著,他想沖下去將那獵戶拉起來就走,卻什麼都沒做,仿佛想證明些什麼。
他只是一瞬不瞬地盯著那窈窕的影,不知不覺繃脊背。
桓明珪似乎察覺到他的目,腳步頓了頓,抬起頭朝二樓來,甚至還沖他勾了勾角。
桓煊笑不出來,若是手里有弓箭,他大約已經一箭把這登徒子死了。
可惜齊王沒帶弓箭,桓明珪平平安安走到侍衛們中間。
Advertisement
看清隨隨面容的剎那,他微微一怔,腳步頓了頓,隨即恢復平日嬉皮笑臉的模樣,不見外地往隨隨對面一坐。
他時常去東宮和齊王府串門,兩邊的侍衛沒有不認識他的,都笑著向他行禮。
桓明珪全無郡王的架子,笑著與他們打招呼。
他時常混跡在市井間,這里的侍衛幾乎都和他喝過酒賭過錢,桓煊的侍衛統領關六郎與他最相,笑道:“豫公子,郎君們在樓上飲酒,你老人家不去作陪,怎的和咱們這些下人混在一?”
一個東宮侍衛意味深長地看了隨隨一眼,揶揄道:“關六兄難道不知道?方圓十里只要有人,咱們豫公子的眼神比蕭泠的箭還準。”
眾人都是會心一笑。
隨隨正喝酒,冷不丁聽見自己的名字,險些沒嗆住。
豫章王毫不生氣,微微側著頭,用那雙狐貍眼端詳隨隨:“咦,這位小兄弟看著面生,是新來的麼?”
關六郎忙向隨隨介紹到:“這位是我們郎君的堂兄豫公子。”
又向桓明珪作揖:“新人面皮薄,還請豫公子高抬貴手。”
豫章王斜他一眼:“怕什麼,難不本公子會吃人?”
他看向隨隨:“小兄弟什麼名字?”
隨隨知道他早認出了自己,只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上回在街邊茶肆可以不搭理,當著這麼多侍衛的面卻不能拂了齊王堂兄的面子。
隨隨道:“回稟豫公子,小人敝姓鹿。”
桓明珪又問:“哪個鹿?”
隨隨道:“一頭鹿的鹿。”
桓明珪一笑:“小兄弟人漂亮,姓氏也漂亮。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桓明珪又問:“聽小兄弟說話,像是關隴一帶的口音?”
Advertisement
隨隨點點頭。
桓明珪狐貍眼一瞇:“可我看小兄弟長相,卻更像燕趙人呢。”
隨隨心頭一凜,父親兼三鎮節度使之前,曾當過幾年幽州節度使,時確實在燕趙生活過數年。
莫非他知道些什麼?
正思忖著,便聽這紈绔悠悠道:“燕趙多佳人,者如玉,我看小兄弟如玉,還以為是燕趙佳人呢。”
隨隨哭笑不得,在河朔時便聽過豫章王的大名,后來去西北平叛,又從桓燁口中聽到他不事跡,不過聽他這樣牽強附會,油舌,還是有些嘆為觀止。
忍不住淺淺一笑。
冷若冰霜的人一笑,瞬間冰消雪融,猶如春乍泄。
桓明珪不由看得一怔。
桓煊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從樓上往下去,只能看見兩人的側臉。
只見桓明珪坐在對面,不一會兒便漲紅了臉,桓明珪眉飛舞說了些什麼,他逗得嫣然一笑,桓明珪頓時兩眼發直。
桓煊看不下去,轉回到房中。
不多時,太子從凈室回來,見弟弟沉著臉,一言不發地喝悶酒。再看太子妃,雖竭力佯裝無事,但眼眶微紅,一看就是流過淚。
太子眸微,不聲地回到座中,向兩人道:“方才我在樓下看見子玉了。”
阮月微道:“怎麼不請他上樓來?”
太子笑道:“他的子你還不知道,正和侍衛們玩樗,呼盧喝雉忙得不亦樂乎。”
阮月微強打神湊趣:“豫章王這卻有些不地道了,全長安誰的樗打得過他。”
太子道:“阿阮這回料錯了,方才我在樓下看了一局,豫章王連輸了兩把給子衡家一個侍衛,那個生面孔。”
侍衛中的生面孔只有一個,就是那扮男裝的外宅婦。
Advertisement
阮月微勉強笑了笑:“這倒是稀罕事。”
太子道:“一降一,那廝歲除夜從我這贏了一塊紫玉佩去,今日讓他也得個教訓,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桓煊臉越發不好看,正打算起去將那登徒子揪上來,不等他起,只聽樓梯上一陣輕快的腳步聲,桓明珪自己上來了。
太子揶揄道:“怎麼舍得上來了?”
桓明珪咧一笑:“上帶的金銀都輸了,一會兒沒錢會帳,只得來找太子和齊王殿下打秋風。”
太子笑道:“這混不吝。”
一邊吩咐侍取盤碗杯盞來,又要了幾樣酒肴糕點。
桓明珪一張可以頂十張,席間的氣氛頓時熱鬧起來。
阮月微酒量很淺,平日有宴飲只喝一兩杯,今日卻連飲了好幾杯,仿佛杯子里的不是劍南燒春,而是白水。
太子見面頰紅、水眸迷離,先前還知道遮掩,這會兒目就像是黏在了桓煊臉上。
他知道是醉了,便向桓煊和桓明珪道:“時候不早了,太子妃明日還要去武安公府赴宴,先失陪了,你們務必盡興。”
桓煊也跟著起要離席,被桓明珪一把揪住袍擺,控訴道:“子衡怎可留下我一個人,太子殿下有家室,你急著回去做什麼……”
太子笑著拍拍兄弟肩膀:“難得上元節,你就陪陪你六堂兄吧,不必送我們。”
說著攜著阮月微的手下了樓。
阮月微只覺頭暈目眩,雙發,每走一步,腳下的樓梯仿佛在涌。
到了樓下,疏竹和映蘭立即上來攙扶,扶著上了門外的馬車。
太子一直神溫和,對太子妃護有加,然而一放下車帷,臉立刻冷了下來。
阮月微靠在他肩頭,已闔上了雙眼。
Advertisement
太子皺了皺眉,將輕輕一推。
阮月微呢喃了一聲,倒在墊著狐皮的坐榻上。
太子冷冷地乜了一眼,便即收回目。
……
太子夫婦走后,桓明珪的眼神瞬間恢復清明,執起酒壺,往桓煊杯中注酒。
桓煊手將杯口擋住道:“不必了。”
桓明珪“撲哧”一笑,放下酒壺,向樓下瞥了一眼,嘆了口氣道:“子衡,此事你打算如何了局?”
桓煊了眼皮,沒搭理他。
桓明珪的狐貍眼中難得沒了平日的玩世不恭:“三年了,你還是放不下?”
“”指的是誰,兩人心照不宣。
桓煊道:“已經過去的事,不必再提。”
桓明珪一哂:“你沒看見方才看你的眼神?”
桓煊有些詫異:“什麼眼神?”
他方才沒去看阮月微,一來是避嫌,二來也是因為心不在焉,一直在往樓下。
桓明珪若有所思地看著他:“你若是已經放下阮三娘,便該好好娶妻生子,當你的齊王。”
他頓了頓道:“你若是還念著,更不該找個容貌相似的子當藉。”
桓煊蹙了蹙眉。
桓明珪微微嘆息:“非是愚兄覬覦你的人。既然我看到那子的真容,便不能不勸你一句。就算是為這鹿氏著想,你也該早作了斷。”
他角帶笑,可說出的話卻像刀鋒一樣冷酷鋒利:“哪天你徹底放下了阮三娘,你還會對屋及烏麼?到時候看到那張臉,你會不會恥?會不會嫌惡?到時候你打算怎麼置?施舍點財帛趕出去?還是鎖在你那荒宅里不聞不問,直到終老?”
桓煊抬起眼盯著他,眼神鷙:“這是我自己的事,不勞六堂兄費心。”
桓明珪嘆了口氣道:“你的事我不能袖手旁觀。”
桓煊執起酒壺給桓明珪和自己斟滿,冷冷道:“我知道你是我長兄之托看顧我,但如今我已不是黃口小兒,自己的事自己能作主。”
他頓了頓:“這些年,無以為謝。”
說罷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放下杯子,起一揖:“失陪了,六堂兄。”便即轉離去。
桓明珪著他的背影,苦笑著搖了搖頭。
……
從瓊林閣出來的時候,坊街上依舊車如水,馬如龍,行人接踵肩。
人們手中提著各燈籠,有紙糊的,絹制的,皮制的,更講究一些的提琉璃燈,隨著人群移,城中仿佛有一條匯聚而的河流,緩緩流淌在大街小巷。
騎在八尺大馬上去,這景致得宛如夢境。
可桓煊卻無心欣賞。
他仍舊與隨隨并轡而行,然而卻不復來時的輕松愉悅,自打從瓊林閣里出來,他便沒再和說一句話。
隨隨瞥了眼他的神,便知曲江池的河燈是放不了。
難得出來玩一次,還偶遇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和夫君攜手同游,他此時的心可想而知。
幸好隨隨對放河燈沒什麼執念,在河朔時,上元節也跟著父親去放過幾回河燈,不知放了多只,每只河燈上都寫著同樣的愿,不過是求一家人團圓,到底也沒實現。
默默地落后一個馬,不去打擾他設地想,這時候他一定想獨自靜一靜。
兩人一前以后往城南行去,桓煊果然沒往東面曲江池的方向去,而是朝山池院西行。
人流幾乎全是往曲江池涌去的,回山池院的一路車馬稀,與先前的熱鬧相比,更顯得清寂寥落。
桓煊忽然放緩速度,與并轡,轉頭冷冷道:“你會玩樗?”
隨隨點頭道:“村子里的人都玩,民跟阿耶學的。”
“你會的東西還不。”桓煊道,語氣里有點譏誚。
隨隨聽出他來者不善,便沒有接茬。
“你贏了豫章王什麼?”他過了會兒又問。
隨隨道:“兩個金餅子,一塊玉佩……”
桓煊臉一沉。
隨隨接著說:“玉佩民沒拿。”
桓煊面稍霽:“本就不該拿。”大風小說
隨隨道:“金餅子要還回去麼?”
“是你自己贏來的便留著吧,”桓煊沒好氣道,“豫章王家大業大,不稀罕兩塊金餅子。”
“多謝殿下。”隨隨道,隨時可能離開,不一定來得及去常家脂鋪取錢,山池院桓煊賞的絹帛又不好攜帶,有兩個金餅子傍,便不怕沒盤纏了。
桓煊冷哼了一聲便不說話了。
兩人默默行出十里,桓煊忽又轉頭問道:“你就沒有什麼想問孤?”
隨隨一時間有些不著頭腦,自問還算懂得謀算人心,但桓煊總是讓一籌莫展,這人的心思比四月的天氣還難猜,偏偏還總讓人猜。
猜你喜歡
-
完結23 章

法醫狂妃:王爺,躺好彆動!
首席女法醫冷夕月,穿越成寧王李成蹊的棄妃。 剛剛醒過來,就遇到冤案。 她帶著嫌疑人家屬偷偷去驗屍,卻被王爺拎小雞一樣捉回去狠狠訓斥。 她費儘心思追查死因,最後嫌疑人卻跪地求她不要再追查下去…… 找出真相,說出真相,她執意要做逆行者。 可糊塗王爺整日攔著她就算了,還弄來個“複生”的初戀情人來氣她…
4.4萬字8 775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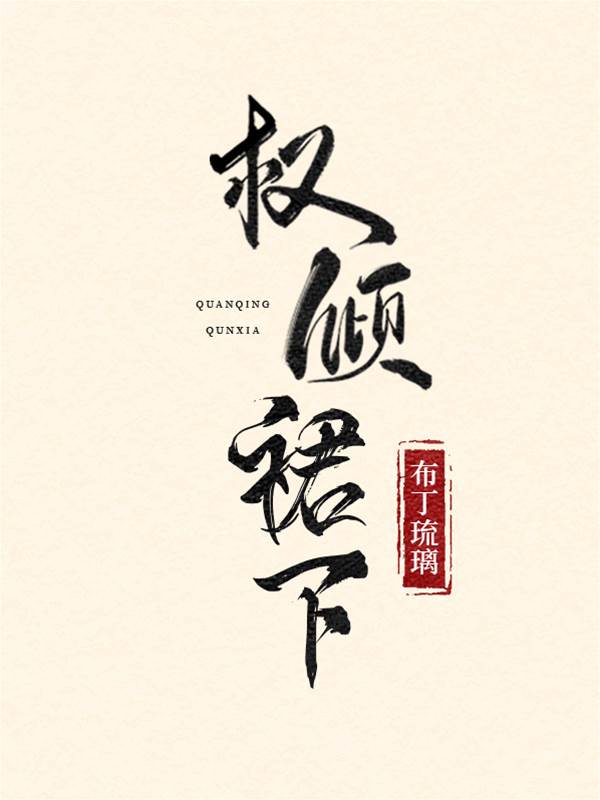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963 -
完結429 章
乞丐醫妃:馭夫有道
穿越成乞丐,救了個王爺?這是什麼操作?江佑希不由暗自腹誹,別人都是穿越成公主王妃,她倒好,鞋兒破帽兒破身上的衣服破? 神仙運氣呀。 還被這個惡婆娘冤枉和敵國有勾結,勾結個毛線,她連去敵國往哪個方向都不知道啊! 火速止住謠言,她毫不留情地報復......了惡婆娘,在王府混的風生水起。 她真是馭夫有道啊! 馭夫有道!
108萬字8 10212 -
完結454 章
山河美人謀
有仇必報小驕女vs羸弱心機九皇子未婚夫又渣又壞,還打算殺人滅口。葉嬌準備先下手為強,順便找個背鍋俠。本以為這個背鍋俠是個透明病弱的‘活死人’,沒想到傳言害人,他明明是一個表里不一、心機深沉的九皇子。在葉嬌借九皇子之名懲治渣男后。李·真九皇子·策“請小姐給個封口費吧。”葉嬌心虛“你要多少?”李策“一百兩。”葉嬌震驚,你怎麼不去搶!!!
108.6萬字8 101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