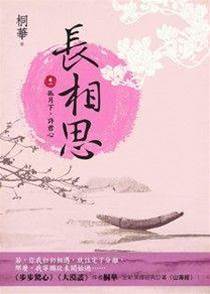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醫妃總想帶球跑》 第562章 下毒是誰
井水應該是有人投毒,水雲月這裏,既然有人能夠將毒藥放進這茶壺裏面,必然是明白水雲月從來不喝外邊水。
如若不是邊人,那必然是悉的人。
「皇上,太皇太后那裏也出事兒了,您趕過去看看吧。」
外頭一聲高呼,顧秦墨立刻站起。
不是已經將春蟬派過去了嗎?難道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兒發生了?
顧爾冬也毫不猶豫跟著顧秦墨離開,屋裏就只剩下水雲月。
「還愣著做什麼,過來扶我一起過去,太皇太后那兒必然是也有事兒了。」
這三人也不過是前後腳就到了太皇太后住的行宮。
「來歷不明的東西,絕對不可以給太皇太后吃。」嬤嬤嚴厲的擋在太皇太后床前面,而躺在床上的太皇太后,則是滿臉慘白,氣息奄奄。
春蟬手上還拿著顧爾冬給的葯,這會兒見的確是沒有辦法送進太皇太后口中了,本打算強闖,卻又想起顧爾冬說的話,擰了眉頭站在原地,另外的兩位年長公也將春蟬攔住。
「這的確是我家小姐給的葯。」春蟬焦急卻又無可奈何,站在旁邊的那位太醫也只能夠著額頭給太皇太后診脈。
Advertisement
「的確是中毒之相,可是顧太醫又從哪裏知道的太皇太后中了毒,需要這葯來解?」
「我家小姐之前被郡主過去,郡主就是中了毒,所以這才順帶的研製出了解藥。」
春蟬本以為這一番話能夠讓他們回心轉意,誰知道這老嬤嬤和太醫對視一眼之後面嚴肅。
「郡主中的毒未必是和太皇太后一樣的,是葯三分毒,你怎麼可以隨意的就將這種葯拿過來,更何況……」
老嬤嬤話還沒說完,門就被推開了,顧秦墨帶著顧爾冬一起進來的,瞧著這架勢也明白髮生什麼了。
顧爾冬從春蟬的手上接過瓷瓶,語氣平和,「嬤嬤,是我不好,沒有提前打招呼,但是事實在是太急了,便直接讓春蟬過來送葯,皇上已經查清楚,這毒是有人投進井水當中,和郡主中的是一樣的,郡主已經服用,現在好許多了。」
「拿來吧。」太皇太后躺在床上瞇著眼睛,像是剛清醒過來一樣。
春蟬微微后一步,角下癟,太皇太後方才一直都沒有睡著,也是肚子疼的那麼厲害,怎麼可能睡得著?
Advertisement
想來應該是聽說水雲月已經把這葯吃了,所以這才醒過來的吧。
顧爾冬收斂起心中失,抿著將葯送上去:「先吃進去,至肚子不會再疼了,副作用也幾乎沒有,等到明日我再調理出更好的……」
趕著進來的水雲月打斷顧爾冬的話:「也別調理什麼更好的了,我想問問顧爾冬你是怎麼在這麼快的時間裏就弄出解藥的?」
水雲月看著顧爾冬,旁邊的太醫也很是深究,「說起來老夫也很有疑慮,這葯實在太過蹊蹺了,顧太醫之前在燕國是神醫還是國手?按理來說調配解藥說也要幾日,從顧太醫的話里不難聽出,郡主應該是剛中了毒你就弄出解藥了吧!」
「那不過只是我家小姐醫高明,不和某些庸醫一樣,半日都弄不出解藥來。」春蟬張口答得飛快,語調里一派嘲諷。
剛才說話的太醫猛地一瞪眼手都在抖,一個小小的丫鬟竟然敢跟他頂,並且嘲諷他是庸醫當真是反了天了。
「你這丫頭當真是膽大包天,難怪都在傳顧太醫邊養了一個主子,現在看來牙尖利的,也的確沒有教養。」
Advertisement
「倘若顧太醫當真醫高明,那我甘拜下風,可是如果這毒是你下的,解藥能夠這麼快拿出來,可就不足為奇了。」
太皇太后抬眼看,向顧爾冬眼神當中充滿了警惕和戒備。
或許是因為剛肚子疼,防備還有偽裝全都沒來得及再次裝上,這眼神赤的就連旁邊的宮都能夠看得出來。
察覺到自己失態了,在和顧爾冬對視之後,太皇太后笑得瞇起眼睛,「顧大小姐為人明磊落,怎麼會是你們說的那樣?」
顧爾冬遲疑片刻,搖頭看向剛才說話的太醫,「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東楚有一項刑罰是對於造謠中傷他人的,這位太醫,我瞧你很是面生,你對我有什麼深仇大恨,用得著在這裏給我扣這麼大一頂帽子,你是瞧見我往水裏投毒了,還是親眼目睹我將有毒的東西投餵給那些大人吃了?」
當被別人質疑的時候,最不能做的就是自證清白,只要自證清白就很容易被人住把柄,反而是落得下風,乾脆就質問旁人可有證據,這般談話的技巧,顧爾冬還是懂的。果不其然,此話一出,這老太醫眨著眼睛,也不知該如何回應了。
Advertisement
顧秦墨簇著眉站在原地看了好一會兒戲,忽然揮手來外面伺候的侍衛:「調查清楚了嗎?」
「回皇上的話,外面的水源已經全部控制住,井水渾濁,已經安排人去查了,但是……」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侯府真千金她重生了
重回十年前的江善(周溪亭),站在前往京城的船只上,目光冷淡而平靜。她是被人惡意調換的文陽侯府的真千金,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里的容妃娘娘是她姨母,溫潤如玉的二皇子表哥是太子之位的熱門人選,出生既頂端的她本該萬千寵愛、榮華富貴且波瀾不驚地過完一生。但十六年前的一場人為意外,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等她得知身世,回到文陽侯府,取代她身份地位的江瓊,已經成為父母的掌心寶。前世她豬油蒙了心,一心爭奪那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論是父母的寵愛,還是江瓊身份高貴的未婚夫,這一世,她只想快快活活地活一...
107.9萬字8 330570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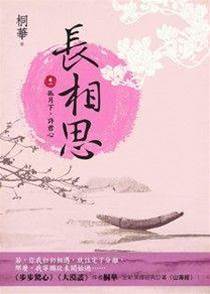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