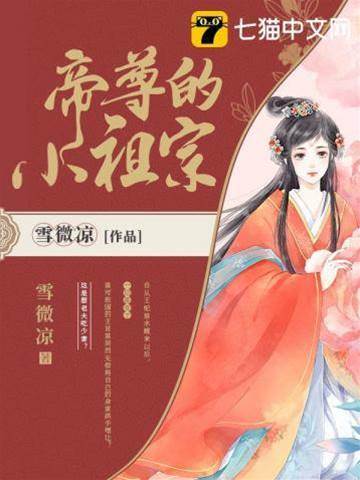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燼歡》 第20章 二更
陸縉并不在意妻子說了什麼,只捕捉到前一句——
妻妹已經“睡下了” 。
他看了一眼滅燈后的水云間,略略思索后,偏偏對江華容道:“時候不早了,我今晚同你一起回披香院。”
這話落到江華容耳朵里,第一反應是陸縉是在刻意等。
等了兩年了,終于等到陸縉為駐足,江華容喜上眉梢,立即便要答應,一看到外面濃黑的夜,忽地又想起這是深夜。
江晚剛剛服了藥睡下。
不能。
江華容角的笑意慢慢淡下去,尋了個借口:“我……我明日要去護國寺燒香還愿,今日需抄經,待明日供奉,不知要到幾時,郎君若是去了,恐難服侍周到,郎君明日再來如何?我備下酒菜,與你小酌一番。”
偏偏那麼巧。
妻妹睡了,妻子也不見他。
“還什麼愿?”陸縉垂眸轉了下指腹上的扳指,追問道。
“祖母病了,我打算為祈福,也好讓老人家早日好起來,還有……”江華容略有些赧:“我想求子,母親一直催我,祖母也病重,子嗣之事著實不可怠慢。”
陸縉本也是要去護國寺,妻子這麼一提,他忽然記起護國寺除了燒香靈驗,似乎還有一位出了名擅長癥的法師。名喚凈空的。
“是嗎?”陸縉眼神多了一打量,“既是祈福,以表孝心,用不用我陪你一起?”
“不必了,護國寺并不遠,馬車來回不過半個時辰,我去去便回,郎君奔波勞累,不用為我分心。”江華容仍是拒絕。
陸縉心里一沉,聲音卻愈發溫和。
他溫沉的應了聲“好”,反安:“這兩年你著實辛苦了,既要持家,又要侍奉母親和祖母,我不在時可遇著什麼難?”
Advertisement
江華容難得聽他關切,鼻尖微酸,卻只能搖頭,將滿腹的苦咽下去:“沒有。祖母慈善仁和,婆母也待我極好,只是郎君你不在,我一個人有時寂寥了些,你如今回來了,我哪里還有值得煩心的事?不過是子嗣被催催,算不得什麼大事。”
“剛圓房半月,子嗣之事你不必急。”陸縉看向的眼,“你我既已了婚,便是夫婦,從前還是往后,遇到了難事你皆可同我說。”
江華容一聽,覺得自己的眼果然沒錯,愈發著急地想趕快解決這樁事,最好是自己的病能治好,治不好江晚也要盡快懷上,太想同陸縉真正的在一起了,毫無阻礙的在一起。
“我曉得的,也不曾著急,不過是為祖母祈福順便燒柱香,又聽說那里香火靈驗,順便去求一求罷了。”江華容低低答應了一聲。
陸縉見妻子言語克制,沒再多言,目送回去,眼神隨著的背影遠走卻一點點暗下去。
等人走后,回了前院,陸縉略一沉,吩咐了康平明早也去備車。
他要親自去一趟佛寺,一探究竟。
***
次日一早,天剛蒙蒙亮,江華容便出了門。
陸縉的馬車遠遠的跟著,不遠不近,正方便觀察,卻又讓不能發現。
一開始,只見,江氏的確是去佛堂燒香,然后供了兩盞海燈。一盞一天是四十斤油,一斤燈草,另一盞是二十斤油,半斤燈草。
但尋常人禮佛不過是供個三斤五斤的,便是顯貴之家,除非婚喪嫁娶,一天也二十斤也算是豪奢了,四十斤的十分見,也有人能出的起。
江氏一來便供了如此多,足見求的愿不小,煩心事也不。
等走后,陸縉了供海燈的小和尚把那兩盞燈拿過來。
Advertisement
“施主,這是那位夫人供的,不好讓旁人瞧見,這……”小和尚細聲細氣地解釋。
“拿來。”
陸縉看了那小和尚一眼,直接打斷。
這一眼一看就是久居上位的人才能養出的氣勢。
仿佛雷霆萬鈞,沉沉的下來,小和尚自小長在佛寺,哪里被這麼打量過,又見他著華貴,氣度非凡,恐怕不是常人,只好唯唯諾諾的答應。
“施主且稍等。”小和尚盯著他的目,從一派神龕中找出了兩個。
每盞海燈下面都懸著一個木牌,上面用紅字描摹著,表明供主的的所求。
陸縉掀開海燈下面懸著的木牌看了一眼,只見第一盞一日供了四十斤油的木牌上面寫的大意是求子,且十分求。
可江氏一個剛婚,剛圓房半月的婦人,為何如此執著于求子?
陸縉將木牌轉了回去,猜疑又重了三分。
又掀開另一盞海燈下的木牌,這個木牌卻是空的,上面一字未書。
這便更讓人生疑了。
尋常人禮佛自然是要把心愿寫的清清楚楚,滿天神佛才能庇佑,江氏捐了如此多的香油錢卻供奉個空海燈,實在反常。
要麼,是有難言之,不方便說。
要麼,是做了虧心事,完全不能說,只能以這種方式求個心安。
但無論是哪一種,江氏,都必定有事瞞著他。
且藏起來的恐怕不止一個,亦不是小事。
陸縉放好海燈,眼簾一掀看向那小和尚:“今日之事不準對任何人說,明白麼?”
“施主放心,我必定守口如瓶。”
那小和尚連聲答應。
陸縉才轉離去,繼續快步跟上江華容。
江華容禮佛之后并沒回去,而是戴了冪籬,由早已知會好的和尚引著去了凈空法師的住。
Advertisement
自以為做的,卻不知陸縉早已站在了對面的閣樓上將一切盡收眼底。
一刻鐘后,江華容戴好了冪籬出了門,陸縉隨即在后進去。
凈空擅長癥,聲名遠揚,每日皆有無數人從四面八方前來拜訪,每日只接待十位,是以陸縉一進來,守在門口的小沙彌便要將人逐出去。
“施主,你不能進!”
這回都不必陸縉發話,康平眼眉一豎,那小沙彌頓時便被嚇得消了聲,為難的看向里面。
凈空見來人樣貌不凡,氣度亦是雍容,只擺擺手,那小沙彌退下,反倒替陸縉斟了盞茶。
“敢問貴客,是有何事拜訪?”
“未經許可,擅自闖,是某違了禮數叨擾大師。”陸縉對著這位法師,倒不像方才對那小和尚一樣威,而是換了懷之策,略表歉意,“實不相瞞,剛剛出去的那個婦人是在下人,人近日郁郁寡歡,怕我憂心,便獨自出了門,來了佛寺。在下也是擔心過度,才追隨進來。敢問法師,我人,是為何而來,所看的又是何病?”
原來是這樣。
凈空想起那婦人的著,與眼前之人皆出自同一針法,信了許多,又見陸縉雖語氣略含歉意,但言辭卻不容拒絕,一看便是上京的貴胄。
且他后還跟了個帶刀的侍從,虎背熊腰的,看著像是行伍之人。
凈空游走于顯貴之間,早已知曉他們的脾,便是不說,他們也有辦法教你開口,且剛剛那婦人吞吞吐吐的,似乎在瞞什麼,當下也不再顧及,便順手賣個人:“郎君不知?你夫人是為了求子。”
果然同陸縉猜的沒錯。
他搭在桌案上的手指叩了一下,眉間微微皺著:“可我有事在外兩年,同我夫人圓房剛半月,時日尚淺,應當診不出子嗣,何故著急求子?”
Advertisement
“剛半月?”凈空乍一聽聞,眉頭皺的比他還深。
“有何不妥?”陸縉追問。
凈空看了眼他,面躊躇,又問:“這半月,郎君同夫人還圓了房,一共幾回?”
“兩回。”陸縉并未瞞。
凈空面難,念了句佛號,行醫多年,這還是他頭一回到比病癥更難治的病。
他沉了片刻,才委婉地道:“剛剛那位夫人患的是不育的痼疾,且之前已下紅一月,最近剛止,先前絕不可能與人圓房。郎君你……是否認錯人了?”
“不能圓房?”陸縉倏地抬起了頭。
凈空見他一副不知的樣子,也深罪過,只點頭應是:“絕不可能。”
原來如此,原來江氏從一開始便不能圓房。
所有的猜疑在這一刻落了定,陸縉眉眼凜冽,周的氣息亦是冷的發灰,仿佛檀香燃畢后的灰燼。
好個痼疾。
好個不育。
他如此敬重江氏,惜江氏,被折磨了數日,就是不想變同父親一樣的人,甚至疑心是自己心思不純,機不正,甚至直到昨晚都夜不安寢,徹夜難眠。
江氏卻一直在欺他瞞他,對所有人撒下了彌天大謊,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可妻子若是不能圓房,那麼問題來了……
前幾晚,與他同床共枕的那個人,又是誰?
幾乎不用思索,不用猜想,陸縉腦中瞬間冒出了一個答案,一個明顯的不能更明顯的答案,囂著要沖出來……
搭在桌案上的指一蜷,他遽然站了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671 章
小弟個個是大佬
穿成暢銷漫畫男主的契約妖獸,還是被炮灰那隻。 然而,並不…… 隨便揍一揍,就揍出個身份顯赫的大佬。 隨便挖一挖,就挖出堆極品靈器與珍寶。 大佬小弟們:“老大太帥了,今天又又又特麼開掛了!” 蘇黎:“不,我隻是個嬌弱又軟萌的小可愛。” 隻是傳說中高冷腹黑清心寡慾的男主畫風也不太對。 他說:“我命裡旺妻,你要不要試一下?”
122.6萬字8.25 12694 -
完結394 章

病嬌相爺以權謀妻
攝政長公主權勢滔天,野心勃勃,手段毒辣,所以活該被至親謀殺,尸骨無存?重生到閑散王爺府上,鳳執表示很滿意,白撿了幾年青歲,郡主身份悠閑自在,還有個未婚夫婿俊美出塵。本想悠閑過一生,然而山河動蕩、皇權爭斗,終究是躲不過權力傾軋。鮮衣鎧甲,華裳錦繡,她千方百計謀奪權勢,終于大權在握,登臨帝位。為國為民?不,她要后宮三千,美男任選。龍椅旁的相爺‘不小心’扯開衣襟,露出她的罪證,‘三千美男’瑟瑟發抖,誰敢跟這位搶?鳳執磨牙,她可算是知道某人的用心險惡了。---------江山為棋,翻手云雨,覆手乾坤,落子無悔!邪魅冷酷權欲女主VS腹黑悶騷病嬌男主。男強女強,勢均力敵,一對一,強勢爽文寵文。
67.9萬字8.18 39735 -
完結690 章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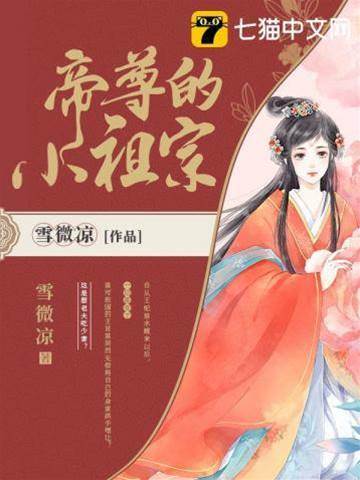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