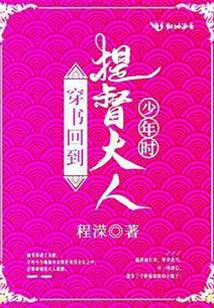《燼歡》 第84章 交鋒
晴了兩三日, 夜半忽地下起了雪。
鉛云低垂,細雪翩飛。
許久后, 房門才打開, 陸縉領口微敞,瀲滟。
自打回來后他尚未用茶,使很心的要替他換壺熱茶, 陸縉只從間低沉地笑一聲:“不用。”
反讓使打了盆熱水。
又擰了帕子,替江晚洗。
剛剛他并未要江晚, 只是看眼底微青,心事重重, 這幾日大約都沒睡好, 讓發泄發泄,睡得安穩些。
果然, 沒多久,沾枕便睡了過去。
呼吸清清淺淺的,長而卷的眼睫還微微著。
睡的沉,且靜。
使鮮見到陸縉,往常見他, 他總是不怒自威, 寡言語。
今日卻過那雙烏沉的眸子看出了一縷溫。
聲音都放的極低。
這絕不是對一個外室該有的耐心, 使頓時對江晚的份又遲疑起來, 謹慎了許多。
再一看,陸縉額角似乎還有沒干的晶瑩汗珠, 眼皮跳了跳,連忙垂下了眼, 放下了盆出去。
陸縉站在門口散了散涼, 吹散滿的熱氣后, 他回擰了帕子細細的了臉,又挑了些藥揭開江晚的,方擁著一同睡。
一上榻,江晚似有所,明明睡得迷迷糊糊的,仍是一點點往他懷里鉆,尋了個舒服的姿勢,又睡了過去。
簡直乖的不得了。
陸縉低笑,單手穿過的發攏了攏,擁著一同睡了過去。
這一晚的確是江晚自從事發后睡得最好的一晚。
尤其倚著個溫溫熱熱的火爐,手腳皆被暖著。
睡的黑沉,第二日天剛平明,便自然醒了。
一睜眼,著眼前睡的陸縉,愣了愣,才想起昨日的一切。
Advertisement
其實,江晚又何嘗不知陸縉對的好,好到無法承。
然哥哥待亦是極好。
誰都不想愧對,只有夜夜翻來覆去,不得安寢。
這幾日實在太,此刻從旋渦中離,江晚方能冷靜。
此時,再仔細回想,發覺對他們其實愫并不一樣。
同哥哥一起長大,那時無憂無慮,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在及笄之前,幾乎沒見過外男,很早便知道要嫁給他,也從未想過會有別的選擇,是以當哥哥在說心悅的時候,并未遲疑便答應了。
然現在再回想,已經記不清哥哥是如何對說的了。
只記得那時他站在一株大榕樹下,過樹梢疏疏落落的下來,有細碎的點跳躍在他指尖。
一邊聽著他的求娶,一邊低頭去看他指上的碎。
指尖開開合合,偶然住了一只誤停上來的蝴蝶,笑著遞到他眼前。
“看。”
“阿,不急,你先回答我愿不愿意?”裴時序失笑。
“自然是愿的。”點頭,心思卻更多放在指尖的蝴蝶上,執著地遞到他面前,“好不好看?”
“好看。”
裴時序了的發,嘆一口氣放飛了蝴蝶。
陸縉則不同。
和他之間本就是一場意外,那時,亦絕境。
面對他,畏過,懼過,哭過,笑過,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他一句話讓如臨深淵,一句話又將送云端。
江晚曾設想過無數次萬一遇上的不是陸縉該如何是好?想來想去,換任何一個人,如今,必然都是萬丈深淵,敗名裂。
他是被卷這場旋渦時唯一看到的一束亮。
就像一株長在峭壁上的花,沒有蜂蝶嬉戲興許會寂寞些。
Advertisement
而沒有,卻是會慢慢枯萎的。
江晚看著眼前睡的人,指尖輕他高的鼻尖,緩緩往下,當及到那薄且鋒利的時,忽然,陸縉張了。
江晚趕蜷手,才免得被銜住。
“還沒看夠?”陸縉睜了眼。
聲音還帶著剛醒時獨有的低沉。
江晚捂著臉:“誰看了?”
陸縉笑,寬大的手扶在腰上:“醒這麼早,不?”
“不。”江晚搖頭。
陸縉又道:“我了。”
“那我幫你倒茶。”江晚很心的爬起來。
陸縉卻抓住腳踝,角淺淺的:“有你在,還用什麼茶?”
江晚瞬間明了,臉頰微滾,瞪他一眼。
陸縉失笑,一手抓著腳踝拖回來,薄在耳畔:“玩笑也開不得了,讓我親親。”
“不要。”江晚愈發抿了,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秀氣的眉都擰了一條繩。
“漱了口了。”陸縉笑。
“真的?”江晚遲疑。
“假的。”
趁著張口,陸縉直接俯欺吻。
江晚睜圓了眼,嗚嗚地去推。
卻被沉沉的住,咬了他一口,方趁機逃,赤著足便下了地,端起茶杯抿了一大口便要吐出來。
陸縉眼底笑意卻更深。
江晚頓時啞然,明白又被戲弄了,他這樣潔的人怎可能沒漱口。
于是悶悶地又將茶水咽了下去。
“……不早了,你還不走?”
“趕我?”陸縉了下破損的角。
“天快亮了,你不是說怕暴行蹤,需要早些離開。”江晚小聲。
“不差這一會兒。”陸縉起,抱起江晚放在桌子上,這個高度,他下頜剛好抵在額上,低沉地道,“剛剛沒夠,頭抬起來,再給我親會兒。”
Advertisement
江晚完全拒絕不了,遲疑了一下,還是朝他仰起了頭。
修長的頸被握在了他手中,調整到更合適深吻的角度。
含吮勾磨,追逐嬉戲,江晚被按在桌子上,腰都塌了,到底還是被里里外外親了個遍,親的天都亮了。
一吻畢,險些了,氣吁吁的趕推開了陸縉:“真不早了……”
真是,越親越解不了。
陸縉從間嗯一聲,雙臂撐在桌沿,到底還是著江晚的臉淺啄了幾下,才將從桌上抱下來。
聲音卻帶著意。
“先攢著,遲早收拾你。”
江晚抿了下,心口卻微微麻。
***
趕在天大亮之前,陸縉還是回到了國公府里。
此時,裴時序也進了府。
冷靜了一夜,他今日原是來向江晚道歉的,還特意帶了最的蝴蝶。
只是剛到水云間卻被告知江晚回青州探外祖去了。
“什麼時候的事?”裴時序皺眉。
“今早。”使面不改,按照陸縉說的道。
“今早?”裴時序眉頭皺的更深。
不可能,阿一向對他知無不言,要離開這樣的事不可能提都不跟他提一句。
且在這種時候,走的這麼急。
裴時序心有不安,擱下蝴蝶立即出府去尋林啟明,得到的答案卻是林啟明也跟著一起去了。
這愈發不對。
便是江晚昨日被嚇到了,沒道理林啟明也不同他說一聲。
裴時序摁了摁眼角,腦中只冒出了一個人——
陸縉!
一定是他。
裴時序曾想過江晚藏起來,推己及人,陸縉必然也是。
他快馬趕回國公府,正撞見陸縉進了門來。
上,還帶著尚未凝固的痂。
這模樣,必然是從溫香玉里剛回來。
Advertisement
“——是你?”裴時序下了馬,目沉沉。
陸縉眼神冷淡,只說:“堂弟這是何意?”
堂弟是陸驥給裴時序安的份,陸縉此言顯然是在暗諷。
裴時序倒是不在意這份,此刻,他眼中只有江晚,聲音也冷如寒冰:“阿是不是在你手里?”
“不是回青州探親了麼,同我何干?”陸縉神如常。
“你不必裝腔作勢,阿要走,不可能瞞著我,一定是被人帶走了。”
陸縉卻只是笑:“你未免太高估對你的信任。”
要同舅舅走,不是也沒對他說過麼?
“是麼?”裴時序盯著陸縉上的痂,“那世子上的痂又是怎麼回事?”
“你說這個?”陸縉了下破損之,“不慎被貓撓的。”
“貓?”裴時序眼睛微微瞇著。
“昨晚犯了小子,撓了我幾爪,不但是,我頸上臂上皆有,堂弟若是不信,大可一看。”陸縉從容的道。
什麼貓?他分明說的是人。
這話擺明了江晚就是在他手里。
昨晚,阿必定遭了難。
裴時序著怒氣:“阿已與我有了婚約,你如此行徑,豈非強占人|妻?”
“即便是妻,與我才是一對事實夫妻,何來強占?”陸縉輕易便反駁回去。
裴時序瞬間暴怒,一手攥住了陸縉領:“你不必詭辯,說,阿在哪?”
陸縉瞥了一眼被弄皺的領,眉眼不悅:“放開。”
裴時序卻只是諷笑,因著傷病未愈,明明在笑,卻更顯郁:“傳聞中,你不是最風霽月,舉世無雙麼,原來不過也是個表里不一,欺世盜名之徒!”
“倒也是,傳聞中,開國公亦是用至深,忠貞不二,為娶長公主曾當眾宣稱不納妾,與一生一世一雙人,可這傳聞,你信嗎?”
“若是信,你又算什麼東西?”
陸縉角亦是勾起。
裴時序臉微僵,須臾,笑意更深:“的確,不愧是父子,皆是假仁假義,我看,這整座國公府,也找不出一塊干凈的磚。”
“既如此,你回來作甚?”陸縉反問。
“我本不在乎這些,我只要阿。”裴時序攥著陸縉的手一,將他在照壁上,“把阿還給我。”
陸縉直接剪住他的手,接著,用三倍的力還回去反一把攥住裴時序脖頸猛地撞在照壁上,撞的浮塵簌簌的掉落。
“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武將出,在我面前手,你就這麼想找死?”
裴時序頸上瞬間暴漲,面卻撐著平靜,吐出幾個字:“莽夫而已。”
“莽夫?”陸縉笑。
“或是……懦夫?”裴時序嘖了一聲,眼睛微微瞇著,“你是怕爭不過我,才使出如此手段?”
“爭?”
陸縉手一松,放開了裴時序。
“不是嗎?否則你為何不敢正大明?”裴時序反相譏。
陸縉只覺得可笑。
而過時,他撣了撣被弄皺的領,勝券在握,語氣輕慢。
“我從未將當過你我相爭的籌碼,我要的從始至終都是心甘愿。”
“再說,你拿什麼與我爭,又配與我爭嗎?”
“僅憑你這句話,你早已一敗涂地!”
猜你喜歡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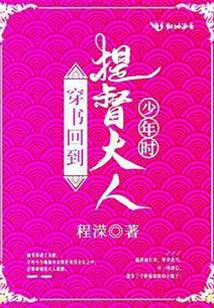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1 -
完結1044 章
法醫王妃別動刀
九王妃慕容諾有個+∞的膽子,你送她花,她看不上眼,你送她豪宅金山,她提不起勁兒,你讓她去驗尸,她鞋都不穿就沖在最前面!身為皇室顏值天花板的九王爺沐清風就很看不慣她,從來沒給過好臉色,寧可抱著卷宗睡覺也不回家。全王府都認定這對包辦婚姻要崩,直到有一晚慕容諾喝醉了,非要脫了沐......清風的衣服,在他身上畫內臟結構圖。蹲墻角的阿巧:完了,王妃肯定要被轟出來了!蹲窗下的伍叁七:王爺怎麼乖乖脫了,等一下……王妃怎麼也脫了?!!!
150.6萬字8 67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