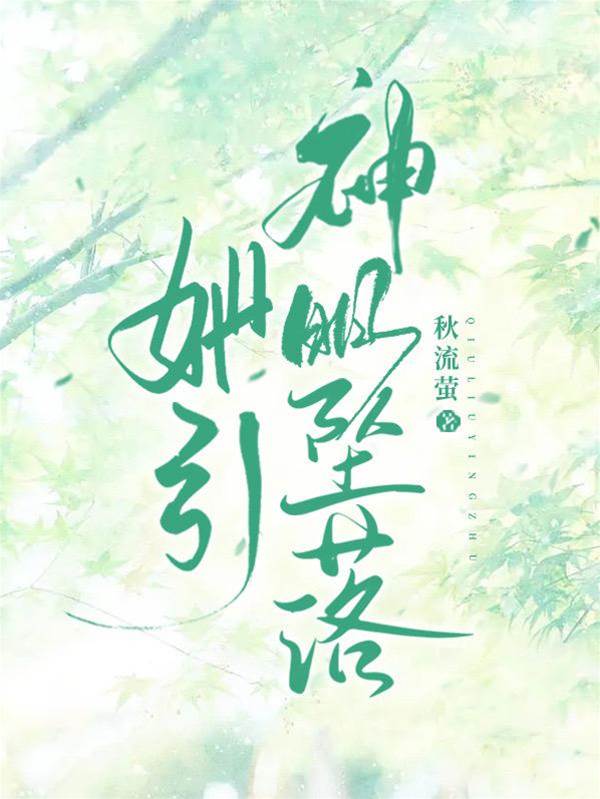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暗里著迷:席總又被小撩精偷吻了》 第482章 啟程篇丶分享欲
他也連忙從床上坐起來,顧不上緩解自己剛醒過來有點暈眩的腦袋,踉踉蹌蹌的追了出去。
到了裴月的病房后,顧傾城和醫院的專家、教授在門外說著什麼,他看了眼兄長,垂眸靜靜走了進去。
但病房,他也看不見裴月。
裴月所有的親友都圍在的邊,他抬頭往最里面看了一眼,看到季雪正與裴月擁抱著。
姐姐蒼白著臉,神有點呆滯,一看就是昏迷剛醒過來,而季雪卻閉著眼睛,滿臉淚痕。
旁邊的其他人也都等待著和裴月說話。
此此景,本不到他和姐姐說點什麼。
一種莫名其妙的無助席卷了奕安的心。
就覺得,自己認這哥哥姐姐的路,應該很難走。
就在他覺得失落時,突然發現這麼多人里,沒有席硯琛。
頓時,青年的眸子亮了。
現在無助,不等于他會放棄和哥哥姐姐的相認。
他果斷的轉過,想要去找席硯琛。
和姐夫打好道,通過姐夫也能和姐姐接近。
之后他在席硯琛睡覺的病房外和他面,一同重回了裴月的病房。
隨后席硯琛和裴月的互,溫馨又令人淚目。
俗話說,患難見真。
裴月這一病,照出了席硯琛,赤,并對毫無保留的真心。
而兩人說了會兒話以后,蘇醒的裴月才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幫移植的骨髓。
此時此刻。
奕安和顧傾城兄弟兩人,隔著三米遠的距離并排站著。
都在人群之后。
但說起骨髓移植,大家把焦點放在了顧傾城上。
而這位拯救了裴月的男人,也輕笑著,和裴月互。
顧傾城的打扮向來張揚極設計,雖如今在醫院,他沒有多在意自己的形象,但他渾上下依舊是一白。
Advertisement
白,在某種時候,會給人一種很清冷很有距離的覺。
這也是顧傾城在奕安眼里的印象。
但現在,這樣清冷的男人,卻靠言語逗笑了裴月還有他的朋友們。
奕安抿住了。
哪怕席昭延和席硯琛都歡迎他在這里,可這一刻,他覺得自己與這里格格不。
因太想,和哥哥姐姐有所集,而眼前沒有任何機會,這讓他更覺得沮喪。
他忽然就想起了綺。
然后他轉往外走,也拿出了手機。
一個電話打在了綺的手機上。
綺的聲音帶著一些愉悅,“安東尼奧,怎麼了?”
奕安勾起了笑意。
平時心平靜的時候還覺不出來,就現在這沮喪時,他發現自己和綺聯系,會有點開心。
他說,“在做什麼,聽起來你心很好呢。”
綺說:“我用很短的時間拼了一張很復雜的拼圖!”
“那很棒呢。”奕安道,“我這里也有一個好消息,你要不要聽。”
綺默了默,“裴月醒了?”
奕安:“嗯。”
綺:“我就說,今天我喂養的小蛇都吃的格外多,它見過裴月,我就覺得這是好兆頭。”
“那你要來看看姐姐嗎?”
奕安在想,綺過來看裴月,他就能站在綺邊,同裴月做一個正式的自我介紹。
可誰料。
綺說的那句話,讓他突然迷茫,也讓他的心跳,突然了一拍。
“你要來找我嗎,我看到你,就等同于看到裴月啦!”
旋即,他的耳朵也開始悄悄泛紅,心跳的快了些許。
回過頭,再往病房看一眼,氣氛越來越溫暖,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話要和裴月說。
裴月也有很多話,想對這些不離不棄的親友們講。
Advertisement
奕安想了想,覺得這個時候,不適合自己和姐姐去相識。
一個是姐姐才剛醒過來,并不是真的康復。
二來,姐姐戰勝了病魔,比起和其他人說話,可能最想和席硯琛還有自己的兒接近。
那麼事就不能著急了。
“好,你在哪里,我去找你。”他回答綺。
“在家,我給你定位,你直接進來就行,我會讓家里給你放行,不需要出卡。”
掛斷電話以后。
奕安悄悄的把病房的一切錄了個視頻。
在錄到裴月,還有顧傾城的時候,他又悄悄把視頻放大了,清晰的記錄了下來與他有緣關系的兩個人的微表。
他沒有發給上嬑,而是打開通訊錄,給備注為“外婆”的用戶,打了電話過去。
在電話接通的時候,他沒有進電梯,而是踩著樓梯走了。
此刻的樓梯上只有他一個人。
他的腳步聲在空間里有的回聲,聽不見對面說了什麼,但看奕安臉上出的溫的笑,必然是對面說了什麼讓他覺得開心的話。
然后便是他說。
“外婆,哥哥和姐姐都很厲害,哥哥的行雷厲風行,姐姐也有很強的求生意識,看到他們相認了,我很開心,也很羨慕。”
“嗯,現在我沒有去和他們兩個說話,雖然我很小的時候就想和哥哥相認,但這麼多年都沒有進展,想了想,也不急于一時,何況席先生記得我,回頭等姐姐的病徹底穩定了,我再過去也不遲。”
“現在我去家,找朋友,也是哥哥的朋友,嗯,給小侄的出生禮我有在考慮,想來想去,我想親手給孩子做一份禮,您覺得呢?”
“謝謝您給我鼓勵,也希有一天,哥哥、姐姐,還有我,能一同去拜訪您。”
Advertisement
除了這些,他和外婆還說了很多。
一直到他走出醫院,攔到出租車才掛斷。
上了車,把地址給了司機,他在v信上也找到外婆的賬號,把自己拍到的視頻發給了外婆。
隨后他收到了一條語音消息。
溫而慈祥的老夫人,言語哽塞:“我的外孫可真漂亮,你哥哥也瘦了很多。”
本來奕安心還很平靜,聽到外婆講這樣的話,他修長的手指頓了頓,發出一句:[從今天開始,姐姐會更漂亮,哥哥也一定能吃得下飯了]。
之后,他收好手機,轉頭看著車外的車水馬龍,他角勾起微笑,但兩行清淚,卻悄然從眼眶落。
雖然他至今沒有同裴月說一句話。
但是因姐姐終于擺絕的激,終于在這一刻,在心里徹底化開,讓他像之前在裴月面前,就沒忍住哭泣的其他人那樣,落下了徹底安心的眼淚。
姐姐,活下來了。
他任由眼淚流了一會兒。
等心平復了,他才又拿出手機。
外婆提醒他也要注意,如果有時間,就去上家找外婆說說話。
他回復了外婆以后,又打開了綺的對話框。
不知是不是新的朋友和自己很契合的緣故,他愈發覺得認識綺真好。
他曾經,很有分。
許是見的多了,麻了,遇到什麼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只是自己平靜的。
但現在,他對綺多了不分。
如,他又給綺發了條v信。
[綺,我這次回國收獲很大,與你了朋友,同時也覺得未來能更幸福,我想,我一定能和我的哥哥姐姐相認,并在未來好好相。]
但是綺沒有回復他。
奕安也沒多想,尋思可能是在忙,沒有看手機。
Advertisement
一個多小時后。
車到上帝都南郊的一座山下停了下來,前面有道閘,就只允許家或者得綺允許的私家車進了。
奕安在這里下了車,到了門房口,與里面的保安大哥作揖,然后繞過道閘,順著寬闊的柏油路往遠以棕紅為主調的別墅去了。
步行了十分鐘,他進了別墅的正門口。
門開著,但他還是禮貌的敲了敲。
室有一位年紀約麼三十多歲的傭人,還是藍眼睛,說著蹩腳的漢語:“總在三樓。”
奕安道謝過,又一路折轉到了三樓綺的起居室。
門微掩,奕安再次敲了敲門。
但沒人應。
奕安又敲了下,還是沒人應。
青年想了想,推開門走了進去。
然后奕安有些詫異。
綺的臥室裝修很抑,沒有什麼窗戶,全都是黑白灰。kΑnshu伍.ξà
現在夜幕已經降臨,天已經很暗了,綺的臥室還拉著窗簾,窗戶前放著兩個大玻璃鋼。
里面都是蛇。
看到這個,奕安的手心控制不住的起了一層細汗。
但除了這些,卻本不見綺。
奕安拿出手機撥通了綺的號,沙發上傳來了震。
而綺還是沒有出現。
這個時候,奕安察覺出了不對勁。
“綺!”
他嗓音染上焦急,一邊喊著的名字,一邊在室尋找。
不消片刻,他在浴室門外看到了綺的上,他再把周圍掃視一圈,其他房間的門基本都開著,就浴室的門關著。
“綺!”他又一聲,抬手用力拍響了浴室門,“你在里面嗎,你有沒有事?”
依舊沒人回應。
接下來,奕安沒有扭,手先是攀上門把手,擰了兩下發現里面反鎖著,他便馬上在自己上的改良漢服上,卸下了一枚別針,然后把針掰直……
幾秒后,鎖在他的鼓搗下開了。
他推門進去。
偌大的浴缸里放滿了水,最上面還全都是如云朵一般的泡泡,綺小小的子在泡沫里,但肩膀、口、膝蓋,都在泡泡外著。
而,失去了意識。
這一幕也讓奕安震驚。
青年震驚的不是綺的在浴缸里昏迷。
而是看到了……
口那抹不掉的帶著侮辱詞匯的紋。
可眼下的境況,容不得他多去消化緒,他很快回思緒,走到浴缸旁蹲下,手探了下的脖子。
大脈在跳,但卻微弱。
奕安的瞳仁,出了慌張神,接著他一手護著綺的頭,一手掐上了綺的人中。
這是他當下想到必須要做的事。
因他不知道綺在浴缸里昏迷多久了,他看見了,他便先第一時間確定了一下綺的心是不是在跳。
他也必須先往最壞、最糟糕的方向去猜測,因近些年,年輕人突然猝死的新聞太多了。
隨后確定綺生命無礙,他就必須得讓睜開雙眼,這樣才能都安心。
又大概四五分鐘后,奕安覺得自己的大拇指有點酸了,綺緩緩睜開了眼。
兩人視線對上的那一刻,奕安松了口氣,收回手站起,道:“我去傭人。”
綺上的泡泡當著的,他救沒有丁點越界,現在醒了,他就要人來幫綺起穿。
但誰料,就在他要走時,綺虛弱道:“站住。”
奕安回頭:“嗯?”
剛醒來的綺眸子有點迷離,但即便如此,的眸子卻垂下看了眼自己的口,“你看見了?”
并不是突然就害怕自己這里被人看到的。
過去,那里被刺上刺青以后,在那日日夜夜里,太多骯臟如老鼠的人,盯著那里的刺青,對說盡侮辱的話語。
從最初的害怕、難堪,到日復一日的心痛苦中開始變得麻木了。
以為自己無所謂了,可后來被羽和顧傾城拯救,又回到了正常的世界后,才發現,過去的傷害雖然麻木了,但一直在。
害怕這里被人看見。
缺失了很多緒,卻在當年那麼迅速的明白了什麼自卑。
奕安順著的視線,目坦然的落在了的口。
敏聰明如他,只是看那侮辱的詞匯,似乎也大概猜到了什麼,他說:“刺青,最早見于春秋戰國時期,也被稱作‘涅’,后來刺青又了黥刑,在犯人的臉上或者額頭刺字或者圖案。”
他淡淡的訴說著這個,那張俊的臉上,也看不出任何緒。
就好像是一位清冷出塵,看萬的神祇,在像后來者,講述歷史長河里的是非善惡。
他不會因此對同,也不會因此對出暗的一面。
就是很平靜的,離開的,看那個圖案。
綺骨突然一哽。
這個異看,不僅不排斥,甚至還生出了一種,想要對他傾訴的。
基于此,問:“是不是很難看?”
奕安默了默:“這樣的刺青的確是難看,但是去不掉嗎?”
他這句話,也不摻雜很多的緒。
就像兩人一起逛街買服,自己試了一件服,他覺得不好看,就很隨意的說了一句,不好看,換一件試一試吧。
而這種隨意,吹散了綺心因這刺青,很久很久都難走不出的偏執的自卑。
“去不掉,只能修改。”說。
猜你喜歡
-
完結511 章

聽說校草被甩了
安靜內斂沉默的少女,嬌生慣養毒舌的少年,兩人之間坎坷的成長曆程與甜蜜情深的故事。*雲慎曾在學校時聽到這樣一段對話--「聽說言謹被甩了……」「誰這麼囂張敢甩了他?」「雲慎啊。」「那個偏遠地區的轉學生?」「可不,不然還能有誰?」全校同學集體沉默了一會兒,唯有一道聲音有點不怕欠揍的說道:「這年頭,言謹還會遇上這麼活該的事情?」雲慎「……」*他們的愛情,屬於那種一切盡在無言中,你圍著他轉,卻不知,他也圍著你轉。很甜很寵,包你喜歡,快來吧~
80.4萬字8 14759 -
連載2595 章

霸道帝少惹不得
安希醉酒後睡了一個男人,留下一百零二塊錢,然後逃之夭夭。什麼?這個男人,竟然是她未婚夫的大哥?一場豪賭,她被作為賭注,未婚夫將她拱手輸給大哥。慕遲曜是這座城市的主宰者,冷峻邪佞,隻手遮天,卻娶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從此夜夜笙歌。外界猜測,一手遮天,權傾商界的慕遲曜,中了美人計。她問:“你為什麼娶我?”“各方面都適合我。”言安希追問道:“哪方面?性格?長相?身材?”“除了身材。”“……”後來她聽說,她長得很像一個人,一個已經死去的女人。後來又傳言,她打掉了腹中的孩子,慕遲曜親手掐住她的脖子:“言安希,你竟然敢!”
424.7萬字8.18 52233 -
完結512 章

新婚夜,我治好了陸先生的隱疾
【一場陰謀撞上蓄謀已久的深情,經年仇恨,也抵不過陸靳宸想要溫晚緹一輩子的執念。】 *** 溫晚緹嫁給了陸靳宸。 她本以為,他們的婚姻只是有名無實。卻不想…… 她還以為,他和她都一樣,各懷目的,於是小心翼翼地守著自己的心。殊不知,他早把她鎖在了心裏。 *** 眾人都等著看她笑話,等著看她被趕出陸家大門的狼狽樣子。 哪知,等啊等,等啊等。 等來的是他替她遮風擋雨,替她找回親人…… *** 片段 他曾醉酒後,撫著她的臉呢喃,「阿緹,我放過你,誰放過我自己?」 他也曾清醒後,黑著臉沖她吼,「溫晚緹,我陸靳宸從和你領證的那一刻起,就認定了你。我們之間不會有生離,只有死別!」 *** ——後來, 人人都羨慕溫晚緹,她不僅是豪門真千金,還是陸靳宸寵在心尖尖上的女人。
98.4萬字8 46973 -
完結50 章

許以晴深
祁邵川是許晴心頭的一根刺……當那天,這根刺扎穿了許晴的心臟,讓她鮮血淋漓的時候,她就徹底失去了愛一個人的能力。但如果所有的一切重新來過,許晴興許還是會這麼做。…
5.2萬字8.18 14495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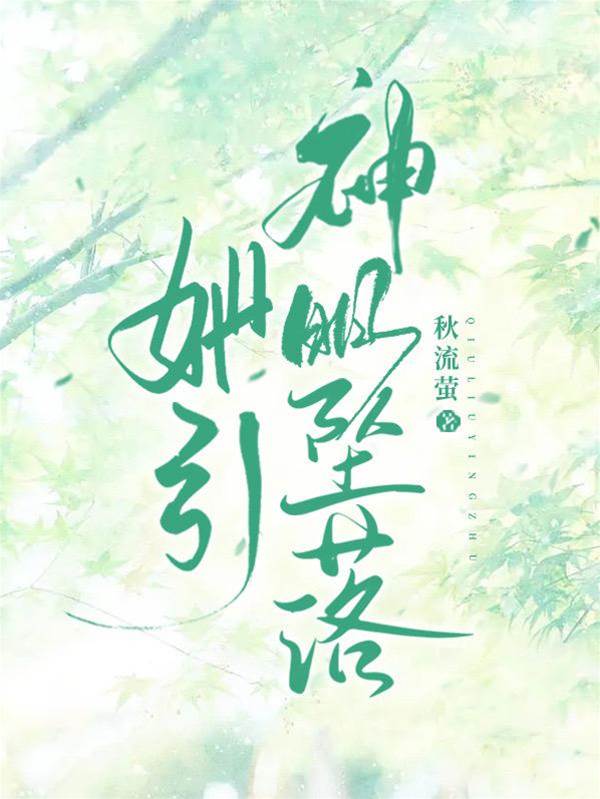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45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